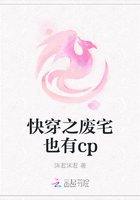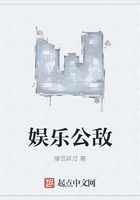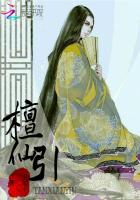性的面面观
中国让我敬畏:中国让我对人类的多样性深感敬畏。中国让我感受到文明的前进,这不断推动我们向更高深知识的掌握和更多的公正与理性思维的迈进。中国宛如世界的中心:它是人类物种基因的一个主要集中地,通过进化使我们获得对宇宙万物更多的启示和更深的了解。
第一次来到上海的时候,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文明的前进。在研讨会之前,我抽空参观了上海博物馆,那里展示了一部分中国最好的艺术品。各种瓷器、石器、铜器、银器和金器展品使我收获颇丰。但是我最喜欢的展厅是玉器厅,那里柔和的黄色灯光营造出了一种异样的平静和静谧。
我观察的第一件展品是一件装饰品——半透明的圆盘,曾经是佩戴在身上的装饰品。令我惊讶的是这件展品旁边的说明指出它制造于公元前三万年。我开始想像那个艺术家是如何制作这件精美玉器的。然后我又开始想像最初它被展示给什么人,当时的社会、住所、儿童和玩具是什么样子。
我来自澳大利亚,我的祖国建立于二百多年前,对我来说,想像三万二千年前的社会的确非常困难。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这件玉器并没有明显的实用价值。它既不是食物也不是住所,不能保护人也不能用来繁衍后代。它只不过是一件精美的物件,由工匠制作出来给别人佩戴。它表明在久远的古代,中国人就已对非实用性的情感乐此不疲了。这体现了一种高度发展的精神和审美感觉。他(她)们尝试着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快乐,情感和物质更加丰富。
我激动地给我远在澳大利亚的男友约翰打电话,告诉他我发现的玉器,和他分享我当时的谦恭和惊叹之情。来到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关于性的多样性、平等与和谐方面贡献一点新的思考,似乎是太冒昧了。而从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来到一个古老的国度似乎又显得过于雄心勃勃。
男友鼓励我坚持下去不要动摇。从古老玉盘体现出来的对美的追求和精神情感现在又被唤醒,让我们理解人类总是在探索自己对美和爱的感受的。人类总是不满足于基本的生存。人类是不断进化的复杂生物。他(她)们富于多样性。对大多数人来说,对自我、家庭、特殊朋友以及大自然的爱是重要的——是探索和渴望永不枯竭的源泉。
所以我克服了自卑的情绪。我要为这次研讨会提出我的想法。我是一名法律工作者,一名独立法庭的法官,一个国际人权发展和近年来抗击艾滋病行动的参与者。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有着不可剥夺人权和尊严的人。而且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所以可以通过分享个人的经历直接参与本次研讨会的讨论。
婴儿退化:对儿童的观察研究表明许多儿童,可能是大多数儿童都害怕或者厌恶与它们自己不同的事物。这当然是婴儿紊乱症的表现。大多数人受过教育后会摆脱这种心理紊乱。他们开始接受人类的多样性以及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形式。但有些人却做不到。
婴儿对不同事物或者陌生人产生排斥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性倾向只是差异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深受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宗教传统影响的国家,宗教经文暗示“选择”不同于大多数人所选择的异性恋作为性倾向的人是罪人、有悖于神之爱、违反自然事物秩序中的性爱情感目的:即繁衍后代、延续物种、推进自然进化。
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受到此类宗教教义的影响。确实,在中国有人信奉这些宗教,但人数并不多。基于此,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似乎更加可以从科学与理性的角度探讨性多样性。当人们认为神或者宗教是拒绝性的多样性的话,那么科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律师要试图改变人们的态度和社会体制就变得更加困难。
但是,中国虽然不曾有强有力的宗教,但却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特别是对家庭传统以及对婚姻、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重视。这些传统使得社会很难容纳性少数人群——包括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中性人的存在和权利。这些人群的出现,颠覆了对过去文化范式二元论的假设:人类被清楚地划分为异性恋的男性和异性恋的女性,没有给那些在心理、生理、性倾向方面有差别的人留下任何生存空间。中国也不例外。
导致产生婴儿紊乱症,对差异表现出恐惧的主要区分标准就包括性或性别。当然也包括种族和民族、肤色和文化、宗教和政治主张、残疾、艾滋病、精神疾病等等。
传统歧视:1993至1996年间,我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人权特别代表在柬埔寨工作。当时柬埔寨正在从战乱中恢复,我的工作就是动员各方尊重上述各个方面的多样性,推动保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
在工作中,我意识到种族歧视、疏远和种族优越感并不仅存在于欧洲社会,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毫无疑问,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也是一样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年轻的时候,澳大利亚推行一个叫做“白种人的澳大利亚”的国家政策,该政策是有法律效应的。非欧洲人后裔很难进入澳大利亚,更不可能成为公民居住在澳大利亚。当时,该政策得到支持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也因为人们从中体会到了种族和文化优越感。这使我联想到在上海博物馆刚刚看到的玉器,很难解释我们当时的优越感从何而来。不过,这就是澳大利亚在1966年前的真实状况。
那时许多澳大利亚人瞧不起中国人,甚至将其称为“未开化”的人。于是就很自然以此作为理由抵制中国人进入澳大利亚社会。不同的外表、饮食、语言、宗教和传统使得中国人在当时不受欢迎。现在这一情况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过我年轻时,那却是事实。
最终,通过教育,法律的修订,接触更多的中国家庭和中国人,理解不同生活方式的共同点等,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然而,这种态度的变化仅仅产生于欧洲后裔有机会接触、了解、信任和欣赏中国人之后。就在那一刻,人们的优越感开始不断减少以至消失殆尽。对差异的恐惧因了解和认识而得到化解。人们开始尊重崇尚和平、品格优秀、事业成功的中国移民,这使得整个国家对中国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了解、熟悉和认识中国人,而不是过去的那种对中国人的隔离。认识和互相尊重取代了恐惧。
性歧视:关于性也是如此。在过去(今天世界的许多地方也还是这样),性少数人群一直都被迫屈服,隐藏他们真正的情感。他们要伪装成为异性恋者,并对自己最亲密、最真切的感情深感耻辱。许多(可能大多数)男同性恋者可以成功把自己伪装成为“直人”(异性恋者)。我自己也是很多年都这样做。澳大利亚和大多数国家一样曾经实行“不问不说”政策。这一原则又得到法律的强化。在澳大利亚,直到二十多年前,男性之间的性行为仍然是严重的犯罪,即使双方都是成年男性,自愿在私下进行性行为。澳大利亚的警察诱捕男同性恋者。如果被抓住的话,这些受害者就会被迫害、羞辱、判刑入狱。此外,宗教宣讲、父母和家庭的期望以及经济方面的考虑也强化了同性恋者的自我否定。
三十年前,澳大利亚几乎没有人会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今天,包括身居要职的许多人仍然否定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当然,他(她)们也是迫于同性恋恐惧者以及狂热分子的压力才这么做的。他(她)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身居要职。但是旧的枷锁逐渐崩塌。我们已经目睹了这一变化的后果,而这一变化尚在进行中。仍然有法律基于性倾向歧视性少数人群。但是澳大利亚全境已经废除了针对同性恋者的刑法条款,引入了保护同性恋者免受歧视的新保护措施。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同性恋公民开始抛弃他们的假面具,寻求或者要求其他公民的承认——承认他们的平等地位、作为人的尊严和自尊。
变化的理由:人们在性倾向问题上态度的转变为何会在这个历史时刻出现呢?为何荷兰、比利时、美国的马萨诸塞州、西班牙、加拿大和南非已经向同性恋公民的平等权利,比如婚姻,迈进呢?为何有些国家立法赋予同性伴侣官方承认的民事结合的权利呢?为何在如此短暂的历史时期内,许多国家废除了惩罚成年人私下自愿进行性行为的刑法条款呢?为何有些国家的法院认为这些条款违宪呢?为何越来越多的地方出现了同性恋的群体,它们庆祝性多样,分享经济利益,享有公开身份,组建民间协会组织保护越来越多的承认对同性有好感的人群,他(她)们再也不因自己同性恋的身份而感到羞耻,而觉得这再也正常不过了呢?
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有些支持性少数人群平等权利的人指出,有必要解释并证实这些新的发展趋势。他们认为,从根本上说,国家和社会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基于某些公民和其他人发生某种性行为或者与其组建何种关系,而歧视他(她)们。对这些支持者来说,这些都是个人的私事。一个社会秩序良好的社会没有权力干涉这些。它必须平等地对待所有人,因为平等是一个人受到尊重的必要体现。
鉴于许多(可能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宗教、社会歧视和其他障碍仍然阻碍着性少数群体对自己性倾向的真正公开,过去几十年中有悖于主流规范之外,不断拓展的变化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因此,有必要对其原因进行整理研究:
(1)对人类心理学认识的进步以及二十世纪中在性吸引特点方面的研究。弗洛伊德、阿佛列·金赛、艾弗伦·胡克和其他学者的研究,从实证的角度揭示了人类性表现的多样性以及早期道德态度在某些程度上所依赖的关于性的二元论的不足。
(2)大众媒体以及电影、电视、广播和互联网通过其巨大的影响力向世界每一个角落空前详细地传播了各种性知识。人类对性的痴迷,产生了巨大的市场,因而人类性倾向的多样性也由此得到了广泛传播。人们的这种认识颠覆了宗教和其他教条对性少数人群性表现的谴责:即一小撮人心怀恶意地故意违背“自然秩序”。但这种谴责越来越没有市场,也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不能接受,因为我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并理解了自然通过多种形式体现于性事当中。理解和认识播下了接纳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