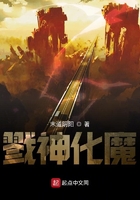憨子载着胡卤三一路狂奔,那拉车的“枣泥子”也果然是一匹良骏。它跃动着疾驰的马蹄,发出铿锵有力的哒哒声。胡卤三直觉得身后的乡野再不断的退缩而去,耳边的风生犹如滚滚的雷动。蜿蜒的小路顺着月光的朦胧错落有致的在田间折叠着,遒劲的林木或是三五成群,或是片片交融,犹如沉浸在月海中的精灵。渐渐的,那村落近了。一副高高的木质楼牌安静的矗立在村口的尽头,这楼牌建造虽是有些简陋,却也如那封卷的古籍玉墨,隐约的侧漏出特有的时代韵意。再看楼牌两侧,分别被几个苍劲有力的赤红大字装帧着……清风沃原人杰地,明月俊秀毓古村。胡卤三看着这游刃桀骜的笔法,犹似飞龙出水势入云天,又若日尽穹苍山河齐色。他眯着眼睛拍手道:好字,好字……“胡老师果然是个文化人,一眼就能辨别好坏来。”憨子听到他的叫好,便回头又道:“这楼牌可是个老古董喽,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谁都知道它的存在,可谁都讲不清它的来处。你别看它现在有些破败,曾经的时候那可气派着呢。”“那为啥成这样子了?”胡卤三不解的问道。“哎,村里也不知谁传的,都用成铺路的石子了。”说到此处,憨子不住的摇头叹息着。随着几声狗吠从暗处传来,车子渐渐抵进村落的深处。一栋栋整齐的房舍挤不断朝道路两侧挤压着,或是红色的砖瓦,或是白色的土坯,又或是青红色的混搭……安静的月光将它们统一的,不分类别的展现在自己的胸襟下。这,似乎让胡卤三想起了他的学生。随着车子的前行,一处宽大的胡同直入眼前而来。在胡同的尽头,一座高高的土坯院落开始清晰出它的轮廓来。“他爹回来了……”话音方落,那青黑色的院门后便走出一个妇人来。这妇人缚着青色的头巾,身着肥厚的棉袄正一脸茫然的朝着胡卤三直视而来。与憨子一样,她也体态壮硕,面容质朴,折起的皱纹爬满了额头,双手交叉的合拢在厚实的衣袖中。岁月将他们植根在这片土地上,村落让他们忘记了远方,应有的勤奋,耐劳则闪烁着人性的光芒,这便是典型的中国式农民。“这是镇上中学的胡老师,我们恰好在北地遇着,你说巧不巧?”憨子望着妇人乐呵呵的道。“哦,是胡老师呀,来,快里边坐吧,我今天刚刚炖了肉。”女主人的热情倒让胡卤三变得拘谨起来,他不好意思的点着头,紧随在憨子的身后。一盏昏黄的灯泡照射在客厅的圆桌上,一锅热气腾腾了猪肉正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很显然,这是为辛苦在外的男主人而特意准备的。“胡老师,有句话叫入乡随俗,我是一个粗人,这老娘们也不会太说话,你就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家……别作假,吃好就行。”憨子递来一副碗筷笑眯眯的道。胡卤三接过手中的碗筷,那眯起的小眼里流溢着满满的感动。此时,他只是不住的点头道谢。对于这家善良热情的乡邻来说,任何多余的言辞似乎都是画蛇添足,反而让气氛更加尴尬起来。憨子的老婆又重新系上围裙,回到厨房继续张罗着。然而,这突然到来的贵客显然超出了食材的储备,肉虽然很多,却没有其他菜蔬的陪衬,显得单调而突兀。那吃的尽兴的憨子也察觉到了饭桌上的尴尬,他对着走出厨房的妻子道:“让猫屎再去买些罐头和烟酒来。”妻子离去不久,便看到一个胖墩墩的少年走进客厅来。这少年一头精神的短发,正憨态可掬的眯着小眼道:“爹,我娘说你叫我。”他一边端着手中的面条,一边用筷子在碗里不停的撸动着。胡卤三仔细端详着这个叫猫屎的少年,才看到碗里是一大块发白的生猪油。“孩儿,快,快来给你胡老师问个好。”憨子一边招呼着,一边将儿子拉到近前道。猫屎傻愣愣的看着眼前的这位胡老师,一脸僵硬的抽动着嘴边的肌肉:“胡……老……师好。”“你这傻愣子,还不快给你胡老师倒酒,以后上学的事……还要多仰仗人家替咱多走动走动呢。”憨子望着儿子正要端起的酒壶,一脸兴奋的接着又道:“倒满,倒满……。”胡卤三一听,这才回过神来,不想这憨子会突然来了这么一出。这肉也吃了,酒也喝了,人情债算是欠下了……事已至此,胡卤三索性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他拍着憨子道:“孩子的事从长计议,从长计议……。”待猫屎走出客厅,又被母亲一把拉住道:“再去买些罐头烟酒来,你爹这可都是为了你!”猫屎接过母亲手中的票子,小跑着走出后院,直朝屋后的林间走去。
孟红旗坐在窗前的桌子上,开心的阅读着胡卤三的那本秘密日记。一束昏黄的灯光从头顶飞落而下,渐渐溢满在这栋温暖而又温馨的小房子里。夜风吹过窗棂的上的雕花,慢慢的被清凉的月光渗透着。恰如此时的孟红旗正随着词汇的修饰,句子的勾勒,内心的独白而一起融化在想象的世界里。“亲爱的花美,你可记得我们邂逅的那个午后。当一朵洁白的云飘过你的安静的窗,我便怦然着心跳的加速,被你的恬静浸透着思念的孤独。”——胡卤三笔。孟红旗继续翻阅着,又看到以下内容。“花间一步落雨下,柳叶沉沉蝉微鸣。卧虹彩翼三千里,一片痴心化七情。”——胡卤三《咏虹》。“桃花落枝上,粉露同蝶翅。相思遍于野,只是春不语。”——胡卤三《相思》。“你在干嘛呢?快点给我添点热水来。”小黑赤裸着上身,半蹲在一副大木桶里,他瑟瑟发抖的催促着。一缕缕腾起的雾气正随着肌肤的干涸而不断向屋顶攀爬着。孟红旗这才回过神来,他放下手中的本子,直向厨房跑去。方才兑了三五瓢热水,便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从屋外传来。“这么晚了,不会是喇叭花又来了吧!”小黑一脸惊慌的望着孟红旗道。“瞧你这没出息的德性,即便是喇叭花又怎样,你这光腚的还怕她那穿衣服的。再说,喇叭花会敲门吗!”言毕,孟红旗忙扔下手中的水瓢大声的问道:“谁呀……”“我……”门外有人轻轻答道。“你,你谁呀!”“猫屎……”听到猫屎两个字,那桶中的小黑猛的一个起身道:“好小子,正愁找他呢!红旗,让他进来。”随着一阵吱吱的开门声传来,那猫屎低头紧跟在孟红旗的身后,像是霜打得茄子般的无精打采的迈入屋里来。“哎呦,这不是孟猫屎吗。嘿……哪股妖风把你吹来了,难道是茅坑里的臭粪发了霉,熏出了你这个屎壳郎。”小黑一脸鄙视的望着他道。“小黑,你别生哥们的气。那喇叭花放出话,非要我向她磕头求饶,不然就打断我的腿。”猫屎哼了哼鼻子又道:“我迫不得已,就跑到外婆家里躲了几天……才回来。”“说吧,过来啥事,有事就说,没事就走。”小黑没好气的道。“我爹今天遇到了一个什么胡老师,让我过来拿点烟酒。”那猫屎话音刚落,却看一旁的孟红旗瞪着眼睛道:“哪个胡老师?是不是头发不多,个头不高的那个。”“是的,红旗,你咋知道的,他是不是过来找你的……我昨天听到孟凡天在喇叭里找你……说你……。”未等猫屎说完,只见小黑不耐烦的道:“别再这儿拌那和你无关的闷屁事,赶紧拿了东西走人……对了,一律现金交易,概不赊账。”“哎,哎,等等等。”孟红旗向小黑一边摆手识意,一边又拉住猫屎道:“猫屎,今天遇到我的事切忌不要声张出去。还有,一会儿我写张纸条给你,你只需这般这般……”言毕,便将一瓶橘子水偷偷的塞到猫屎的手里。那猫屎欣然接受,孟红旗将他送出门外,直到他提着东西消失在了夜色里。与此同时,那胡卤三正坐在饭桌前,与憨子喝得痛快起来。一道月色的朦胧,一声狗吠的低鸣,一场即将到来的师徒博弈就这样慢慢拉开在村庄的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