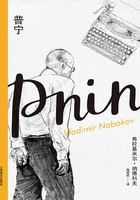她向我要的时候越来越多。我想不给,她就哀求。看着她可怜的样子,我就想:唉,又不是什么坏事,无非就是这么一点钱,只要她乖。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居然把给她钱,她的欲求,甚至她的乖张,都看成非原则的事。重要的是她要乖。现在想来,那是因为自己老想控制她,乖,就是被控制了。在控制之下,一切都是没关系的。我甚至还想出了自己的理论:重要的不是钱的问题,而是钱被怎样用?谁来用?
似乎也对。
她得了好处,就欢天喜地的,什么都肯表演。太可爱了!有时候,我会不自禁把她搂在怀里。我说:“给爸爸咬一下!”
我的牙齿好痒。她不肯。死也不肯。我就更要咬了,说:
“咬一下,给五毛!”
她仍然不肯,脸颊上的肉都吓得颤抖了。我就硬咬她。我真的想咬她,不是装模作样的,是真的咬。只有咬,才能充分表达我对她的爱。狠咬!把她咬破,咬得血淋淋,咬碎,连肉带骨头吞下去。当然我仍然不可能真咬,我舍不得。我只能竭力把握着强度,但常常会倐忽间就疯狂了,不小心就突破了尺度。我也感觉到危险,自己会把她咬伤,甚至咬死的。我控制不住自己。我只能在能控制住自己的最初时候,就忍住,只用恐怖的发声来吓唬她。动作也化成了硌,用下巴拱她的后脖子,硌她的脖子,硌她的腋窝,硌她的腰,硌她小脚掌,把她硌得哇哇大叫,痒死啦!我叫:
“你求饶!”
她就乖乖地求饶。
我又叫:“你喊‘救命’!”
她就喊:“救命!”
她喊“救命”跟真的似的,她也小题大做,吓得她母亲从厨房跑了出来。“吓死我啦!”妻子说。
妻子这么说时,脸上是欣慰的。我知道她是喜欢的。总比我真的打孩子让她欣慰吧。我不打孩子了,她也高兴。孩子懂事了,我为什么要打她?我又不是非要打人的恶人。家里充满了笑声。谁不喜欢家里温馨呢?
因为有了女儿,家里才温馨。我们只是女儿的附属。你为女儿而生,我也为女儿而活,吵架也经常是因为女儿的事,但分歧再大,最后都能修复。因为我们目标是一致的,我们都爱孩子,我们都要她好。作为父亲,我更是任务重大。孩子渐渐长大了,我还要为她做更实际的事,明白地说,我要为她攒家产。我要给她一切!她要什么我给她什么,多多给她,喂她,让她满足,甚至让她饱得要呕出来,这样外界诱惑对她就不会有吸引力。我在家里全给了她,我要把她关在家里爱。
学校里同事也纷纷在做生意,都说,那些没知识没文化的人,都比我们会赚钱,不相信我有文化反赚不过他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当老师,靠的是学生家长。弄紧俏物资来倒卖,倒化工原料,倒水泥,倒钢材……学校只有一台电话,在办公楼,电话机旁几乎每时每刻都站着人,都是联系生意的。好容易排上了,对方还要考虑一下回话。“好,我等您回话啊!”刚放下,电话铃又响了,马上接起。“喂,我是王老师,您考虑好了?怎样?喂,喂!哦,是找黄老师啊!”
叫黄老师。黄老师接电话。这边我就在边上等,只听黄老师在问:“我这里有二丁脂,你那里要不要?”
对方似乎不要。黄老师失望地放下电话,这边我悄悄朝他招手:
“黄老师,你有二丁脂?我这边要,多少价?”
教书没心思了。学校不高兴了,校长来警告。从校长室出来,感觉着众人的目光,也觉得害臊。毕竟当教师的,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可是又怎样呢?人要活,是最大的理由,这话在当时很有支持率,已经被普遍认同了。
“老婆女儿都养不活了,还怕什么?”我说。
恰好我班上有个学生,爷爷是南下干部,原来化工厅的领导,常常利用老关系批些紧俏物资,而且价低。我找到他。那个操北方话的老头倒挺爽快,但他的儿媳,我学生的母亲可不是吃素的,明里暗里,叽叽歪歪,什么老头子的关系也是钱呀,也来之不易呀,我明白了,她要从中提成。本来老头子那边已经赚了大头,到我这里利润就不多,我又不能直接联系到买主,也要通过人转手,赚得就更少了。这下半路上再来个吸血鬼。怪只怪,我自己没权力,只是个教书匠,只能靠学生家长。只得答应了人家。
可就是这样,还不敢怠慢了她的儿子。这小家伙,好像也知道我有求于他家,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不听我的话,还不敢批评他,还得拿班干部给他做。我觉得屈辱,为了挣一点钱,其实只是分点残羹剩饭,还得这么低三下四。
我真想不通,凭什么你们就能这样?紧俏物资是国家的,又不是你们私人的,你们凭什么占为己有?让大家凭本事竞争吧!但现实就是这样。中国就是这样,又不是美国。说是凭能力过好日子,只是空谈。我能理解,前些年为什么有人向美国总统里根写信,要求里根来主持中国。制度如此,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应该把它铲除!
有一次,我忍无可忍,批评了那小子。那小子居然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回嘴道:
“你还不是靠我爷爷?对我爷爷都会摇尾巴!”
是啊,我是在对他爷爷乃至他母亲摇尾乞怜。我为什么要那样?我这还当什么老师?我是教师,有知识,知识是有尊严的,我这还有什么尊严?我摔了他一耳光。
他们家马上冲到学校,大吵大闹。校长慌忙把我叫了去,又怕我跟他们直接撞上,就让我单独呆在另一间办公室里。不料那小子母亲发现了,冲过来。校长慌忙制止,她却说,要过来评理,他们家是讲道理的。
“抢得天下了,就会讲道理了?操!”我道。
那女人脸青了下来。“你这还是老师?操?”
“操!”
我又说。这下我确实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操的就是她!
她跺脚,哭了起来。她老公闻讯赶来。这家伙,长得一副高干子弟的模样,好像很了不起。但是现在,他老婆被我操了,他的气焰也该灭了。我很得意。这就是骂的好处,要不然,怎么会长期流传、屡试不爽?不料那家伙突然扑过来,一把揪住我的裤头,要解我的皮带。
“你操?你会操?我倒要看看你本钱有多大!”
他叫。我慌了,挣扎。我只能挣扎。也许我应该反击他,也扒他的裤子,但是我心虚了。我害怕自己的家伙暴露了。并不只是被扒光的羞耻,而是,我那个确实拿不出去。假如我拿得出去,亮出来就亮出来,流氓是流氓,我不是要操他老婆吗?亮出来正好操。我抗拒,我躲闪,死死抓住自己的皮带扣。我想我的样子狼狈极了。这是我的软处。幸亏他没说,你会操?也就操出个女儿来!
我恨哪!为什么我的家伙不争气!
也许正因为不行,才特别爱说这个词,才特别受用于这个词,从嘴上得到满足。越是不行,越爱骂“操”。
那家伙又说:“要是在战争年代,我让我爸拿枪毙了你!”
确实,他能做得到。我恨我没有枪。
我想是我的熊样,要成英雄却成了狗熊,让他们越加猖狂了。他们告到了教育局。我被处分了。
母亲知道了,埋怨我:“你呀!你有能耐当土匪,就拿枪当土匪去!没能耐,咱们就顺顺地躲着喝一口稀粥!”
母亲知道我的脾气。母亲也清楚,我没有能耐。但是我“顺”不来。
说是物价要飞涨了。大家都跑去抢购,什么都抢。妻子一个人在外面排队,回来时,连头发都被挤乱了。她索性绞短了头发。她都不像个女人了。我作为丈夫,我无能,我有愧于她。
北京闹了起来。我从《美国之音》听到的。我躲在家里,从嘈杂的电波中捕捉着每一个音,每个音都令我兴奋。“要给这些乌龟王八蛋算总帐了!”我叫。
妻子说:“瞧你那眼睛,贼眼似的,都闪绿光了!”
“我就是贼!”我说。
妻子她不能理解我的激动。即使告诉她,我们将会在平等的状况下挣钱了,她也未必能完全明白,因为她不是挣钱养家的人,不是父亲,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理解一个要给女儿人类全部财富的父亲的心。
当然别人更不能理解。在他们眼里,我也是这制度上的寄生虫。他们想象不到我的屈辱感。那天我跟我的大妹夫说起这,说起社会不平,他是火柴厂工人,他说:
“你还不满足?当老师,有学生家长门路……”
他大概猛然想起我刚吃了这个苦头,改口说:“即使不说学生家长,你们当老师的,工资也比我们高。”
“高个屁!”我反驳,“难道你没听说?‘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做茶叶蛋的’?”
“那有什么?”他说,“同样是上班,干活,人家做茶叶蛋的又是洗,又是煮,又是烧火,又是卖,出入风雨。你造原子弹的就舒舒服服坐着……”
简直是“文革”思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居然还这种思维。你说不彻底改变,行吗?我说:“你知道什么是知识的含金量吗?”
他说:“你也知道含金量呀?你为什么不用?换成我,有钱赚,让那小子说几句,怎么不行?人家有权,我们好歹可以喝点汤。”
“那你是,不是我!”我说,“知识是有尊严的!”
“所以嘛,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所以混不好!”
是吧,我混得不好,因为我有知识,我知道什么叫公平,民主、自由、平等。我既想挣钱,把生活搞好,又要尊严,讲究平等,所以我只能向往彻底的改变。
这世界很快就要改变了。苏联改变了,东欧改变了,没有理由偏偏我们这里不改变。北京越闹越厉害,报纸居然也报道了。这说明这场斗争大势已经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我得意。我承认其中也有幸运的得意,我走对路了,我走的路,不仅是我要走的,而且是大家要走的,而且是眼看要胜利的。我们学校也动起来了。我也在班上拿那个当官的爷爷为例子,愤怒声讨,我说这个社会是应该改变了,那些贪官污吏,都应该抓起来杀掉!把那小子整得哭哭啼啼。让你哭,让你哭!没人可怜你!黄河尚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意时?让火烧起来吧!哪怕把我也一起烧毁,我也心甘情愿。
可是,戒严了。
我记起了十三年前,难道又要发生?难道会镇压?不会的。他们是在否定了那年代的基础上,才得到政权合法性的。同事们都在议论,有的说会,有的说不会。我怎么也不相信。和他们争得脸红脖子粗。他们说我:
“你是个书呆子!”
我不是书呆子!我讨厌人家说我是书呆子!书呆子就是弱!虽然我又很自得自己是知识分子。也许不是自得,而是无奈,我已经是知识分子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我辩。
但是,开枪了。
我们没有枪。手无寸铁。
校长找我谈话,说我曾在班上说了不该说的话。“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你又不是不知道,政治这东西,怎么好去碰的?你怎么这么不成熟!”
是啊,我不应该不成熟,我好歹已经是有孩子的人了,我是一个父亲。
我进了学习班。学习,然后检讨。然后我被调到了教务处,打杂。我,“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天之骄子,国家“青黄不接”时期的人才,居然到了这种地步,这是什么世道?
我没有枪。手无寸铁。只能任人宰割,用你也罢,弃你也罢,就像女人。
“小平南巡”了。大家又开始做生意。十三亿中国人,十亿在经商。大家好像把一切给忘了。但我没有做。我不知道再做,是否会重蹈覆辙。仍然没有公正。现在只不过表面上抚慰抚慰百姓罢了,或者把大家注意力引向赚钱,也好像谁都可以赚钱了。
而且,我讨厌沆瀣一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