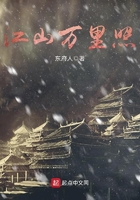彭辛沉默了。
添戈摇摇头微笑,笑容中有明显自嘲:“那时候我就觉得她的坦荡,我这一生都做不到。”顿了顿,又说:“没想到现在再被问起来,还是没有答案。”
彭辛安慰她:“其实很少有人能像她一样,要么是爱却不敢说,要么是敢说却不敢做。”说完,心情却渐渐低迷,也不知道这句话究竟在说给谁听。
但情绪终究沉淀下来,接下来直到结束,两人各自忙碌,除了必要的交集,再无他话。
然而每个人都有些心不在焉。送走彭辛,又简单整理了卫生,添戈去浴室泡澡。玫瑰精油的香气使人沉醉,添戈坐在一片热气中发呆。
她最近频频想念邵宗光,不知是不是因为刚刚确定关系,处在焦灼的热恋情绪中。但此时想的不是他在干什么,不是有没有按时吃饭,而是遥远过去里他递给自己一只抹茶味的甜筒,忽然说:“跟我在一起吧。”
清晨拉着当时的小男友在冰柜前吵吵嚷嚷,身边甚至有趁周末半天假连校服都来不及脱的来来往往的同学,瘦高男孩儿突然表白,吓得小姑娘差点掉头就跑。
被表白的添戈脸红脖子粗的沉默了,明明头顶浓荫蔽日,却被炙热的情绪烤的像只煮熟的虾。
她急切的在心里呼唤清晨快回来,可她正沉浸在甜蜜的快乐里,根本无法关照好友的情绪。
邵宗光从不知半途而废怎么写,耐心的等了一会儿,没听见任何回答,有些站不住了:“要不你考虑考虑——”他伸出手去,想像往常一样摸摸她的头。添戈却受惊般突然退了一步。
邵宗光一怔。
添戈生怕他再靠近自己,紧张的手心发汗,捏着衣角更退了两步。
邵宗光不懂,打着鼓的心情逐渐冷却。添戈怯生生地抬起头,细细弱弱的出声:“老师说,不能谈恋爱,要考、考大学……”
如此,邵宗光便懂了。他侧过头,沉默的看着不远处一棵茂盛的腊白杨,好一会儿,笑了笑:“知道了。”
结果接下来好几天,清晨都对她不冷不热,好不容易叫她相通是因为邵宗光,她又气急败坏的来找自己,非要去吃烧烤。骂着骂着哽咽了,捂着脑袋哭:“他还骗我什么都没有,回去就在房间不出来,他喜欢你,这事儿谁不知道!”
添戈嘴巴张了又张,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很久以前的记忆,但对她真的重要,所以还是记得很清楚。
说曹操曹操到,正在想邵宗光,邵宗光就打来了电话:
“干什么呢。”
“想事。”她闭上眼睛,电波里的声音熟悉温暖,不再是当年那个男孩儿。
“想什么?”
“……我在想,如果退回当年你跟我表白,我会不会答应。”
邵宗光以肉眼可见的时间陷入沉静,添戈耐心等待着,不一会儿,听见电话那头有椅子划开的声音,她猜他离开了桌子,或许走到了窗前。
“反思的怎么样?”
“你猜。”她笑,伸手撩身边的水。
邵宗光低声说:“如果还是当年的你,我想结果不会有什么改变。”
“我想会的。”添戈轻声说:“你说我拒绝了你,可我并没有说,我不愿意。”
一瞬电闪雷鸣,邵宗光忽然要紧牙关。
添戈表情廖远,盯着不断升腾水汽的天花板发呆。
心爱的男孩儿跟自己表白,她明明那么开心,晚上回去连楼梯都是一蹦一跳上去的,结果周末一过,刚到学校就听说迎夏追到了邵宗光。
“你说老师不准谈恋爱——”
“老师还说早上要吃一个鸡蛋,可我从来没有吃过……我不喜欢吃鸡蛋。”
可我喜欢你。
“……添戈。”邵宗光垂下头,眼眶刷的红了。
年少轻狂,做事,总少了些思量和张望。
第二天彭辛迟到了,晚上熬夜画画,结果正撞上班主任调课。本来只是象征性问他:“昨晚干嘛去了?”
其实这段时间以来任课老师已经对彭辛肖自强两个迷途知返的浪子颇有改观,只是走过场的例问,只要回答一句看书、写试卷任何与学习有关的事情就能过去偏偏他面无表情的说:“在画画。”
“画什么?中国地图?”班主任脸色有些变。
肖自强坐在座位上跟他拼命使眼色,彭辛却不冷不热的说:“画人,画女人,怎么着?犯法了?。”
教室里出奇的安静,班主任的脸色锅底一样黑:“去办公室。”
彭辛转身就走,却不是办公室方向。
班主任暴跳如雷。
正午,添戈忙完店里的事情,照例开始准备晚上的教学,虽然只是临时的老师,但她总是很认真,只是没想到等来肖自强,挺不好意思的,眼神又很着急,委婉问她:“能不能找你借点钱?”
彭辛被妈妈打了,出门时被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孩儿撞了,气急败坏直接追上去一顿爆踹,刚买的自行车报废了,要赔。
从他遮遮掩掩的话语里,添戈大概总结出这么个现状。
“我爸妈不给我钱,我手里一点存款都没有……”
“他怎么了?”
肖自强叹气,和盘托出:“他妈不准他走艺术生,说糟蹋钱。”
彭辛不听话被找了家长,老师冷嘲热讽,走艺术生,你有钱吗?
话说到这肖自强索性都说出来:“彭子家境不好,原先家里的钱都给爷爷奶奶治病了,去年两个老人走了,但是他爸又出了点事,把腿摔坏了,他妈省钱省的跟什么似的,就希望他能出息——”
添戈不解,问:“学画画不出息吗?”
“她们老一辈人眼里只有读书才出息,写写画画都是不务正业。”
“对了你注意点,彭辛他妈妈有点——”肖自强不好形容,支支吾吾做了几个动作,烦躁的直挠头发:“反正彭辛随意说了几句,学校怀疑他滚混,找家长了,你别让他妈妈找上——不是讲理的人,你招不住。”
“……好。”添戈应下,拿上手机,一副准备出门的架势:“他现在在哪?”
“医院打针,脚被自行车滑了,缝了几针,还要打破伤风。”
“去看看。”
“你去干什么?”
“那是我学生,还是我朋友,还是我的债务人。”添戈往外走:“你说我是不是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