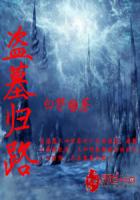果园的事情,谁都没有说。大家见了面,只是目视,不说话。有时,你斜视一下,或吐一口痰;有时他瞪一眼,剁一下脚。相互都保留着尺度和距离。
一天,马彪头上血淋淋的,一走一瘸,进来了。
贺红梅害怕了,赶紧把严青松找来,说:“严青松,你个子高,腿长,跑得快,赶紧回一趟马家咀村,把马彪家长叫来。”
严青松尻子一摆,像脱缰的野马,撒腿就跑。跑出贺红梅的视线,就开始了一步一步地走着,边走边数,数到九百九,错了,重新数。
马彪的父亲马亮娃正在麦场上碾场子。过几天就要收麦了,得提前拾掇麦场,把地面弄平整,弄瓷实。马亮娃已经给麦场淋了一层清水,正套着骡子,骡子后面拉着一个大大的碌碡,碌碡圆溜溜的,把骡子曳得气喘吁吁。
骡子转着圈圈,马亮娃也跟着骡子转圈圈。骡子在“嗬嗬”的叫,马亮娃就“嘚儿”“喔喔”的赶着。
严青松朝着转圈圈的马亮娃喊:“叔,出事了!”
“你说啥?”不远处的手扶拖拉机在轰隆,马亮娃听不清,只能“驭——”的一声,让骡子先停下,接着问:“啥事情?”
严青松上气不接下气,咽了口唾沫,说:“彪子哥,出事了。”
“咋,又打架了?”
“不是,头流血了。”
“晕了吗?”
“还能走路,清醒着哩。”
马亮娃一声“嘚儿起”,又让骡子跑了起来。转了两圈,又觉得不妥,就说:“是这,你给你婶子说,让你婶子先去,我还忙着哩。”
“好!”严青松很干脆。
“记得给你爸也打个招呼。算了,你先从你屋里头看着拿点药,我弄完这就来。”
麦场的土墙上已经刷上了“三夏大忙”和“防火防盗”的标语。严青松走过去,不远处的不知谁家的门房砖墙上也写着“颗粒归仓”和“龙口夺食”。严青松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他知道,麦子快熟了,忙假就快来了,终于可以不用上学了。
严青松给马彪的母亲传完话,马彪母亲借了邻居的加重自行车,火急火燎地就去学校了。马彪母亲也没有问严青松要不要捎他回去。严青松觉得不问正好,反正自己也不急着回学校,就顺着那条小路,一路游走,准备撵天黑刚刚赶到。贺红梅要是问起,就说“为了传消息,跑得脱水了”。脱水不脱水,只有他知道。他还知道,走了一趟马家咀,来回十五里路,走饿了,饿了就绕个道,到土整街上咥碗踅面。
土镇一横一竖,两条宽宽的街道。街道两旁打烧馍的、碾调货的、烙水煎包的、扯布的、挂肉的、涮下水的、卖当的、抓药的……林林总总,有时少了打烧馍的老梁,问起,说女子出嫁了,忙得没来;有时水煎包味道不正宗,一打听,才知道老姚少给工人钱了;有时会来几个耍猴的,一看,原来是外乡人在走江湖。但是,不管如何变化,始终都有几家卖踅面的摊位,无论有无集会,无论刮风下雨,蓝色帐篷,四角用木棍棍撑起,沿路方向挂着各自的招牌,字号老的,挂着“老店踅面”;自信的摊主就打着自己的名号;不太自信的,就以自己的村子命名;特别有心思的,就在招牌前再立一块醒目的板子,板子上叫村里的能行人写着踅面的来历及自家如何代代相传,把踅面文化发扬光大。不过,无论板子上的内容怎么变化,韩信黄河边木罂渡军必然会提到。
严青松一眼望过去,街上人山人海,就知道逢会了。逢上集会,烙水煎包的老姚就亲自出马了。严青松最喜欢蘸着踅面里面的大油辣子水水咥水煎包了,黄灿灿的,掉叶叶的牛肉水煎包,咬一口,酥软香脆,脆中带点皮,扯不断的感觉,扯不断就有了嚼头,严青松就喜欢这个嚼头,能一尻子坐在那,半天不起来,就着咸香咸香的踅面面汤,慢慢品尝。
今天,严青松趁着太阳还没有下山,要美美地享受一回。
严青松发现,虽然太阳快要落山了,但人们还没有回家的意思,两边的摊位也没有收摊的迹象,反倒是多了些卖扫帚簸箕的。一路走过去,什么木锨口袋,什么筛叉镰刀,什么刮板耙耙,收麦要用的家什齐刷刷地摆了一溜。殷勤的人已经和摊主讨价还价了,总是想方设法多拿几个工具少掏几分钱。
走过土镇,不远处黄亮亮一片,麦浪翻滚。头顶上几声“旋黄旋割”渐渐远去,严青松仰望高空,就跟着叫起了“旋黄旋割”,叫着叫着,又打起来口哨。严青松觉得,这次传话,值得。
马彪母亲在医院看到儿子血淋漓的头颅,就嚎啕大哭,扯着贺红梅问:“是谁?谁弄的?”
贺红梅说:“是在校外弄的。现在就看你的意思了,需要报警吗?”
马彪摸着头上的绷带,扶着床说:“不要!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处理。”
马亮娃来了,身上的汗衫也没来得及换,说:“忙忙的,快要收麦了,你弄下这事!”
其实,马彪只是受了点皮外伤,打人的人很有技术,仅仅让马彪的肌肉受损,骨头什么的好好的。
打人的人叫曹星星,是街面上的。起因很简单。马彪下午上体育课的时候,偷着溜出去了。溜出去,先美美地咥了一顿饭。咥的是老姚家的水饺包。吃完包子喝了汤,没事干,钻进了“星星录像厅”。本来没有什么事情,出门的时候,把门口正下棋的两个老汉的棋盘撞翻了。一个老汉就说了一句:“你看这娃,毛里毛躁的。”老汉说着就去拾棋子。也是该出事哩,马彪也撅起尻子准备去拾棋子。这一低头,和老汉来了个正面的亲密接触,一下子就把老汉怼倒了。本来说一句“对不起”也就没事了,可是,至此,马彪还没有说一句道歉的话。老汉就不高兴了,把棋子往桌子上一砸,说:“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老汉是街面人,在土镇这两条街道上混了一辈子,经常骂一些年轻的后生。搁在一般人身上,骂了就骂了,默默避开就行了。那天马彪看的是《古惑仔》,正热血沸腾的,就回了一句冯文道评价他老校长的话:“为老不尊!”冯文道的老校长好歹还算个文化人,没有跟冯文道计较,下棋老汉可是街霸曹星星的老爹。曹星星是什么人,土镇街上的人都晓得,曹星星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年轻人不晓得,上了年纪的都有所耳闻。
于是,这个当年敢拦马旅长轿子的人就说:“好娃哩,话要好好说;年轻人呢,要学好!”
这一切,让从远处走过来的曹星星看见了,也听见了。
曹星星上去就是一拳。曹星星比马彪还要矮一点,但壮实得很,胳膊上的肉瓷实,泛着疙瘩,后面跟着一个年轻的女人,曹星星就说:“今天,我媳妇在跟前哩,不想动你。”
马彪人高马大,一点都不怯火,也不知道对方是谁,就冷笑:“动我的人,还没有出生哩!”马彪还未掏出手奎,就被曹星星一脚撂翻。
马亮娃是知道曹星星的,就劝说:“你以后要学好,不要跟街面的人闹,咱闹不过!”
马彪不言传,他可能也明白,学校才是他的江湖。
后来,我才知道,张三是认识曹星星的。张三说:“老曹嘛,一看是白脸黄毛的家伙,就明白了,就打得更厉害了。”
张三又说:“老曹还给马彪撂了话,说,看你这碎怂就不是个好东西,以后把你那撮黄毛卷起,嫑欺负娃娃打老汉!”
马彪确实宁瓷不少了。安安静静一直挨到放忙假。
放忙假的前几天,我们比较兴奋。但我们不确定具体哪一天放。“旋黄旋割”的声音天天在教室前后,在操场,在路上萦绕飘荡,搅扰得我们没法听课。
马仁杰说:“我今年忙假,要拾一百斤麦子,换西瓜吃,换作业本。”
何晶晶就问:“一百斤,拾死你啊。”转眼,又问:“你爸同意?一百斤,都是你的?”
“我上次考得好啊!”马仁杰就得意了。
我们都开始盘算这个忙假怎么过,都希望班主任布置的作业和拾麦任务少一点。着急的人就旁敲侧击刘小佟:“小佟家肯定不着急收麦了,人家一家子都是吃商品粮的。”
刘小佟就急了,说:“胡说!”
他们套不出话,就换话题,说:“小佟人就肯定不拾麦穗的。”
刘小佟说:“今年忙假我在我外婆家过。”
我和张三兴奋得几乎尖叫。刘小佟的外婆家,就在我们村——贾家庄!
一个明晃晃的中午,没有一丝风,贺红梅终于走进了教室,庄严宣布:“放忙假了!”
她布置的任务什么的,我们都没有细听。
我们说:“刘小佟,帮我们记下。”
我们说:“何晶晶,快给我们记下。”
我们收拾着书包,打扫着卫生,唱着歌。我们甚至走到马彪和严青松的跟前,和他们握手道别。
马彪头上的伤已经好了,他吹着口哨,一脸的不在乎。
贺红梅在我们后面说:“哦,一群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