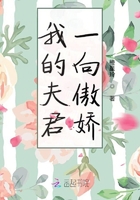“他买了我半生风月。”
正坐在他面前整理今天采访笔记的我反应极快:“您说的是陈魄陈先生吗?”
话刚出口,我才察觉到自己的唐突,这次上面好不容易才使这位松了口,答应今天关于戏剧文化传承方面的采访,哪能还不知足地询问教授的私事。
可是说出去的话哪有收回来的道理,我只能尴尬地补充:“陈教授,我没有要打探您隐私的意思,只是为了准备这次采访,才查了一点关于您........”
“是他。”
“什么?”
“你说的确实不错。”
陈教授倒是面色如常,甚至还对着我善意地笑了笑:“无事,我的那些往事二十年前就闹得满城风雨,说说倒也无妨”
气氛和缓了许多。
而我像是因为不经意之间撞破了天大的秘密一般,有些坐立难安,左手不自觉地捻了捻端放在我面前的笔记本。
坐在桌子的另一端陈教授端起了桌上的新沏的茶,吹了吹茶杯溢出来的热气,热气浸润了他的眉眼。
这时我才敢光明正大地打量面前这位曾名动京城的陈家公子,陈舟。
“丫头,来的时候没打听好,我啊,本名不姓陈。”
丫头这是我们当地人对晚辈的爱称。
听到陈教授叫我丫头,又因着这一天的相处,我便也大胆了许多:“是因为陈魄先生吗?”
他含着笑意微微颔首:“不错。”
三十年前
陈舟不叫陈舟,当时他是京城最大商户舟家独子,舟舟。
“当时”这两个字很有意思,它意味着往事不复返。
那日的太阳倒是喜人,年仅八岁的舟舟跟着管家的小儿子阿峰偷偷跑出府玩。因着舟舟是府里的独苗苗,夫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叫人跟着别出事。
舟舟一边嗦着三毛钱一个的奶油冰棍,一边神色认真地看着阿峰拿着用着吃剩的小棍儿挑着泥里面的蚯蚓:阿峰,它们为什么扭来扭去的呀?是因为害怕了吗?
阿峰抬起胳膊,不在意地胡撸了一把冒着热汗的脸,嘻嘻笑道:少爷,蚯蚓不过是个玩物,哪有什么害不害怕一说。
舟舟撇了撇嘴:阿峰,这样是不对的。
阿峰反问:那少爷告诉我是哪里不对了?
舟舟咬着冰棍,皱了皱眉,含含糊糊地也没答出个所以然来:反正,就是不对。
阿峰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小棍往土里一插,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少爷,我们回府吧
舟舟点了点头,将剩了没多少的冰塞进了嘴里,腮帮子用力一咬,“嘎嘣”:嘶,好幺。
阿峰似笑非笑地看着舟舟在一旁冰的连话都说不清的样子:少爷,慢点,不差这半刻。
说完忍不住伸手去摸了摸舟舟毛茸茸的头发。
舟舟不满道:阿峰,男子汉的头发是不可以随便乱摸的!
八岁的奶娃娃说话哪有什么威慑力,故意瞪大的眼睛,在阳光的折射下,可以清晰的看见自己,只有自己。
阿峰突然用手遮住了舟舟的眼睛:“丑死了,少爷。”
舟舟自生下来时就生的好看,接生的是阿峰的母亲,那日回来,母亲一脸笑意说个不停,手里还忍不住比划着奶娃娃的模样,用他们那里的土话讲,是“小少爷这模样青丝的很呐”,这点阿峰是知道的。
等舟舟再大一点,就喜欢跟着阿峰四处溜达,都是半大的少年郎了,自然不喜自己身后多了个娇娇嫩嫩的小家伙,终于一次,阿峰故意甩掉舟舟,玩得尽兴,阿峰傍晚回家时想。
进门时,不料,好脾气的父亲竟拿着棍子不留情面地一下又一下地打在了他的身上。母亲最终还是忍不住哭着护着,阿峰硬是没有吭声挨了一顿揍,事后母亲来给阿峰送药时,阿峰才知舟舟跟着他走丢了,一个人偷偷蹲在街上哭,幸好路过的孙家少爷看到了,赶忙送了过来。
阿峰嗤笑,这孙家少爷倒是真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