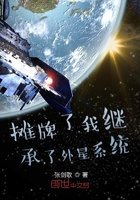但见那刺客动手行刺,厅内众人尽皆是看的众目睽睽,但距离如此之近,就算是江云卿都来不及打开“世界编译者”,其余人等又为之奈何?
眼见那匕首即将便要刺向楚王,只听见一阵空气爆裂与瓦片碎裂的声音,一支箭自房梁上射来,正中那伪作小僮的人的后脑,贯穿了他的颅骨,直直地钉死在了地上。
江云卿抬头一看,见房顶已是破开了一拳头大小的裂洞。那箭矢,竟是透过了房顶而穿射过来的!
一瞬间兔起鹘落,除了龙且、英布以及江云卿之外,其余人等甚至没能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台上似是有匕首的光芒闪起,而后便是一支力可摧墙的劲矢自房顶上射来,刹那之间,便取了那小僮性命,不由得一阵胆颤。
若是数米之间一箭射杀一个刺客,对于寻常武人来言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只是这隔着宫殿的屋盖,直接从房顶之上射穿屋檐,直中刺客后脑。光这劲力已非常人所能及,而发箭之人又是如何判断刺客方位与动作的,细思起来,更是令人毛骨悚然。无论是听声辨位也好,或是听息辨位也罢,按他的这等数米之外隔墙取人性命的功夫,实在是不知该如何让人抵挡才好。
那些史上有名的刺客,无论武功再超然,伎俩再出离,也要将刀刃架在人的脖子上,尚需以身犯险境,而这等隔着屋墙就直接把人射杀的手段,又怎么有方法去防范呢?
想到此节,江云卿不由得咽了一口唾沫,后背上已经开始直流冷汗,就连一直以乐天派著称的钟离昧在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之后也不禁两股战战。坐在一旁的英布被钟离昧的大腿抖到之后,也一反常态的没有对钟离昧恶语相向,只是用手默默按住钟离昧的大腿,仿佛在说:别再抖了,我也怕极了。
钟离昧一边抖着腿,一边颤巍巍地小声问向英布:“呐,这箭的力道,已经至少是神将级别的了吧。你和龙且,应该也能办到的吧?”
“如果你想找心理安慰的话,那我告诉你,我和龙且就是俩神将级中的水货,这一箭,”英布边回答边摇头,“无论是箭的力度还是准度,我们俩都做不到。”
这时,只听殿外一阵翻墙跳跃的声音,俄而,自门口走来了一位持弓的中年人,想必便是那刚才在房顶发箭之人了。
待他走进大殿中后,江云卿仔细观察了一番。那人生的矫健,眉目之间自带几分威严,穿一无袖贴身皮甲,双臂皆用白布裹着,但隆起的肌肉轮廓清晰可见。右臂提着一米长有余的弓,泛着银白色的金属光芒,弓弦呈金色,都不知道是什么材质。身后背一钢铸箭囊,里面整齐排列着他所用的箭矢,箭矢的尾羽都呈乳白色,也看不出来是什么样的家禽才会生如此洁白整齐的正羽。仔细端倪那箭身,竟浑身可透过光芒,是晶莹剔透的晶体,江云卿这才注意到,他的箭矢,包括适才射杀小僮的那一支,都应该是钻石所制的,钻石的莫氏硬度据最高级别的十级,也难怪适才那一箭有着摧枯拉朽之势。就不知在中国古代,究竟是怎么样的工艺,才能把钻石打造成箭矢模样。
那人进得殿内,向楚王行了一大礼,说:
“末将养由基,救驾来迟,损了宫殿屋檐,请王上责罚。”
原来如此,江云卿这才知晓,原来这便是第一个做到百步穿杨、箭术家的鼻祖、相传只需一箭便在两军阵列中取了敌方上将性命的“养一箭”养由基了。如果不算神话中射日的后羿的话,此人当算是民间传说中最为广为人知的箭手,今日见此人如此功夫,也是真当了得!
楚王刚从惊吓中回神过来,忙令周围的侍卫将那刺客的尸体收拾了去,对养由基说:
“怎么能责罚你,若非养卿,本王的性命便由此交代了。来人,给养卿赐座。”
待养由基入座后,大厅内一片寂然,大家都不敢出声,楚王环顾群臣,似是在观察众人脸色,最终将目光落在了一直一脸平静的孙叔敖身上:
“看来蔿子说的对啊,真没想到,敌人在郢都已经渗透到了这般田地。”
未及孙叔敖答话,只见一人慌忙出座,跪于地上,正是春申君黄歇:
“王上,这情报工作本由臣下来负责,今日如此之变,臣不求免去这死罪,只请命将城内的奸细与特务彻查清楚,再将自己的戴罪之命交由王上处决。”
江云卿见此人既英俊潇洒富有公子气概,又有如此担当,不由得向季布那低声夸赞了一声,季布听闻,却摇了摇头,小声说:
“春申君黄歇久居官场,自是老奸巨猾,这起行动的首要责任自然是在他,他却直接上来主动请命,一来是为了撇开嫌疑,二来如此认罪,楚王也不便严惩,三来主动请命,却是在试探楚王。”
“试探楚王?”江云卿疑惑地问。
“若是楚王准了他去彻查此事,那自然是还留有信任,若是让春申君不再插手,那便是对他起了疑心了。”
江云卿听了季布这一番解释,顿觉十分明了,也不由感慨:此人能位居战国四公子之名,也自是有其城府手段,刚才那一句话里竟有如此多的用意,要论自己则是实在做不得来的。又有几分好奇,又问:
“那你觉得楚王会怎么想?”
季布凝神思索了一会,答道:
“按照楚王的性子,怕是会表面不愿失了和气,准其去查,暗地里再派人盯梢或者同时调查吧。”
季布话音刚落,只见那楚王果然说:
“好。春申君果忠义果决之人,此事便交由你调查,查清之后,本王自不会因此事而责怪你。”
“是,臣定当肝脑涂地,以报王上之信任。”
江云卿经季布提点,现在看这两人如此这番一唱一和,暗忖这君王和臣子都不是好当的,原来那些宫斗、官场剧,也是有如此的讲究啊。
未及楚王原场,只见养由基突然又站出来说:
“王上,臣听得城内有骚乱。”
“骚乱?可是百姓之间的聚会游戏?”楚王问。
“似有兵器相交之声,还请王上当即调遣禁军,我自保护王上安全。”
众人正狐疑,反正大家都没听见什么骚乱声,不知是否该去信他,正犹豫间,一侍卫踉跄奔入殿内:
“禀大王,城内,城内四处都是叛军。”
众人大疑,楚王问:
“叛军,何来叛军?”
那侍卫答曰:
“不知晓,像是突然冒出来的一样,到处都是。装备是我军制式的。”
众人皆是一阵讶异神色。
楚王虽知事情紧急,但听闻侍卫的汇报后,还是不由得又问了一句:
“装备是我方制式,难道是我郢都军中作乱?”
“王上,如此突如其来,四方皆起,定是有所组织,无论是我军,还是别人偷了我军装备,怕是背后都有人谋。现今之计,应是速度令此间的诸位将军率军去城内镇压叛乱啊。”成得臣一边上奏,一边用粗大的右手按住腰间的宝剑,似乎是在表示只要楚王一声令下,便可出门杀敌。
“来不及了,”养由基眯着眼睛看着门口,默默搭了一支箭在自己的弓上,“他们已经杀入王宫了,不对,应该是王宫内也有他们的人。”
话音刚落,一支箭便朝着右边墙射去,穿过墙面,只听见一声惨叫。众人看去,见墙体的裂隙内流出了阵阵鲜血,又是一阵愕然。
“保护王上与诸位大臣!”
侍卫长一声大喊,殿内诸人也纷纷起身,将领们也各自拔出了自己的兵刃,但未及冲至门口,便见一干士兵已经袭杀了门口的守卫,直冲大殿而来。看他们的装备,确实是楚军制式,也难怪能不加通报地如此迅速地进入这楚国王宫。
养由基搭起长弓,飞身便是几箭,那箭矢一连贯穿几人方才停下,但敌军人数实在是太多,自门口鱼贯而入,光靠养由基一人之力焉能全部击杀。
龙且持了一柄长剑,翻身便与先行冲入殿内的敌军拼杀起来,一边血战,一边朗声说:
“诸位将军,今日我等就死战在此,务必保护王上与诸位大臣的安全。”
江云卿见状,也开了世界编译者五倍速度与力学半导体的能力,而后抽出自己佩剑砍杀过去。杀人这种事情江云卿并没有经历过,故而在击杀了第一个敌人时还是忍不住干呕了一下,但大敌当前,也顾不得这么多。又回忆起自己曾经玩的战阵冲杀类的虚拟现实游戏,便以此心理暗示自己,习惯后,一时间竟觉杀人如同砍瓜切菜,袭击的士兵中鲜有人能抵挡住自己一招半式,即便是偶尔遇见好手,不出五合也能削下对方头颅,便愈发觉得自信与顺手。
江云卿回头一看,发现诸人皆已与敌军缠斗在一起,钟离昧与季布等人围着楚王与诸位大臣结了一个圈,若是有漏网之鱼,便有他们料理。
“钟离昧,”江云卿于阵中寻不得那位最为潇洒的人的踪影,不由得着急地问了一句,“屈夫子呢?”
钟离昧刚刚刺死了一位敌兵之后,听得江云卿问询,用脑袋朝一个方位指了一指。
江云卿朝那个方向看去,只见一袭素衣,一柄寒光,翻斗在身着黑甲的士兵当中,用剑的方法也与龙且、英布这种久经于沙场之人也截然不同,一挑一划极度讲究招式变化,虽少了几分效率,但俯仰之间,俊逸非凡,举重若轻,只是看了几眼便觉如痴如醉,更为难得的是,相较于武将们的切、砍、剁、大卸八块,屈原杀人时大多只是用剑或在喉头,或在心口,或在足筋手脉轻轻一挑,尽中要害。这等打法只觉得优雅动人,浑不似在进行杀人这项粗鲁又残忍的运动,偶尔有鲜血滴溅在了屈原那雪白的袍子上,倒似艳梅开雪山、红日映云天一般,在屈夫子的流云剑影之下,竟别有一番浪漫。江云卿端倪良久,只是机械地砍杀着冲向自己的敌人,眼睛与注意力全在屈原那边,一时竟不由得看痴了。
心中暗叹着:
什么叫开浪漫主义先河,这他妈才叫开浪漫主义先河,何止是诗篇韵律,连杀人都如此的浪漫优雅。
江云卿一边痴痴地看,一边又痴痴地想那李太白诗中“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中的境地,相比于这屈夫子,怕又是另一番的恣意潇洒。
一个不注意之间,所击杀士兵身上溅出的一滩血水迎面洒来,江云卿心神未收,没来得及躲避,竟被直直地打在了脸上。
一股血腥之气瞬间渗入了江云卿的鼻息与齿缝之间,她急忙用手擦了擦脸上地鲜血。但不是不是闻了血息的缘故,一阵躁动开始从江云卿内心泛起,似是一只猛兽要在自己的身体内醒来,一个强大的意志要将自己撕裂,一时抬剑不稳,摔倒在地。
一旁血战的龙且见状,急忙抢过一步将江云卿抱在怀里:
“少将军!少将军!”
此时江云卿只是觉得自己的意识像是要炸裂一般,倒也浑身不痛不痒,只是感觉一阵狂躁以及意志的模糊。
“吃了它,你扶住他去别处歇息,这里由我来应付。”
江云卿模糊之中随声音看去,正是自己崇拜无比的屈夫子,他递给了也在一旁的英布一颗蜡黄色的药丸后,便转身离去。
英布拿了药丸,敲开了江云卿的牙关,和着宫内的酒水将药丸给她喂了下去,并与龙且一起抬了江云卿前往钟离昧等人所在的阵列。
江云卿被投了那药丸之后,只觉得一阵甘甜自口舌发出,直沁心肺,那狂暴之气也逐渐为一股宁静之息所替代,躁动不安的灵魂也逐渐安定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