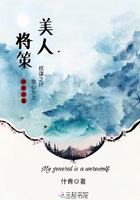终章
人在黑暗和安静的环境中能够更快入睡,因为白昼的光明太过刺眼、忙碌太过吵嚷、生活糟心事儿太多,解决不完,却又不得不面对,被动又无力。可黑夜不一样,既有夜黑风清,又有万籁俱寂,眼睛不必受光色的刺激,耳朵不必通晓八方,大脑不必运筹帷幄,四肢不必忙不过来。一张舒适的床,或者一个能躺下的沙发,足够容纳一个疲惫的灵魂,带来一场难得的安眠。黑色的世界里,众生平等,每个人都是瞎子,都看不清脑海里思维的运行,没有夜盲症,没有近远视,只有无尽的冰冷的漆黑。我们以一个让自己最舒服的姿势,或蜷缩,或舒展。躺在最习惯的空间,或许是简单温馨的房间,或许是单调统一的学校宿舍,总之,我们能放下对外界的防卫和戒备。卸下精致的妆容,从擦去眉毛的墨黑到清除嘴唇的红艳,从恢复发型的爽利到进行面部的清洁,回归到每天早晨醒来时候的样子。头部靠在枕头上,一点点地清空纠结盘错的思维,逐渐松弛紧绷的神经,放松有些麻木的肌肉,调整每一次的呼吸,尽可能地使呼气和吸气变慢,变得均匀而深长。闭上眼睛,彻底隔绝一切物体散发的微弱光亮,将这个感官的所有感知交还给黑夜。慢慢地,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一点点减缓,体温下降到三十五摄氏度——一个让人嗜睡的温度。意识模糊,最终在心理和生理的调试下沉沉睡去。
睡眠,有时候是逃避,逃避白昼所有不愿意直面的一切,失败、挫折、喧嚣、失望、虚假……逃避世界对所有追梦人的恶意,逃避他人对自己的否定,找一个只有自己的地方,做着属于自己的梦;有时候储备,顺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规律,给疲惫了一天的身体一个休憩的机会,同时也让渐趋枯竭的灵魂重新思考和丰盈,让不知所云的神思辽远旷达;有时候是依赖,就好像鱼儿之于水,鸟儿之于天空,花朵之于芳香;有时候是寄托,男人渴望在梦里找到自己的洛神、朱丽叶和白雪公主,女人希望偶遇心里的潘安、纪梵希和白衣少年,谁都知道那是虚幻的,并不真实,可望而不可即,但谁都愿意义无反顾地守护自己的白月光,哪怕是在梦里。片段而丰富的梦,顽固而不屈的执着。尽管第二天早晨醒来记不清楚,但意识仍在思维着,重复又重复。
网上有这样一句话:“当你梦到一个很久都没有见面的人,说明他正在遗忘你。”我们无法验证它的真伪,因为这种事情永远没有标准答案,愿者自会上钩,但我们可以理性地思考一下。当我你们梦到一个许久不见的人时,对方是否同时梦到你这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警示。与他(她),你还是记忆里的你,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们之间的点滴,乃至你的外表会一天天地模糊,然后记不起,最终忘记。而你,如果没有梦的提醒,也会逐渐遗忘那个在联系人列表里的人的身影。人类大脑的吸收能力很强,可以记住很多新东西,但同时也会飞速的清除陈旧的堆积不用的记忆。所以,你如果梦到,请问候一下,就一下,这很重要。
冬季的天色从树影婆娑、隐隐绰绰到万家灯火、昏黑一片,就是几分钟的事,而从长夜到明昼却长得难熬。间断的睡眠中,列车从河南贯穿湖北,也途经武汉——这个在不久后被全世界密切关注的城市,也是我又一次错过的梦想之地。记得去年九月份来的时候,水田里的水稻还没有抽穗,半年之后重新路过却碍于视线看不清田野,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风景,只有黑漆漆的一片。火车里的灯光被人性化地调整到昏暗的色调,车厢内也没有白天的嘈杂吵闹声,安静下来。陆续有人关闭刺眼的屏幕,合上了眼,我亦如此。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夜我睡得格外沉,格外长,但没有做梦,以至于我开始怀疑杯子里的浓咖啡的真实性。
醒来时火车已经驶进贵州境内,离终点站贵阳只剩下一个钟头的车程,十来公里,和近三千公里的旅程相比,已经很近了。对面的情侣早已不见,想是在之前的站点就下了车,现在应该到了家。新上来是两个中年男子,还在睡觉,也就没有搭上话。还有一个小时,这趟二十六小时的行程即将结束,窗外的风景早已不是北方阴沉单一的灰暗天穹和厚重冰雪,也不是长江平原望不透的黑夜,轨道两边是绵延的青山,青山之间是纵横的沟涧,随处可见接连的桥隧和星罗棋布的池塘坑坳,这些扑面而来的西南最为普通的景带来了一种乡土熟悉的情,虽说这不是我要抵达的终点,但这样的感觉依然让人觉得亲切。
中午十一点,火车抵达贵阳。由于另一趟车很快就要出发,所以在贵阳待的时间很短,以至于没有时间去车站外的商业街逛上一圈,也没有机会去贵阳人推荐的小吃市上喝点小酒,有些可惜。匆匆下车,出站,找了个能充电的面馆将就了一下,给肚子垫了垫底,给手机续了续命。随即又匆匆在前台取票,奔赴下一趟即将出发的火车,这一次,终点是目的地,我的目的地。中间没有多余的停歇,马不停蹄,嗒嗒不休,只是为了早一点出发,早一点达到。
十个小时,从中午到午夜,一个人,一个包,一趟旅程。看过城市里早已不存在的土坯房,泥瓦红墙,矗立在山坡之上,像个徐徐老矣却又心有不甘,倔强地反抗的老头;看过无数次出现在地理书上、我曾在此之上长大的红土地,生养着西南一带最优质的丑苹果的红土地,从蛮夷到如今从未褪色的红土地,在高原狂风中屹立不倒的红土地;看过乱石耸立,有碳酸钙构成的石灰石,还有更多叫不上名字、说不清成分、形容不来的石头,就好像镶嵌在裸露地皮上的珠钻,毫无规律地自由散落,配上偶尔从石缝中探出来的被风霜淬炼成黄红色的枯草,竟让人有种置身大漠荒原的感觉,这是比最纯粹颜料浸染出来的画作更令人震撼陶醉的风景;也看过云淡风轻,天穹在深蓝中透出一种摄人心魄的黑,又在朵朵云絮的衬托下酝酿出透灵的亮白,微风拂动,人心也跟着摇曳起来……心里涌现过无数次的画面一一浮现在眼前,一连串的简单名词,一连串算不上华丽的形容,一汪怎么也说不完的乡愁,此刻,我又回来了,我的灵魂回来了。
今天的天色暗得较晚,因为南方的冬天比北方白昼要长一些,天还亮。新冲的咖啡保持着温热,激动的心却愈加滚烫。我注视着火车离滇东北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一刻也不想错过。我呼气擦拭车窗久积的灰尘,睁大眼睛,看着向后行进的矮山,似乎只有昭鲁坝子才能将山地的高峻危耸,盆地的富饶,高原冬日的苍旷与辽远完美地概括,多一分,少一分,都不会如此独特。
不知道为什么,到站的时候眼角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已经许久没有流泪的我有些感慨,不是故事不感人,不是情歌不悲伤,也不是生活不无奈,只是年纪大啦,总觉得情歌有深意,故事可推敲,生活还有戏。只是这一刻,眼泪不争气,硬是没有被憋回去,于是昭通车站门口,一个人,一个包,哭得像个失恋的孩子,实则是个归乡的,本该开开心心的,漂泊的人。天空黑得宁静,手机里适时地飘来交通部门的短信,于是找到了感慨的由头,以此来遮掩丢人的泪珠。
三十八个小时,东北到西南,终于,到达了旅程的终点。
云南,我回来了!
2020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