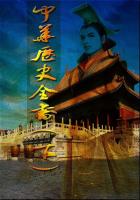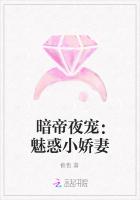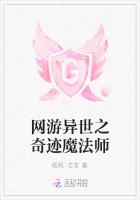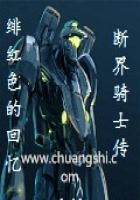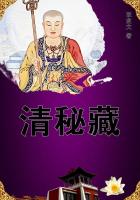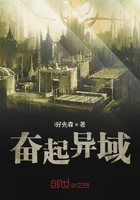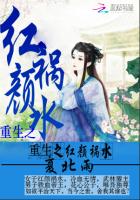提起汤显祖,人们自然会想起那出令人百转千回、柔肠寸断的《牡丹亭》,剧中的杜丽娘为情而死,又因情而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之中,演绎了一幕可歌可泣的人间情事。杜丽娘的身上,其实寄托了汤显祖太多的梦幻与理想。
汤显祖,字义仍,号海若,出生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从小就生长在王阳明心学的重镇——江西临川,十三岁时受教于泰州学派的罗汝芳,后来读到李贽的《焚书》,深表敬服,他称李贽为“畸人”,意思是奇特之人。这种求学的经历,使得他与心学有着扯不断的联系。他人生的前四十九年,热衷于仕途经济;后十七年则弃官归隐,潜心文学创作。汤显祖最著名的戏剧作品是被誉为“临川四梦”的《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与《邯郸记》,这四部代表作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
《牡丹亭》讲的是情事,这个“情”耗费了汤显祖一生的光阴去求索,他在情与法、情与理之间徘徊,到了晚年内心的情才彻底战胜了理。道学家讲“存天理、灭人欲”,情与理是对立的,理在情之上。汤显祖不否认情与理的对立关系,但他把情看得比理更重要。
《牡丹亭》的女主角是杜丽娘,她在梦境中和素不相识的青年男子柳梦梅幽会,尽情享受着男欢女爱的愉悦快感。但当她醒来时,才发觉这只不过是场春梦,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她忧郁而死。到了地狱,判官审讯之后发现她是因慕色不得而亡,怜悯之下,将她的灵魂放回人间寻找梦中人。当她的灵魂找到了柳梦梅并再次结合后,杜丽娘死而复生,最终和意中人结成夫妻。故事虽然只是虚构的,但汤显祖要传达给我们的显然是“情”的巨大力量。在《牡丹亭题词》中,他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在他的心目中,情是可以超越生死的伟大力量。据说有位道学先生看了《牡丹亭》后,问汤显祖:“你有如此的妙才,为什么不去讲学呢?”汤显祖回答说:“这就是我的讲学,你所谓的讲学讲的是道学,我讲的是情。”道学家将伦理纲常道德的“天理”置于“情”之上,汤显祖则认为世间总有情,人生的一切都无不是出于情、为了情。情和理虽然对立,但“情”应该有存在的权利,有宣泄的途径,相应的,世间男女也应该从“理”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理直气壮地抒发自己的真情。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即被赋予了强烈的个人生命感与自觉意识。她的梦里梦外,生生死死,莫不是为了一个“情”字,她的真情穿越梦幻,她的深情渗透地狱,她的至情征服人间。
汤显祖所提倡的情,不是一般的常人之情,而是纯真无邪、超乎生死的至情。他以为,情是人人生来具有的,情的产生不以外界环境与对象为诱因,而是缘自先天的对情的追求与渴望,源自于人的内心深处,当情达到极致的时候,便能超越个体,甚至无需语言便能打动人心。现实生活中两性关系的肉体结合,这也不是他所追求的永恒而普遍的情。在他看来,只有超越肉体的欲望与性关系,人的情与爱才会具有一种永恒而普遍的意义。那么,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至情”到底是什么呢?
明代社会是“天理”和“礼法”的天下,大臣动辄受廷杖,或充军或杀头,对老百姓的限制更严密。这不是一个“有情之天下”。汤显祖梦想中的情的世界是李白生活的盛唐时期。他认为,那个年代里君臣关系很和睦,在那种宽松自由的环境下,人的才情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如果把李白放在明代,他也只能俯首低眉,不复当年的豪气了。为了追求“情”的世界,汤显祖在当遂昌知县期间,曾做了一件让人惊讶的事情。有一年的除夕,他竟然放囚犯回家过年,让他们在正月初三时再返回牢中继续服刑;元宵节的时候,他又将囚犯放出监狱,到县城的一座桥上去观赏花灯。他对自己的行为颇为得意,认为实践着自己“至情天下”的主张,因为他认为即使是对囚犯,也该讲“情”,以“情”为重。但这种行为显然是草率而任性的,给不满者抓住了把柄,汤显祖差点因为此事而丢了官职。看来,他的“有情之天下”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而社会生活的现实告诉他,这样的理想是很难实现的。
现实的环境不可改变,汤显祖就纵情于戏曲创作,在他的笔下,无情之人变为有情,“有法之天下”变成“有情之天下”。在《南柯记》第二十四出《风谣》中,汤显祖就描绘了他的“有情之天下”:这是一个青山环绕、绿水枕碧、草木茂盛、鸟兽怡然、一派生机的世界。步入其中,井然有序,百姓的徭役轻、米谷足、老少相安,夫妻恩爱,官民之间平等和乐,四方道路通畅,商人来往其间,好一幅物阜人和、亲密友善的和睦景象,这是一个充满生机而人人自足的有情世界。
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中,《紫钗记》和《牡丹亭》都是反映男女爱情,《南柯记》和《邯郸记》则体现出具有宗教意味的出世文化内容。
《紫钗记》取材于唐人传奇小说《霍小玉传》,故事情节是这样的:卢太尉看上了青年才子李益的爱姬霍小玉,他对李益威逼利诱,迫使李益遗弃了霍小玉。李益后来中了状元,出任边塞军管,两人远隔数千里。霍小玉思念丈夫,每年的七夕节都会与丈夫在梦中相见,魂灵相依。最后李益归来,两人重新团圆。戏剧歌颂李益、霍小玉之间坚贞不渝的真挚爱情。
《南柯记》描写一个名叫淳于棼的人,醉倒在古槐树下,梦中进入大槐安国,被国王招为驸马,并成为南柯太守。在任上,他勤政爱民,深得百姓拥戴,在打退敌国的侵犯后,他被封为左丞相。在还朝途中,他的妻子因病去世。回朝后,他深得国王和王后的宠幸,后来因为淫乱宫廷而被逐出朝廷遣还人世。当淳于棼醒来时,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一场醉梦而已,那个大槐安国其实是古槐树下的一个蚁洞。作品的主旨是宣扬人生如梦的虚无,但对于南柯郡的描写却让我们看到了汤显祖心中那个有情天下的理想王国。
《邯郸记》也是取材自唐人传奇小说,同样是描绘一个梦。青年书生卢生在梦中与富家小姐崔氏成亲,又依靠崔家的钱财进行贿赂,从而中了状元。后来经受了各种磨难,屡建奇功,出将入相几十年,享尽荣华富贵。作品借卢生醉生梦死的经历反映了人生的虚无。但作品对人的贪欲、对统治集团内部尖锐的政治斗争和风云变幻的政治情势的描写入木三分,颇为深刻地描绘出宦海风波里的各种人情世态,正显示出汤显祖对虚伪官场敢恨敢憎的厌恶之情、对贪官污吏敢笑敢骂的鄙夷之情、对世间得不到真爱的女子们可悲可悯的恻隐之情。而这些也是“情”,是超越了男女诚挚爱情的多种情感,是对社会、对民生、对他人的“情”,这也是汤显祖所追求的“至情”的多维性体现。
汤显祖把自己对至情的追求寄托在文艺创作中,在一个虚幻的文字世界里表达着自己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对禁锢人情的“天理”的不屑,并构建起一个人人有情、用情温暖的世界,这是一个可以让浮躁的心灵得到宁静和慰藉的港湾。汤显祖的至情世界,让那些在传统礼法笼罩下冷冰冰的社会中挣扎的人感受到了一丝丝暖意。他最为得意的作品《牡丹亭》在问世之初,便以其“至情”感动了世人,同时,作品所揭示出来的人在现实中的无奈困境也引起了时人的共鸣。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曾说过,《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势头大大盖过了《西厢记》,几乎令《西厢记》剧本减价。据传,娄江有个女子名叫俞二娘,在读《牡丹亭》后,不禁深有所感,自伤身世,自知在现实中无法追寻真挚爱情,整日悲伤愁苦,十七岁便抑郁而亡。这无疑是困于残酷现实中,因不堪正常的情感需求和人性遭受压抑而断送性命的又一个“杜丽娘”。
还有一个名叫冯小青的才女,是万历时人,生于扬州,父亲早亡。小青聪慧灵秀,风姿绰约,又精通音律诗赋。长至十六岁时,其母贪图巨额聘金,将她嫁给杭州的一个富豪公子冯云将做妾。冯云将性格憨鲁,冯妻奇妒,小青曲意侍奉,却终不相容,被冯妻幽禁于西湖孤山中的小屋,其夫亦漠然不顾。小青的生活几乎与世隔绝,由此幽愤凄怨,俱托之于诗词,因孤独愁闷,遂常常顾影自怜,后世著名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经过研究,认为她这是因为压抑而导致的性心理变态,患的是一种“影恋”的心理疾病,有自恋的倾向。小青后来患了肺病,拒药绝食。临死前,她将自己的画像供于榻前,焚香设酒以奠之,抚几哀泣,吐血而亡,年仅十八岁。她曾写下一首数百年来为人传唱的绝句:
冷雨幽窗不可听,
挑灯闲看《牡丹亭》。
人间亦有痴于我,
岂独伤心是小青。
片言只语间,我们依稀可以看见,一个孤独的女子在四顾悄然、冷雨敲窗的深夜,百无聊赖中挑灯捧读《牡丹亭》,感怀世间真情的难觅,不禁以泪洗面的悲伤模样。这是一个沉浸在浪漫文学作品中寻求心灵安慰的女子,这样的伤心女子又“岂独”小青一人呢?许多女子的悲伤与如花生命的凋零,正是对当时严酷压抑人性的理学禁欲思想及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强烈控诉。《牡丹亭》对她们而言,无异于一部知音书,而汤显祖正是反映这一时代心声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