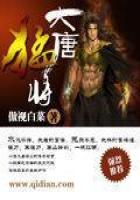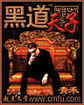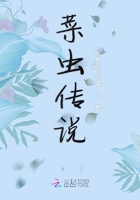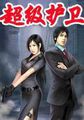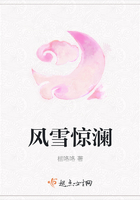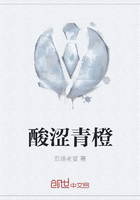商业在明代中叶得到长足的发展,不受商业影响的偏僻地区变得寥寥无几,商人的地位也随着他们财富的增长而逐渐升高。明中期后,商人逐渐成为一股非常活跃的社会力量,这样一个群体面对充斥着烟花脂粉、如云美妓的香艳青楼世界时,又有怎样的一番行为态度呢?我们就以足迹遍天下的徽州商人为例来看个究竟吧。
徽州商人是明清时期最为有名的商人集团之一,与之齐名的要数山西的晋商。所谓徽商,是指以新安江流域为中心的明清安徽徽州府的商人,从地域上看,这个地区属于贫瘠的山区,山多田少,因种地无以生存,必须另谋他路。这种生存条件劣势造就了这一地区的男子多出外经商的历史传统。
根据徽州地区的俗例,男子一到十六岁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因此,徽州男子一般十一二岁就要完婚,然后外出经商。俗话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徽商足迹几乎踏遍天下,有的一走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回归故里,有的“黑头直到白头回”。著名学者、徽州人胡适也曾回忆说,徽州当地有“一世夫妻二年半”的俗谚,讲的就是徽商外出经商、夫妻聚少离多的情形。
成年男子多年在外闯荡,远离妻子,难免会有生理上的需要,而徽商大多资财丰厚,故在娶妾、宿妓方面,往往不惜挥金如土。时人形容说,徽州人有个怪脾气,一辈子只在乌纱帽红绣鞋这两件事上,不争银子,最是舍得花钱,其余诸事就吝啬得很了。所谓“乌纱帽”“红绣鞋”,前者指的是仕途,后者指的则是美妾名妓。明人谢肇淛在《五杂组》中也说,当时天下最富有者,江南要数徽商,北方则推晋商。徽商在衣食住行上甚为节俭,就是在娶妾、宿妓、争讼三事上挥金如土。
徽商舍财狎妓的情况在明代的戏剧、小说中有非常生动的表现。《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明代通俗小说家冯梦龙撰写的著名短篇小说,可谓千古绝唱。杜十娘本是一位青楼女子,与忠厚的李甲相恋,杜十娘自出私房钱赎身从良。本是一段好姻缘,偏偏遇上了一个名叫孙富的徽州商人,他家资丰厚,是个盐商,生性风流,向来流连青楼,追逐红粉,挥金如土。待他见得“国色天香”的杜十娘,便拿出千两银子,欲从李甲手中买下杜十娘为妾,最终造成了杜十娘悲愤投江的悲剧。作者正是基于徽商在狎妓这一风流事上挥金如土的特点,塑造出了徽商孙富这一人物形象。
随着商贾势力进入青楼和奢靡逐利的社会风气影响日益深远,金钱至上的观念也逐渐渗透于妓女对客人的选择和态度上。明代的青楼女子,尤其是色艺俱佳的名妓,往往认为商人不够风雅俊儒,也不懂得怜香惜玉,所以在选择客人时,总是最愿意交结那些名士文人,她们可能宁愿接纳风流倜傥的寒士,也不愿招揽富商大贾,这在很多小说作品中都有体现。名妓钦慕寒士的才情或气节,钟情于他们,而鄙夷那些商贾之流,比如冯梦龙笔下的杜十娘。但是,明代中叶以后,商人财富的不断积累和地位的逐渐提高,也使得青楼娼妓对于商贾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北京歌妓刘凤台,艳名冠绝一时,与很多入京应试的举人相好,最后却委身于福建商人林尚炅。明人张瀚也说过,随着商贾逐渐过上锦衣玉食的优裕生活,诸妓们也争相取悦商人。那些名妓们,在从良问题上,也出现了更加务实的选择和拜金主义的倾向,毕竟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还是要比很多贫寒的读书人更加有能力帮助妓女们赎身从良。
徽商离家在外,过着流连青楼、沉湎酒色、怀拥美妓的生活时,他们家中的妻子却过着俭朴度日、独守空房、苦盼夫归的辛酸生活。徽商大多年少时成婚,婚后就只身外出经商,将年轻的妻子留在家中。因为徽州地区田地贫瘠,生活困难,这些妻子们大多非常勤俭,含辛茹苦抚养子女、孝顺公婆。她们的情感世界非常空虚寂寞,却只能恪守妇道,过着与守节寡妇相似的生活。《歙事闲谭》中有一个关于徽商妇记岁珠的故事,颇能说明问题。故事中的徽商在娶新妇刚两个月时就外出经商,商妇在家独守空房,以刺绣为生,艰难度日。她每年都会积攒一点余钱,买颗珠子,用来标记丈夫离家有多少岁月了,她称这些珠子为“泪珠”,每颗珠子就代表着商妇每年中日日夜夜盼望夫归的那些辛酸眼泪。待商人回家来,商妇已去世有两年了。其夫打开妻子的棺柩,看见妻子积攒起来的珠子已有二十余颗,象征着这位商妇凄凉的一生。所以,在徽州地区现在还有这样的歌谣:“悔呀悔,悔不该嫁给出门郎,三年两头守空房。图什么高楼房,贪什么大厅堂,夜夜孤身睡空床。早知今日千般苦,宁愿嫁给种田郎,日在田里夜坐房,日陪公婆堂前坐,夜伴郎君上花床”,可谓唱出了徽州商妇们的心声。徽商的冶游青楼、纵情声色与商人妇的独守空房、寂寞凄凉是一个鲜明的对照,也正浓缩了传统社会中男女两性在精神和生理需求上的不同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