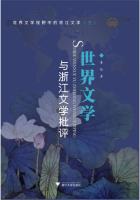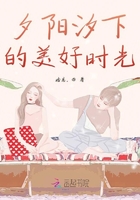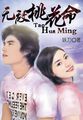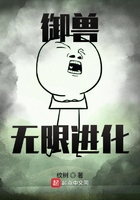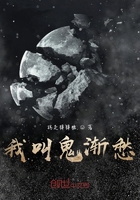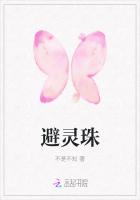张静
我一直相信眼缘,就像我第一次走进万邦书城时的那种感觉。记得好像是个冬天吧,很忙,很累,刚歇下来,在那里工作的学生打来电话说,到了一批新书,我若想看看,周末赶紧过去。
那个时候,学生在万邦书吧的前台办理会员和借阅手续,我可以随意挑几本书拿到最里面的书吧中,充分享受书吧里宽敞明亮的空间和幽静娴雅的氛围。
当时的书吧有三间。其中进门右手边的一小间是藏书,密密麻麻摆满了各类书籍;中间门厅处搁置了四个原木书桌和四把藤椅,算是接待会员的地儿。再往里,就是较大的一间了,进去,青色带釉光的地板一尘不染,象牙白的沙发散落其中,靠墙的角落里,几只一人高的青花瓷瓶上悠然可见清明上河图中烟雨朦胧的景致,几排沙发的空隙处用雕花的屏风隔开,屏风上,是苍劲老道的书法。人刚一落座,立马有漂亮勤快的女导购上前来沏好茶,茶香墨香交织在一起,令人有怦然心动的感觉。
那一瞬间,我便喜欢上了那里。加上那会儿,孩子刚上小学,周末要经常到市区学英语和围棋,在孩子跟着老师两个钟头的学习时间里,我会信步万邦,翻翻书,喝一杯淡淡的菊花茶,听几首书吧里缓缓响起蔡琴的《渡口》《被遗忘的时光》等歌曲,墨香徐徐靠近,歌声缓缓飘远,宛如深寒的黄昏里闪烁在天边的那一抹柔和的光亮。
与万邦相遇的最初日子里,我读书很随性,更谈不上写作,充其量只是偶尔记录一下自己生活的点滴和感悟而已。印象里,非常喜欢书吧里恰到好处的氛围,记得有一回来翻陈丹燕的新书,读她写外滩路、黄昏中的咖啡馆、悬铃木的老街与巧克力派,读到感觉眼睛疲倦了,掩上书,闭目聆听书吧里流淌的音乐声。有时候是风笛,似有风声,吹皱一池春水;有时候是口琴,音色绵长里带来稻梗,或者无花果的香;更多时候是钢琴的轻浅淡泊,如止水般的宁静……
万邦书城就这样走进我的生活,成为我闲暇时释放疲惫和缓解压力的一处心灵港湾。在那里,我读了很多喜欢的书,比如舒飞廉《飞廉的村庄》,一本怀旧思乡的书,读来温暖亲切;后读《华丽一杯凉》,钱红丽著,文辞犀利,又不乏温润柔软,颇有张爱玲的遗风;比如读《我打不赢爱情》,和菜头著,恣意狂放,嬉笑怒骂,令人惊叹;读车前子的《品园》,文字像氤氲着一股水气,湿润、清冽。苏州园林的雅韵与幽微在他笔下如水墨画般渐次展开,一幅一幅让人慢慢沉醉;而辛丰年、严锋父子的合集《和而不同》是和儿子一起读的。我告诉他,辛丰年擅长写音乐随笔,这本书却是乐评之外的文章,大多是谈历史,用词精雕细琢,同样是读书笔记,严锋则偏重于文学性,感性,自然。相比之下,比较偏爱严锋的《好书》《好看》《好音》,曾一读再读,爱不释手。
一晃几年过去了,某日,我又来这里,意外读到和我暌违几年的迟子健,这个常居北京的女作家,我曾经深深迷恋,尤喜其沉静温暖的笔触。当看到淡黄色的干净书架上她新出的《亲亲土豆》《北极村童话》等时,欢喜和兴奋之情不言而喻,还有她写给已逝丈夫的文字,心动意暖,情深义重,读得人眼眶濡湿……这些难以忘怀的精神大餐和享受,是我自食其力的艰苦岁月里一叠又一叠的美好回忆。完全可以说,在万邦浩瀚如烟的藏书里,我与这座城市日渐亲近起来,我依然记得每一个晨曦与暮霭,每一次迷茫与失意,是这里一本本飘散着睿智、浸透着情感、洗涤着思想的书籍,以它们极其盛大的滋养与润泽安放了我一颗漂泊的心,我将自己浸泡在其中,目光趋渐平和,内心趋渐丰盈与强大。
之后,孩子上了高中,琐事缠身,去万邦读书的时候自然少了很多,偶尔去,也是漫漫暑期和寒假,会抽出整整一个下午,安静坐到那里,尽情体验阅读和书香带给我的诗意栖居。比如漫卷一册典籍,便可徜徉于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触摸沧桑厚重的文化跫音;隔着油墨的馨香同大师对话,沐智者雨露,一份来自心底的澄明与豁然油然而生;再比如,溽热夏日,静居书吧,一杯清茶,几缕书香,浮躁喧嚣不再,人亦清凉如水;漫漫冬日,雪落簌簌,红泥小炉,一帧泛黄的线装书,便是一个人的天荒地老。更何况,我本凡尘之人,身居繁华旖旎的都市,总有一些心绪无处安放,也总有一些浮躁和空虚填满身心,可只要我的脚步踏进这里,总会在墨香深处,找到属于身体和心灵的一条出口,一份慰藉,我甚至不止一次给友人推荐,来万邦吧,读书吧,即便你足不出户,但照样可以从这里、从墨迹里,抵达千山万水、芳草萋萋、红尘万丈,这种感觉是美妙的,惬意的。
如今,万邦旧貌换新颜,以前的沙发和屏风被拆掉了,整个书吧青砖铺地,字画满墙,厅堂中间一对石狮左右相望,像是要望穿书香里描摹不尽的人间百态,或者诉说不完的前世今生,置身其中,依旧古朴悠然,依旧翰墨生香。让人更为欣喜的是,在万邦,时不时地,会有小城的文友们的新书发布会、品读会、诗文朗诵会,以及前辈们的文学主题讲座,我由此结识了很多文字路上的良师益友,以书为媒,以文会友,奇文共赏,博采众长。总而言之,与万邦结缘的日子,犹如沐浴鸟语花香,阳光清风。并且,正是因为有了万邦一年又一年的墨香熏染,我平淡清宁的中年日子竟也活色生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