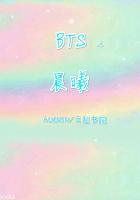杨海亮
妻子约我去书店,说给女儿买几本书,什么《弟子规》《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读物。
我没有反对。
前几天,朋友富兄在他的微信里转发了一条微信,说是青岛一个四岁的娃娃已经能读《千家诗》,已经认识三千多个汉字,还煞有介事地表示“虽然我不知道传统文化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
对于这样的“诗词萌娃”,或者如撒贝宁说的“最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我倒是不感新鲜。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所谓的天才、神童,只是禀赋殊异而已。据富兄所言,他所在的小区也有一个小孩,区区八岁年纪,已经读了不少古籍,如《易经》《道德经》《黄帝内经》等;也背了不少的诗词,像白居易的《长恨歌》,八百余言,这“恨”确实够“长”,那小孩花上几日,也一字不落记住了。
富兄说,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可同时进行,也可分个先后。我深以为然。让孩子陶醉在诗词的韵律中,浸染在书香的氛围里,总比一天到晚捧着个手机、盯着个电视要好得多吧?
那么,让小孩大段大部地背诵经典名著,究竟有没有意义?
我想,大概还是有的。
我出生在乡下农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小时候没有人要求我或指导我背诵什么唐诗宋词。我所背的都是语文课本上有的,老师说应知应会的,期末考试要考的。对于那些诗文名句,要么全然不懂,要么似懂非懂。哪怕上了中学,念了大学,也还是这般情状。不过,很多文句,一旦记住了,倒是不能忘了。
有一首数字歌:“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从一到十,一气呵成,简单地勾勒出一幅乡村田园风光。几十年过去了,这还是我最喜欢的数字诗。
又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从小就喜欢,没有理由地、始终如一地喜欢。
再如,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意为“处在忧虑祸患可以使人或国家生存,处于安逸享乐可以使人或国家消亡”。八个字,很简单,很深刻,要体悟透彻,怕是再多的经历也是不够的。于我,是深受了它的影响。
换作他人,一生当中,遇到好的句子、好的篇什,击中心坎、抚慰心伤、启迪心智、伴随新路……怕也是数见不鲜。
比方说,一名女记者,知道了朱光潜的座右铭——“此身、此时、此地”。从此,就记住了,爱上了。她说,“此身”,是说凡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绝不推诿给别人;“此时”,是说凡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绝不推延到将来;“此地”,是说凡此地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绝不等待想象中更好的境地。
比方说,一名公务员,很喜欢读书。每晚临睡前,都要翻上几页。他很喜欢陈公博死前的绝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是啊,明月岂能常圆?为人处世应知朔望盈晦之道。
再比如,一名年轻教师,她买的最贵的书是《胡适四十》。说“最贵”,是因为页数少、留白多,且原价买的。年轻教师爱画也爱花,却也格外欣赏胡适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如果胡适不介意的话,她似乎也可以对别人说:“瞧,这就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好诗好词,好文好句,字字珠玑,句句金玉。不要分难易,不要管长短,只要从头到尾,一字一句读下去,背起来便是。这如同练字练画、练拳练舞,记得多了,背得多了,不知不觉中便成了自己的知识、学识与见识。
当然,好文好句好好记,是愉快地记忆,轻松地记,而不是死记,不是硬记。一件事情,如果勉强,还过分勉强,不能说没有好的果子,但付出的代价往往太多太大,并不可取。
末了,说说我家女儿。她快六岁了,能够记诵的好诗好文,有《鹅》,有《元日》,有《山行》,有《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还有《如果我是一片雪花》,里面一句“我愿飘落到妈妈的脸上,亲亲她,亲亲她,然后就快乐地融化”,连我也禁不住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