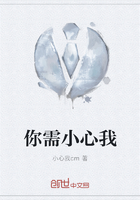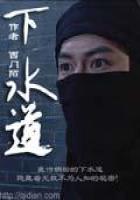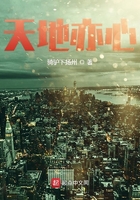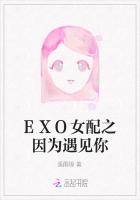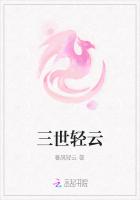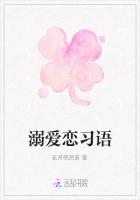小儿心思无人知,只是纸上徐徐来。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梦中行。
“喜欢是什么?”
“喜欢就是不好意思接近,所以一再远离”
“喜欢就是迫不及待亲近,所以一再靠近”
“喜欢是什么?喜欢是什么?”
“他冷静自持、他淡定沉稳、他学习优秀,但是那是喜欢吗?”
我一再分析利弊,他始终没有飞出我的条条框框。儿女心思扼杀在梦乡,少年意气放飞出围墙。
“喜欢太难,只想欢喜地长大!”
咿咿呀呀——咿呀——床板咿呀作响,梦里不是梦中人。
周周复始,去医院看过奶奶又回家。
回到老屋。墙上的坑坑洼洼还在,童年时被逼着站墙角反思的小可怜似乎还在那儿傻傻地立着,戳戳含着稻谷壳的墙,对着它嘀咕一番。在风吹日晒下,它瘦弱的身子却从每个小孩子的倾诉中变得厚实了许多。
这是文心对于墙的记忆。
每逢新年,文心会在那个墙角根儿点燃爆竹,期待着能炸出一个巨大的洞,一个时间的洞。在那个洞里,它从风雨中走来,颤颤巍巍的,风声时而发出吼声,恐吓着它瘦削的躯体。她曾无意中看过一眼,它仿佛就要倒了。
但在下一个晴天到来的时候,它又复活了,像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家,披着满身风雨,浸润着一身沧桑感,但那个黑黢黢的烟囱还呼呼地冒着热气,宣示着它的活力与生命。
老屋对面有一棵很大的桑树,绿莹莹的嫩叶在养蚕人看来格外喜人。一条条乳白的小蚕爬上簸箕,卧在那一丛绿叶之间,畅快淋漓地品味人间最美风味,最后吐出细丝回报着农家的馈赠。
小时候她还会爬上去,慢慢地将屁股挪上去安置好,手紧紧地抓住青白色的枝干,它无奈的抖抖叶子,稳妥地拖住她滑稽的身体。
而在那棵被欺压得驼着背的桑树上面,她看到了一个奇妙的世界,一个谜一样的老屋。门前青黑色的池塘里,惨淡的月光和水光摇着,摇着那老屋,残只碎影。那土黄的墙在水光与夜色的映衬下朦胧得像一面铜镜。
初中过着寄宿生活,周末回到那间老屋的时候,她又遛进了那片田野。
那片田野在冬天俨然是没什么生气的,唯有荷塘边妈妈种的一片月季花还开着,花骨朵里还含着雪,鱼也在池塘里簌簌发抖。此刻,孤高的月亮显得尤为亮堂,明晃晃的照进了她的眼里,心里。
抖掉一身冷气急忙钻进那老屋,一碗青菜面条加上几块加餐的牛肉,热气迷蒙了双眼。吃饱喝足,爸爸还得絮叨几番,拉拉家常。
说到这老屋的历史,文明又是停不下嘴了,一撮面条掺着一句话,边吃着还笑了起来,文心顿觉碗里的牛肉还不比他嘴里吐出来的话儿更有滋味儿。
在氤氲的热气中,她察觉到他停顿了一下,又低下头埋进碗里吸着面条。呼哧呼哧的还夹杂着几句“不说了,不说了......”
文心怎么能依着他,还得追着他问。
老屋是在他十八岁时诞生的。爷爷去世得早,留下“虚张声势”的奶奶和几个兄弟姐妹相依为命。身为计分员的爷爷一死,村里的流言就像夏天乱飞的蛾一样,还得在黑暗的时候扑上你的脸,钻进你的耳朵里。
“这家人怕是不行咯!”建一所新房仿佛就成了父亲证明自己的第一个使命。
家里的顶梁柱垮了,犹如虫蛀了般,挡不住风雨的侵袭和谣言的侵扰。父亲要建一所新房,一所抵抗所有流言的新房,那个房子的门面要大,裱着大写的“自尊”二字。
两层小土楼建了起来,18岁的父亲和15岁的姑姑磨出了岁月的茧子,挑着一砖一瓦将那座尊严的圣殿建了起来。
土黄色的墙像是一张会说话的照片,那上面似乎还留着父亲手指甲里钻出的血珠子。老屋高高的门楣上还闪着玉米的金光,凹凸的墙面里夹杂着稻壳的芳香,丰收的硕果更是家中值得炫耀的资本。
父母一代的童年与文心犯错站墙根的童年好像重合到了一起,都与那墙,那老屋有着血脉般的联系。
如今她很少去爬树了,也听腻了父亲一遍遍如数家珍似的故事。
“想啥子?听到妈妈在问你没得?读的书都吞到肚儿里去了?”王小强叫了几声。
“啊?我晓得!是要马上月考了,这次考完就是期末考试了!”回忆里的人还能保持着对现实的沟通。
“哦哦幺儿乖!好好学习,这次好好考哦!”
“你们班上第一是哪个哟?”
“常胜将军嘛!”
“上次被你打败了?你看你还是歪,把别个常胜将军打败了!就是这样,还是我教育得好啊!没得我小时候看到你不会,就整你两棒棒,你没得今天这样!”翘着脚搅一筷子面条自豪地笑。
“那还是我基因好嘛!我娃儿嫩个聪明!”
“要得!哎呀,两人基因都好都好!吃饭吃饭!”爸刚刚说过一茬,又接过一茬。
“还得考一中,好中学里氛围不一样!好好搞!爸爸养得起!莫担心!”
“幺儿好好读书,走出去不要当农民啊!”
吃饭的时候是农民们难得的休闲时光,也是父女、母女难得的谈心时光。只有这个时候可以不用劳作,可以不要读书,谈谈父母的期许和女儿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