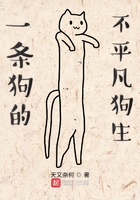离开青白山,三日路程便到了临安城地界。
离开半年,这座城依旧繁华。
半年前轰动附近数城的姜堰去世,姜府散尽家财的消息也归于平静。姜白长在姜府,因父亲曾心系她的血脉,所以自幼姜白很少出门,即便出门,也是有府里下人周密保护。临安城受过姜府恩惠的人有十之八九,此刻走在偌大的大街,街面竟无人识得姜家小姐。过往行人看着这一面容温润姣好的道姑暗叹可惜,若是哪户小姐,提亲的媒人怕是要踏破她家门槛。
郑忘书跟在小姐身后一言不发,穿过最繁华的长街,身旁少了街面上叫卖的嘈杂。离城南越近,街面就越冷清,到了距离城门数丈的位置便渺无人烟了。
城南的景,依旧枯萎。
姜白的脸上写满了落寞。郑忘书想安慰这个失去了家的孩子,可平时嘴碎的他,现在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在母亲的墓前跪下,旁边新落的一座墓是父亲的。
“娘,虽然从未见过你,但爹这么多年对你痴痴不忘,想必娘也是当年倾倒整个临安城的女子吧。爹去找你了,你们俩留我一人在这世间,我讨厌你们。”姜白说着说着,语气渐渐急促,而后便放声大哭起来,尖利而嘶哑的哭声是那么苦涩,仿佛在黄连水里泡过似的。
跪着挪了挪位置,朝着父亲的墓磕了三次头,姜白不停地抽泣,梨花带雨地继续说到:“爹,我是骗娘的,我不讨厌你们,我只是想你们了。我在青白山很好,师父师兄们都很照顾我,忘书哥在教我练武,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姜白就那么一直跪着,一直对两方冰冷的石碑倾诉,脸上晶莹的泪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直到最后声嘶力竭,再也坚持不住,晕倒在墓前。
深秋了,一天比一天凉。萧瑟的临安城南,连一片枯叶都没有,人说枯木逢春,可这姜家墓前,再也没有了春天。
郑忘书将小姐扶起,背在背上,一言不发地离开这地狱般死寂的地方。姜白在他宽厚的背上睡了过去,这一睡,便是数十里的路程。
“你醒啦。”郑忘书感觉背上的孩子动了动,发出声响。
姜白看着自己在忘书哥的背上,脸咻地红了,嚷嚷着要下来。长这么大,除了爹,没人背过她。
“我睡了多久啊?”姜白一脸不好意思地问。
“你还好意思问呢,哭得那么用力,哭完了倒头就睡。我们这都出了临安城好几十里地了,你再不醒,我都要累死了。”郑忘书故作生气的样子说到,其实他一点不累,天下数一数二的剑道修士,背个小姑娘实在算不得什么难事。郑忘书说罢,将小姐放下,从包里拿出干粮递给她。
“吃吧。吃完了打坐运气调理一下,不急着赶路。”
“嗯。”姜白连连点头,她其实是饿醒的,只是没好意思说。
郑忘书一脸认真看着小姐运气,吃饭。
“你为什么想练功?不是说只想读遍天下书吗?”
“我想保护自己,如果可以,我想保护师父,师兄,青白山所有人,当然还有忘书哥你。”
郑忘书听着这话,心里虽然暖暖的,但还是哈哈大笑:“就你,还保护人呢,别让别人保护你就不错啦!”
“我会保护自己,我要练功,有一天一定能保护你们。”
“谢谢您嘞,不用哈。”
“忘书哥,你为什么要练剑呢?”
“小孩子别问那么多,好好吃饭。”
姜白放下手中的馒头,温润的眼眸里印着郑忘书的影子:“你是为了报仇。”
郑忘书没有回答,坐在姜白身边,手放脑后,靠在树旁。眼睛望着天际火烧过的赤色云彩,黝黑而坚毅的脸上刻满了二十多岁不该有的沉重。姜白从未如此近距离认真看过他,听着忘书哥轻声喃喃的说到:“赵寒山,天魔双戟败尽天下武夫,天下第一的赵寒山哟,什么时候才能比得上他。”
她有些心疼。
“你为何那么执着呢?你从未见过西蜀,老郑叔的国仇家恨,你能感受得到吗?”
“只是想给老头出口气。”
“报了仇,就是终点了吧?忘书哥,再也没有西蜀了,打败了赵寒山,就跟我回青白山修道吧。”
平时话多的郑忘书今日话却很少,只是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说:“走吧,天快黑了,我们得赶到镇上歇息。”
子夜,花溪镇。
郑忘书背着早已经微鼾姜白,站在花溪镇的牌坊前注视着这个幽静的镇子,青瓦白墙,夜幕中熟睡的人悠然安宁。独自走在镇上主街,逛了一圈,郑忘书未发现有客栈之类的店面,倒是街角尽头有一间小屋还有摇曳的烛光,便前去轻轻敲了敲门。
“有人吗?过路人,可否借问哪有客栈?亦或是可否在此借宿一晚?”
里面久久无人回应,郑忘书又敲了敲门:“有人吗?”声音又提高了几分
“来啦。”
房里有人回应,可这尖利凄惨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
开门的是一位看不出年纪的驼背老妪,一张十分丑陋恐怖的脸阴气沉沉,皮肤干瘪得像枯了百年的杨树,脸上全是岁月用刀划出的沟壑,右眼的眼眶里只有空空荡荡的黑,不知是瞎了多少年,光秃秃的头顶没有剩下几根头发,如风中残烛一般。
眼前这老妪吓得郑忘书不自觉地伸手扶住腰间的悲鸣,身体的抖动也惊醒了背上的姜白,姜白睡眼惺忪间看见眼前这一位恐怖的老妪,吓得惊声尖叫,从郑忘书背上滑落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
“哇......哇......”在疼痛和惊吓中,姜白嚎啕大哭起来。
老人一副习以为常的冷静,说到:“乖,乖,别怕,奶奶是好人。”老妪蹲下想伸手去将姜白扶起,可姜白听见这凄厉的声音哭得更大声,手撑着地连忙往后退。
郑忘书将姜白扶起,姜白赶紧躲在忘书哥的身后,只敢偷偷瞄着这驼背老人。
郑忘书定了定神,向老妪行礼道:“大娘,我们是临安来的过路人,天色已完,请问这镇上可有客栈?”
老妪把门大开,侧身示意二人进房,缓缓说到:“这花溪镇净是些农民,哪有什么客栈。”
姜白扯着忘书哥的衣角,躲在身后慢慢走进小屋,见并无危险,才渐渐放下紧张的心。
“咳,咳……年轻人,你带着妹妹从哪来,往哪去啊?”
“我们临安来的,去东海看看家里亲戚。”郑忘书坐在凳子上,说到。
“年轻人带着妹妹跑那么远,家里是落了难了吧。”独眼驼背的老太小声说着,转身去柜子里捯饬一床破旧棉絮,铺在地上。
“你们要不嫌弃就睡这地上吧,老婆子床上脏,地上比床干净,家里小,没第二张床了。”
姜白平复了心情,小心翼翼靠近老人,帮她打地铺,收拾东西。
“婆婆,对不起。”
“这傻姑娘,没事儿啊,老婆子这辈子就生这模样,在这住了几十年,他们都叫我鬼婆婆,吓着你不好意思啊。”
“您的眼睛……”
“瞎了几十年了,不说了。孩子,铺好了,你们就在这将就一晚吧。”
姜白将老妪扶上床,自己再坐在铺好的地铺上,说到:“忘书哥,来睡觉吧。”
“你先睡吧。”
姜白实在困了,躺下没片刻便睡着了。
小小的屋里一只白烛的黄色火焰缓缓摇曳,郑忘书坐在凳子上,闭着眼,任由气息在身躯中流转。
“快睡吧,睡着了就没事了。”老人翻了个身,背对着郑忘书轻声说到。
“大娘,何出此言?”
“没事,没事,赶紧睡吧。”
郑忘书也不再问了,闭上眼睛,坐在桌旁缓缓睡去。
不知过了几个时辰,门外似乎传出阵阵哭泣之声。
郑忘书睡眠本浅,又加之警觉,听见这宛转啼哭之声便惊醒了,起身正想出门查看,却被床边传来的凄厉声阻止:“别出去,她哭过就好了,天亮之后就无事了。”
见鬼婆婆如此说到,郑忘书心里就更疑惑了:“大娘,这到底怎么回事?”
老人从床上坐起来,驼背的样子犹如一只厉鬼蜷缩在床沿,用她那尖利凄婉的声音缓缓说到:“她已经哭了六十多年了,倒也不是每晚都哭,只是你们今晚遇上而已。”
“她叫柳若云,他们柳家在她死后就搬走了,不知道她怎么死的,只知道后来她化身夜哭鬼在这镇上游荡。起初那时,有人好奇,晚上寻哭声而去,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在夜里哭泣,可去的人都一去不返,白天就发现死相瘆人。从那以后,家家户户门前都贴着驱邪的符咒,晚上再也没有人敢出门。这魂,便在花溪镇哭了六十多年。”
“那你怎么知道她是柳若云?”
“老婆子这辈子活得就像鬼一样,我那时候想去死,就晚上出去寻她,我看见了她的脸,是镇上匆匆搬家的柳家女儿。她只是哭泣,却不曾害我。”
“为什么没杀你?”
“我可能算是她唯一能称得上朋友的人吧,她是要我活下去。自那以后,我再也不寻死了,在这小屋活这七八十年,时常夜晚听她哭泣,倒也习惯了。”
郑忘书摇摇头驱散睡意,提着黑剑悲鸣和白剑寒江雪,说到:“我去看看。”
老妇在后劝阻,郑忘书轻声道:“请放心睡吧,去去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