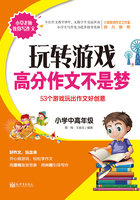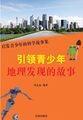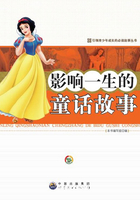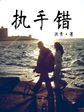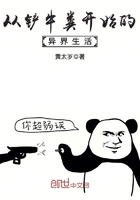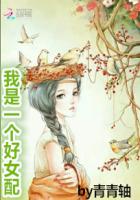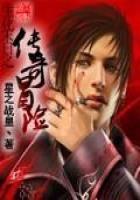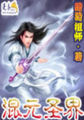黑釉瓷和结晶釉
在已发现的宋代瓷窑中,有三分之一的瓷窑烧造黑瓷。特别是其中一种黑釉碗盏,产量特别大,这与宋代盛行的“斗茶”风气有关。“斗茶”使饮茶者染上一种超出止渴作用的典雅风尚。黑釉就其釉色来说,并不雅观,但是经制瓷工匠的特殊加工后,釉面上烧出了丰富多彩的点缀,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从而深受欢迎,风行众多地区。黑釉的装饰大体有以下几种:
兔毫盏,碗身里外的黑釉上都有细长的条状白纹,细长的程度很像兔毛一样,并闪烁着银光色,所以叫“兔毛斑”、“玉毫”、“鹧鸪斑纹”。其产品以福建的建阳窑最著名。
油滴釉,黑釉面上可以看到许多具有银灰色金属光泽的大、小斑点,形似油滴,又很像黑夜天空上的繁星,大小不一,大的约可达数毫米,小的只有针尖大小,我国叫它为“油滴斑”、“鹧鸪斑”,日本人也极喜爱它,称它为“天目釉”。其产品在南北许多窑都曾有过生产,也以福建建阳窑最典型。
以上两种釉在现代陶瓷学中根据其生成机理,称为“结晶釉”。这两种瓷品是建阳窑的高档产品,极难烧制,出土及传世的极为罕见。
玳瑁釉,以黑、黄等色彩交织混合在一起,有如海龟的色调,宋代称这种瓷为玳瑁盏。这种釉应属于以黑釉为基调的花釉中的一种。它色调滋润,在当时以江西吉安永和窑的产品最著称。
剪纸漏花,是把当时民间的剪纸花式移植到黑釉茶盏而创造出来的黑底白花的瓷器装饰新手法。产地主要在南宋时期的江西吉安永和窑。
黑釉剔花,是在胎坯上着以黑釉料(烧成前),再剔刻流畅的线条或图案,露出内部白色胎体,以装饰黑釉瓷。这一手法在当时南北方的瓷窑都使用,风格因地而异产品以山西雁北地区的最杰出。
以上两种装饰显然都是对北方磁州窑铁锈剔花装饰的继承和发扬。
黑釉印花,其装饰手段最早出现在定窑,以后许多窑都学习掌握了这种技法,其中山西部分地区制瓷工匠吸取了定窑的装饰艺术的长处,又保留了本地区工艺特色而发展的黑釉印花瓷器最引人注目。
总之,上述黑釉技艺及其装饰手段使黑釉瓷在宋代风行一时。各地的黑釉瓷虽然装饰手法不同,但是它们在烧制工艺和形成机理有许多共同之处,人们对此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各种不同品种的黑釉都含有较高量的铁的氧化物,这些氧化铁无疑是黑釉的主要呈色剂。此外黑釉中还含有少量的MnO、CuO、Cr2O3等着色剂,虽然含量很低,但对色调变化有一定的影响。这些黑釉已基本上由石灰釉转变为石灰碱釉;即在石灰中掺入了杂木灰,釉层厚度也;显著增加,由早期的0.1~0.2毫米增至后来的1毫米左右。釉色也由早期的深绿褐色或黑棕色逐渐变为乌黑色,光泽也有较大的改进。
宋代烧造黑釉瓷器最负盛名的窑是福建的建阳窑和江西的吉州窑乙建阳窑烧造的“油滴”、“兔毫”黑釉瓷为众多文人所津津乐道。例如宋代大文豪苏轼的诗“送南屏谦师”写道:“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勿惊午盏兔毛斑,打出春瓮鹅儿酒。”反映了建阳窑黑釉兔毛盏的盛誉。南宋时,福建泉州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之一,建阳窑的黑釉瓷作为深受欢迎的商品,由此远销日本、东南亚、南亚乃至欧洲。
古代瓷艺的鼎盛时期
明清时期,景德镇以外的窑场先后衰落,各种具有特殊技能的制瓷工匠云集景德镇,造就成该镇的“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繁荣局面。明代万历时人王世懋在介绍当时景德镇的景象时说:“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戏呼之曰四时雷电镇。”据考,在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时,在景德镇从事瓷业的人数已达到了十余万人。景德镇生产的瓷器不仅数量大,品种多,而且质量高,销路广。正和宋应星所说:“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景德镇先后生产的釉下彩青花瓷器,釉上彩五彩瓷器、斗彩瓷器、珐琅彩瓷器、粉彩瓷器以及各种多样的高低温色釉瓷器,代表着当时中国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景德镇生产的瓷器不仅要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更要担负着宫廷用瓷和赠外礼品瓷的重任,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瓷业生产中心——瓷都。
最具民族特色的青花瓷器
青花瓷器是指应用所谓“青钴料”在瓷坯上绘画,然后着上透明高温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呈现蓝色花纹图案的釉下彩瓷器。这种瓷器的釉彩着色力强,发色鲜艳,呈色稳定,彩在釉里不易磨损模糊,加上白地蓝花有一种特殊的明净素雅之感,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效果。美观实用的特色使青花瓷器深受人们喜爱,从而获得迅速发展,逐渐成为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主流之一,远销国内外。
釉下彩绘和运用青钴料作为呈色剂是青花瓷器烧制的基本工艺要素。通过对这两个要素的考察,可以认为青花瓷器在中国烧制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段相当长的发展历史。关于釉下彩绘技艺,早在唐代,长沙窑已曾采用含铜和铁的矿物为颜料,烧制成釉下彩瓷器。到了北宋,这种釉下彩装饰方法为磁州窑所继承,创造了白地黑花釉下彩瓷器。随后这种方法为更多瓷窑所掌握。釉下彩的技法经历了400多年的发展,于是在元代出现了成熟的青花瓷器。运用青钴料做呈色剂在唐代已较普遍。唐三彩的蓝釉就是采用了青钴料,那么唐代似已应有青花瓷器。出土文物证实了这一推测,1975年在江苏扬州唐城遗址曾出土一件青花瓷枕的残片;另外在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着一件据说是1948年出土于河南洛阳的唐代白釉蓝彩的三足缶复(按无缶复字,可能自钅复字演化而来,钅复为金属质大口釜)。宋代的青花瓷片曾在浙江龙泉县金沙塔的塔基和绍兴县环翠塔塔基中发现,据测定它的MnO/CoO比为10.25,Fe2O3/CoO比为0.61,与其他时期的青花瓷器不同。从它的外观来看,其青花色彩暗蓝,甚至带有一点黑色,初步推测它大概是采用含氧化锰很高的国产钴土矿。其烧成温度约在1270℃。
在唐宋青花瓷器烧制的经验基础上,元代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制作达到成熟的水平,并开始大量生产。近40年以来,在元代居住遗址、元代窖藏及元代墓葬中陆续出土了不少青花瓷器。它们的共同点是施淡青白色釉,而不是无色透明釉,青花的色泽带灰,而不是典型的深蓝色,纹饰也比较简单。据对景德镇元代青花瓷片的检测,可以发现它是在当地青白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胎中A12O3含量明显增加,表明当时制瓷胎料已开始采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而不是只采用单一瓷石。元代青花瓷的釉层色白微青,光润透亮,釉中CaO含量较少,Na2O、K2O成分相应增加,表明釉已由石灰釉向石灰碱釉过渡;使用的青花钴料既有进口料,又有国产料。此外,元代青花瓷器在胎釉方面尚普遍存在原料淘洗不细,制作较粗劣的缺点,这里既有时代的烙印,又有原始的特征。
在明代的景德镇众多瓷器中,青花瓷器一跃占据了主流地位,它较元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数量上,更突出地体现在质量上。大多数明代的景德镇青花瓷器不仅胎质细腻洁白,釉层晶莹透亮,而且以其青色浓艳、造型多样、纹饰优美而负盛名,使青花瓷器的生产迈入了一个黄金时代。明代的永乐(1403~1424)、宣德(1426~1435)、嘉靖(1522~1566)等年间都曾烧制出具有各自特色的青花瓷器,这与它们采用了不同的色料有直接的关系。永乐和宣德年间的产品所用青花的色料主要采用郑和等从南洋、伊斯兰国家带回的含锰低、含铁高的“苏麻离青”(一种含氧化钴的青料的译名),所以产生浓艳的青花,但时有黑斑出现。自宣德后期,由于进口青料的减少,于是多使用进口青料和国产青料相配合的混合料,在适当的烧成温度下,青花色彩变成柔和淡雅的蓝色,黑斑也少见。至成化、正德年间,由于已普遍单纯采用国产青料,加上正德初年的宁王叛乱,景德镇御器厂一度停产。这时期其他瓷窑的青花瓷的色调大多较淡浅或稍浓带灰。嘉靖年间,则又恢复使用了进口青料,并在使用进口和国产混合青料时对适当配比也有了更多的经验,所以烧出的青花呈现蓝中微泛红紫,浓重而鲜艳。万历中期以后,可能由于进口青料的中断而再度普遍改用国产青钴料,然而这时期的工匠对国产青钴料的加工使用已掌握了较丰富的经验,所以烧成的青花虽然没有嘉靖时那么浓艳,但是蓝中微微泛灰,也颇有沉静之感。由上述史实可以窥见明代景德镇所烧造青花瓷器的变化和发展,所使用的青钴料原料及其加工技术则是这一变化的主要根据。
由于瓷器上的青花分别与釉和胎熔合,刮下来的青花试样中,除青料外,必然还含有部分釉和胎,因而所得的分析结果并非单是青料,而是这种混合物的化学成分。从分析数据来看,青花部分中氧化锰和氧化钴的含量差不多,而氧化铁较高。表5—2是分别产于浙江、云南的钴土矿的化学成分。由表可见,国产钴土矿的成分中,氧化锰的含量要比氧化钴高达数倍乃至十余倍。对照之下,可以推测上述宣德青花大盘上的青花所采用的青钴料是进口青料。由于进口青料含锰不多,含铁量却很高(是属于含钴铁矿),所以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青花,其颜色是蓝中泛绿,深色的部分呈黑色,大的呈黑斑,小的呈黑点,是Fe2O3,产生的效果。国产青料,矿物学上名钴土矿,产地分布颇广,名称也不统一。钴土矿实际上是由二氧化锰、氧化钴和其他氧化物所组成的复矿。
一般未经烧制的钴土矿是不足以直接用做青料的,仅经一般加工的国产青料,呈色往往明显带灰。明代时的制瓷工匠还绝不可能了解到青花的主要着色剂为钴的氧化物,氧化钴用量过高,会使色泽易发紫黑,过低则不能显出青蓝色;钴土矿中氧化猛、氧化铁的含量多寡会对青花呈色造成很大的影响等。但是他们却在实践中逐渐掌握了进口青料和国产青料的适当配比及进口青料和国产青料的深加工,从而烧出了高质量的青花瓷。他们在配制釉料中,还认识到钴土矿用多了,会使颜色泛紫(由于铁、锰氧化物的增加);若是矾土石用多了,则会使研磨加工变得困难(矾土石主要成分为氧化铝)。他们根据经验,对国产钴土矿采取了一系列富集挑选等加工手段。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就写道:“凡画碗青料,总一味无名异(漆匠煎油,亦用以收火色)。此物不生深土,浮生地面,深者掘下三尺即止,各省皆有之。亦辨认上料、中料、下料。用时先将炭火丛红煅过。上者出火成翠毛色,中者微青,下者近土褐。上者每斤煅出只得七两,中下者以次缩减。如上品细料及御器龙风等,皆以上料画成……凡饶镇所用,以衢、信两郡山中者为上料,名曰浙料,上高诸邑者为中,丰城诸处者为下也。凡使料煅过之后,以乳钵极研(其钵底留粗,不转锈),然后调画水。调研时色如皂,入火则成青碧色。”朱琰在其《陶说》中写得更为详细:“其八曰采取青料:瓷器,青花、霁青、大釉,悉借青料,出浙江绍兴、金华二府所属诸山。采者入山得料,于溪流漂去浮土。其色黑黄、大而圆者为上青,名顶圆子。携至镇,埋窑地三日,取出重淘洗之,始出售。其江西、广东诸山产者,色薄不耐火,只可画粗器……白地青花,亦资青料。明宣德用苏泥勃青,嘉靖用回青。青非不佳,然产地太远,可得而不可继。”又说:“其九日拣选青料:青料拣选,有料户专司其事。黑绿润泽,光色全者为上选。仿古霁青、青花细器用之。呈黑绿,而欠润泽[者],只供粗瓷。至[于]光色全无者,一切选弃。用青之法,画坯上,罩以釉水。入窑烧成,俱变青翠。若不罩釉,其色仍黑;火候稍过,所画青花亦多散漫……按明用回青法:先敲青,用捶碎之。拣有朱砂斑者为上,有银星者为次,约可得十分之二。其奇零琐碎,碾之入水澄定,约可得二十分之一,所得亦甚少。选料不精,出器减色,故必属之料户专司。”对钴土矿的淘洗、煅烧、拣选、磨细等加工,实际上是提高了青料中氧化钴的含量,部分地剔除了铁、锰氧化物的成分。色料的磨细程度不仅影响画工,就对显色来说也很重要,色料愈细,更能使颜色均匀调和;若色料中有过粗颗粒,在烧成中就可能出现黑斑。
正是在逐步认识、掌握青料的采集、加工的实践中,明代青花瓷器的发展经历了上述的曲折过程。到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的御器厂仍主要采用浙江产的青料,烧出的青花瓷达到了纯蓝色,不再泛紫色,并有深浅层次分明的青花色调,即取得了比明代更高的工艺水平。清代康熙年间的青花瓷浓淡一致、层次分明,则是由于着釉技术有了改进。明代青花瓷的浓淡层次,是瓷工用小毛笔在涂抹青料时,利用笔触青料的多寡来掌握;而清代的瓷工则已能熟练地运用浓淡不同的青料,调染出深浅有别的蓝色色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