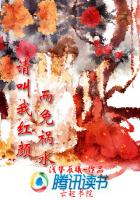次日,果然九桓王便上了书说想要认冼乐郡主做干妹妹,理由是原本高太后赐婚本就是为安抚为朝廷殉职的肃国公,慰藉一下冼乐郡主丧失父母的悲痛。如今自己上书认冼乐郡主做干妹妹,结果也是一样的,肃国公府依然保有它应有的哀荣,冼乐郡主的身份也算是抬一抬。
正巧此时冼乐郡主也上书说自己不够格做九桓王府的正妃。本来呢,这桩亲事也没什么人支持,说肃国公府为朝廷尽忠殉职,本就是一个天大的福分,朝廷又没有对不住肃国公府上上下下,凭什么肃国公府没落了,肃国公府的千金冼乐郡主反而还能攀嫁进九桓王府。
她的确也觉得冼乐郡主身世可怜,可这种先例,一开便是永无止境。那所有殉职的大臣都觉得自家女眷可以嫁入王府,那大夏的王妃也未免太过好当了。
下了朝,她今日倒是没想要留在宫里面了,难得的大早晨,她也实在不想观景观到一般又被谁拉过去救命。
不过,大殿之外,一个服饰看似是宫女打扮的,很是恰到好处地拦住了她的去路:“长公主殿下。”
她有些吓了一跳:“我不认得你,你是何人?”
“奴婢是冼乐郡主身边伺候的宫婢,”那宫女朝她拜了拜:“长公主殿下说笑了,宫中奴婢众多,殿下又怎会每个都认得?”
唔,这个小婢子果然同她主子一样是个伶牙俐齿,一样很是不讨她的喜欢。
“我家郡主说,新得了个很是别致的好茶,听闻长公主殿下也是个爱茶之人,我家郡主想邀殿下到湖心亭小坐一番。”
她笑笑,有些不耐烦:“替我谢谢你家郡主,不过恐怕我同你家郡主的交情没有深到可以一同坐下来喝茶的地步。我这人怕尴尬,恐怕要让你家郡主失望了。”说罢瞪了那宫女一眼,就要走开。
“殿下,”那宫女挨了上前:“我家郡主说,有些事情,恐怕殿下会很感兴趣。”
唔,她如此说,她还真的有些感兴趣。左右这些天让她感兴趣的事情太多,她还真有些想知道这个冼乐郡主明知道她不是很喜欢她,接二连三地要同她拉紧关系,会有什么特别让她感兴趣的事情。
倾阳长公主一身朝服,红裙曳地,也不做过多的修饰,担当得起清雅脱俗这四个字。她拉着梳茶,走进御花园。御花园果然是皇家的院子,同外面许多别致的院子也有所不同,一年到头,四季別景。
湖心亭,顾名思义便是御花园里那湖面上的一处亭子。远远望去,亭子里还果真坐着刚刚退婚的冼乐郡主,正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湖面风景。
见她上来,冼乐郡主微微一拜:“冼乐给长公主殿下请安。”
“你今日倒是很客气。”她坐下,示意眼前的冼乐郡主也坐。
倾阳长公主看着桌上的茶盏,茶盏上飘着淡淡的茶香,倒真的是上好的茶叶,可同前两日她从漱玉斋顺走的那一排,还是有些差别的,一不留神便说出了口:“你这茶,茶香倒很是怡人。可我府上比这好上许多的,也不是没有。”
冼乐郡主一愣:“殿下名动天下,府上所用的自然都是上好的物什,冼乐区区一包茶叶,入不了殿下的法眼也是自然。”
“你不用说那些好听话来奉承我,”她淡淡啜了一口茶,唔,还真的不如昱先生的茶来得好喝:“你的婢女说,有我感兴趣的事情要说与我听,我不过有些感兴趣你口中这个感兴趣的是什么事情罢了。”
“呵,”冼乐郡主笑了一声,果然明牙皓齿,黑发如瀑,这一笑,也算是个美艳佳人,是有些可惜了她的那个三弟。冼乐郡主接着说:“冼乐只是一直不是很明白,殿下为何如此厌恶我。”
“厌恶倒是说不上,”倾阳长公主说:“你应该晓得,从小我便是一个人生活。纵然我还有挽阳润阳她们几个妹妹,但我从来都不曾与她们亲近过。我对待兄弟姐妹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对你,你不必妄自菲薄。”
冼乐郡主静静听着,倒也没有反驳:“殿下名动天下,冼乐早晓得殿下不会那么好相处。”
“我是不好相处,”倾阳长公主笑笑:“若你没有什么非要见我的要紧事,我想我同郡主的交情,还没到可以坐下类喝杯茶的地步。”
“殿下,”冼乐郡主紧接着她的话尾:“冼乐看得出来,殿下同太后娘娘之间,怕是有些嫌隙。”
“你既然看出来了,便应该知道,我是极不喜欢你的。”冼乐郡主还未说完,倾阳长公主她便打断了她的话:“你觉得我一口一个母后,便真当她是我的母后了?你同高氏日日混在一起,我对你自然没什么好脸色。”
冼乐郡主一笑,却突然说了一句:“殿下,可是在为当年的事情记恨太后娘娘?”
她放下茶盏,眼眸犀利地盯着对面坐着的冼乐郡主:“敢在我跟前提起当年事的,郡主你是第一个。”
“高太后害死我母后,我如今一口一个母后,不过为了抱全我和陛下罢了。”她似笑非笑地说:“认贼作母,恐怕我亡母地下有知,不能瞑目。”
湖面上,几个鲤鱼跃出水面。前两个月覆盖在湖面上的冰雪已然渐渐融去,又看得到湖底的一片景色。
“冼乐今日邀殿下小坐,便是有一件事关当年的要紧事,想同殿下讲讲。”冼乐郡主说:“殿下说的不错,我肃国公府如今沦落到如此境地,她高氏难辞其咎。若不是太后娘娘同陛下举荐我父亲治水,我父亲也不会葬身秦江,我母亲也不会寻了短见。”
“肃国公府家破人亡,又搅黄了我的婚事,即便无心,我也无法装作无事。”冼乐郡主抬眼:“殿下做的是十分凶险之事,即便我如何怨恨高氏,我都还不想将自己一条性命搭给殿下。”
倾阳长公主轻啜一口茶:“你能想通自然最好。左右我也没想过让你帮我,你想要袖手旁观,我也觉得没有什么。”
冼乐郡主挨近了她一些,压低声量:“不过我前些时日听到些有趣的事情,想同殿下讲讲。殿下可有兴趣?”
她一顿,眼中有凌厉的神色:“你继续。”
“殿下回兴州城那一夜,太后娘娘大发了一通脾气,倒不是因为殿下出征北境的事情,”话毕抬眼看了看,有些心虚:“一开始可能是,但是到后来,张嬷嬷进了仁寿殿,同太后娘娘说了一些话过后,娘娘气得更甚了。”
“我因听说太后娘娘大怒,做了些甜汤过去。偶然听见,”冼乐郡主一顿:“太后娘娘身边的张嬷嬷,提到一个名唤抒若的女子。”
抒若?倾阳长公主心下一惊。
“说下去。”她放下茶杯,一双眼睛紧紧盯着茶盏下熊熊燃烧着的炭火,狠厉非常。
冼乐郡主一顿:“我听见,张嬷嬷对太后娘娘说这个叫抒若的女子,又同太后娘娘要些银子,银子的数目好像不小,太后娘娘听后大怒,足足为此事在仁寿殿发了好几日的脾气。我派人去查了查,这个叫抒若的,从前在慕容皇后手底下当过差,殿下心里,怕是也晓得的。”
她自然晓得,晓得的不能再晓得。
她握紧拳头:“你可有听到,这抒若如今是在何处?”
“冼乐听说,张嬷嬷今晚会将银两放在城郊的一处荒庙里。具体是哪一处荒庙,这个我不知,”冼乐郡主说:“不过,太后娘娘说了,这件事必定会让张嬷嬷亲自去办。我想殿下今晚派个人跟着张嬷嬷,一切便会水落石出。”
冼乐郡主抬眼,眼前端端坐着的倾阳长公主面色看上去没什么大的变化,那一双眼睛却是血红无比,紧紧攥着的拳头越握越紧,直直掐出了一道血痕。
她起身,步伐有些慌乱:“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我告诉殿下,就当是还了殿下保我清誉的恩情。我从小便是这个爱憎分明的性子,我想此事对殿下想必极其重要。”冼乐郡主坐在凉亭的石凳子上,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我不知道殿下打算如何处理此事,但我今日告知殿下,算是了了殿下对我的恩惠。从此,冼乐不会再打扰殿下。”
冼乐郡主站起身,在倾阳长公主身后福了一福。也不等倾阳长公主说什么,转身便走出了凉亭。
梳茶在一旁看着自家主子如此失态,匆忙上前扶住她。她脚一软,跌坐在凉亭旁的长凳之上。
抒若,抒若……她从未忘记过这个名字。当年的事,若是没有抒若的信誓旦旦,恐怕当时她的母后便不会死,临川王府不会血流成河无人幸免,容止不会逃难至今。
梳茶搀着她,一脸担忧:“殿下,殿下你这是怎么了。”
她闭着眼,她早晓得当年桩桩件件的事情都同高太后,同如今风光无两的梁国公府脱不了任何关系。可她倒是从未想过,是这种可能。抒若,原来同高太后一直暗地里来往,要置她的母后于死地吗?
“梳茶,我们即刻出宫,”她睁眼,眸中犀利无比:“你让邢尘立刻来见我。”
夜里,已经到了万家灯火皆熄灭的时辰。打更的人提着灯笼走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之上。
凉风吹过重重红墙,青砖绿瓦。倾阳长公主府里,她房中仅仅点着一盏灯,着了梳茶不必伺候,似乎在等着什么人。
门廊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邢尘推开门,走了进来,拉下蒙着脸的布条,是邢尘没错。
“殿下,”邢尘跪在她跟前:“殿下交代属下去做的事,属下已经办妥了。”
倾阳长公主点点头,眸色急切:“她可有说什么?”
“她说了。”邢尘抬眼,看向自家主子的眼神里有哀切之情,心生不忍:“当年的事情,她什么都说了。”自家主子查了那么多年的案情,原来根源就在一个女子的身上。
作为倾阳长公主身边待得最久的侍卫,他心里自然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自家主子此次下山,不是为了匡扶大统,不是为了整肃朝纲,也不是为了保家卫国。这些事情,倾阳长公主不过占了一个名分,这些年,自家殿下受过怎样的苦楚,旁人不晓得,他看得清清楚楚。
他有些不忍,可此事,无论如何都要说与她听:“抒若进宫之前,随着母家的哥哥们读过几年的书,还会写几个字。她悄悄偷了几份娘娘的手书,背地里学了几个娘娘的字,然后再将那些信放进娘娘梳妆盒子底下的暗格子里。”邢尘说:“高太后许诺她,事成之后会放她出宫,天涯海角,去过她想要的日子,还会拿出很大的一笔银两供她度日。这次,是因为银两用光了,才冒险返回兴州城同高太后要的。”
“属下跟着张嬷嬷一路跟到了西郊城外的一处荒庙,张嬷嬷走了以后属下便将抒若带进了城,安置在府上的密室里,没有惊动任何人。”
微薄的烛火下,她的眼眶里缓缓落下一滴泪:“你说……是她做的?”
“殿下……”
她深吸一口气,嗓音隐隐有哭腔:“此事你不要告诉容止,你也知道容止的性情,知道真相后会干出什么事来,谁都不晓得。”她说:“找到合适的时机我会告诉他。这些事情,他有权知道真相,我不会瞒他太久。”
“是,”邢尘应到:“殿下可要唤梳茶进来?”
“不用,你出去吧。”她轻声。随着邢尘关好门的声音,烛火下,她觉得脸上有些痒,抬手轻轻一抚,指尖上的泪滴闪闪发光。
何愁,何怨……皇宫,临川王府,药师容府,那一条条的性命,血肉之躯,不过是为了名利,高氏和高家,就如此下得去手吗?如此深仇大恨,她记在心里那么多年,午夜在冰冷和孤独中醒来,这些年,这么多年,那些失去的,或者说她不曾拥有过的,就像一缕烛光,短暂且悲凉。
夜色寒凉里,烛火短暂里,一恸,她掩面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