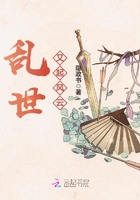漠北大军军营内,拓跋旦坐在营帐里,眼前是刀斧加身却丝毫面不改色的西夏倾阳长公主。
“漠北拓跋氏一向以温厚治下闻名于世,如此对待客人似乎不是漠北应有的礼数吧。”倾阳长公主一身素服,站在他面前,身后是一众大大小小上上下下漠北将士们。
拓跋旦抬手示意漠北将士离开营帐,整个剑拔弩张的气氛实在很是紧张。眼前人的突然造访让他有些意外,也猜不透原因。
他自不会相信眼前权倾朝野的大夏倾阳长公主会只身一人就有那个胆色夜闯漠北大军营寨,他也没有那个胆色拿倾阳长公主怎么样,若是敢动眼前人哪怕是一根毫毛,搞不好无端给大宋和西夏生出结盟攻打漠北,回击漠北大军的借口罢了。
大宋和西夏结盟,他是很愤怒没错。可这乱世中风云变幻,各国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行事,譬如先前的西夏和漠北,也譬如现下的西夏和北宋。
他又岂会不知。
“宋军既然千里迢迢相帮夏军,恐怕倾阳长公主如今也没什么好担心了,现下又找上门来,是个什么说法?”拓跋旦说。
那边倾阳长公主自顾自地倒了杯茶润润口:“我今日来此,是来给阁下一个台阶下,给你三十几万大军一个台阶下,也给贵国一个台阶下。”
“将军现如今恐怕还在纠结吧,纠结到底要不要孤注一掷一攻我灵州城,”她说,声音云淡风轻,丝毫不见在意的形容:“攻下来了自然是最好,能交差嘛。你们漠北要动员三十万大军不容易,那么窝囊地回去不说占不了什么便宜,恐怕还会成为全天下的笑柄吧。”
呵,还真是。拓跋旦心想。漠北拓跋氏朝廷养精蓄锐二十年,二十年前在大夏临川王的军下大败,本以为趁着如此内外不稳的大好良机可以一雪前耻大展漠北拓跋氏的雄伟,这大宋一搅和,拓跋旦在心里略略计较计较,着实没有什么胜算可言。
不过一夜,这大夏和漠北的形势和立场彻底调换,唉,实在是天意弄人啊。
“小王还是想不通殿下为何要亲自到我漠北大军的军营同小王说这些话,如今如此形势,殿下莫不是来落井下石的不成?”拓跋旦嘲讽地笑说:“殿下如此格调,可是有失长公主身份啊。”
“阁下怎么这样说呢,我冒着被阁下杀了的风险都要来相劝,阁下就这样回礼吗?”她说。
“相劝?呵,你要劝我什么?”
“劝你退兵。”倾阳长公主轻啜一口茶,唔,茶叶是次了点,倒是温度火候刚刚好。
“长公主大晚上的来,是来与我说笑的吗?”这位漠北拓跋氏的六皇子说:“长公主莫不是忘了我拓跋旦南下是所求为何了?攻不下灵州城便要我退兵,殿下不知是哪里来的自信。”
漠北拓跋氏一向与武将朝廷立国,他拓跋旦一向以军功赫赫著称,漠北的铁骑前锋一向以威名名震天下,如今尚且不博便要主动认输,不只滑天下之大稽,还堪堪丢了整个漠北拓跋氏朝廷的脸面。
“左右阁下已经是攻不下灵州城了,不是吗?单是论阁下大军的人数,即便强攻,也绝不是宋夏两军的对手。”倾阳长公主抬眼:“这一点,阁下在知道宋夏联军的时候便知道得清清楚楚,不是吗?”
“前些日子,我夏军左侧军烧了阁下大军的粮草,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很是过意不去。但没想到在此时竟然派得上用场。阁下何不借着这个说法,以大军没有后备军粮为由退兵,总比和宋夏大军孤注一掷最后大败涂地来的更体面吧。”她笑笑:“我也没什么想法,不过希望大夏能够在乱世里有一席之地,对得起大夏列祖列宗罢了。”
“再说了,我与阁下并未曾有什么深仇大恨,阁下也没必要对我抱着处之而后快的心情,不是吗?”
现下的确已经很夜,可营帐里的两人,却清醒得很。
倾阳长公主望着眼前人,她已经告诉他自己今夜来此的目的。她心里清清楚楚,能够与漠北谈判求得对方借此退兵,自然是极好的办法。这样一来,北境也能够避免生灵涂炭,她欠北宋的人情,还起来也不会那样吃力。
拓跋旦屡屡建立奇功,自然也不是个好糊弄的人:“殿下既然今日要来当一回说客,那怎么不说说,我漠北如若就此退兵,将会有何好处?”
眼前的倾阳长公主一听,将手上的茶杯缓缓放下,觉得有些好笑:“好处?阁下是要与我谈,阁下退兵之后,漠北会有何好处吗?”
“看长公主的样子,难道小王不应该提吗?”
“阁下觉得应该要什么好处呢?”倾阳长公主脸色一变:“本公主在此处可以告诉阁下,阁下若是退兵,没有好处;若是不退,漠北大军必定损失惨重。”她的一字一句,句句铿锵,让他心头为之一震。
“宋夏大军只是不善战,不是不能战,若是阁下真的要拼死一搏,正好也可以看看,这些年来,阁下威名赫赫的漠北大军,到底有没有长进。”她说,站起身,随意地打量打量眼前这位军功累累的皇子:“我以为,阁下会是个识时务之人,没想到也不过是张口闭口有何利益的小人罢了。”
“我奉劝阁下一句,各国博弈,利益固然重要,不过若是为了利益,失了道义和人心,就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买卖了。”她微微一拜:“我话已经带到,阁下如若还是与我张口闭口皆是利益利益的,那阁下也不用手软,自可放马过来。告辞。”
拓跋旦一惊,看着那个身影甚是潇洒地消失在他面前。她说的话不多,可字字句句正中要害。她知道目前这个光景,他拓跋旦最怕的是什么,最顾忌的是什么。
她自然是迫切的希望漠北退兵,可若是一味依傍大宋,那和败在漠北的铁骑下又有何区别?她今天来,当然首先是想到大夏,可如若大宋和大夏联手公然与漠北为敌,他漠北纵然有几十万大军自然也绝对是讨不了好。
他从前只听说过大夏的倾阳长公主如何如何心计无双,如何如何聪慧过人。他一向只觉得这不过是传闻,而传闻有失实。那日在哨站附近见到她,那一身风骨傲立于世,今日在此处见到她,的确是风华绝代,举世无双。
“殿下,就这样放大夏倾阳长公主离开?”营帐外,一个参将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那可是如今大夏权势最盛的辅政公主啊。我们若是挟持了她或者殿下直接杀了她……”
“然后呢?”他怒道:“然后大夏举国上下便可讨伐我拓跋旦,然后宋夏更有理由对我漠北下手。你这是要置我于何等境地?”
“末将该死。”参将跪在了地上。自己不过小小一个参将自然没有多想到这么深的一层,如今想来,想必她倾阳长公主也是料到这么一层才坦坦荡荡全无畏惧地跑来漠北大军的军营里吧。
拓跋旦坐在主位上,依然觉得很是惋惜。可这眼前形势如此明了,他若是强攻必定损人又不利己。可你要让他就此放弃,班师回朝,拓跋旦一身傲骨如何能放下如此自尊心。
“传令,即刻整顿,明日一早便回漠北吧。”良久,他叹了一生气,闹腾了许久,到头来,也不过如此罢了。怕是回了漠北,他自己也落不到一个比现下更好的下场。
若是早知道,他定不会像今日这般,一步错步步错。
“殿下,你可回来了。”还未过了城门,她远远地便瞧见邢尘在城门口来回踱步,慌张至极的形容。
“我不过去了趟拓跋氏的军营,瞧你一副紧张样。”她翻身下马,一整夜在风沙里耗着体力,实在是累极了,唔,还有些饿了。
那边邢尘过来牵过她的马:“殿下去了漠北军营?殿下去漠北军营做什么啊?殿下怎么不带属下一块儿去啊?”
她顿足,眼眸含笑:“没发现啊,你小子还挺多话的。要带你去我干嘛在你杯子里下药啊?再说了,你邢尘大人多厉害啊,我要是带你去,恐怕我们连人家的大门都进不了吧。”
那厢邢尘跟在她身后,天边泛起了一丝丝的天色:“殿下过奖。殿下下去还是不要给属下下药了,属下担心……”
“有什么好担心的,”倾阳长公主说:“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还分毫不损的。”
“可是殿下做什么大晚上的跑到敌军的大营里去啊,若是有个万一,属下百死莫辞。”邢尘看着自家殿下有些疲惫的侧脸,有些不大好意思,毕竟自己昨晚喝了那杯下了药的茶倒是睡得很好。
那边倾阳长公主却笑笑,眸中已经没有前几日的哀沉之色:“当然是过去让漠北退兵,你觉得你家主子我闲着没事干吗?大晚上的不睡觉去送死吗?”
“属下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不过,”邢尘跟在她身后:“漠北答应退兵了吗?拓跋旦可不糊涂,断不会眼睁睁看着到手的肥肉又溜走的。”
“不甘又能如何?左右他不是非要我李氏的鲜血为祭,没有胜算的仗,我想他拓跋旦也不会打来毁自己名声的。”倾阳长公主走在清晨的薄雾中。自从宋军入驻西城郊之后,城里的守卫也松懈了许多,将士们也不像先前对战漠北大军那般紧绷。
拓跋旦脑子聪明的很,倾阳长公主自己知道她昨夜的那番话代表着什么。她只是将拓跋旦心中一直不想承认的事情大大方方地摊开了同他说个清楚,退兵这件事,与其说是倾阳长公主游说,倒不如说拓跋旦自己心里本就有此意,只是找不到一个借口罢了。
是以她昨夜连夜出城,便是要去给他一个借口。她都亲自去找他了,再放不下来的面子也该放下了。
眼下走了一个漠北拓跋氏,又来了个北宋煜王,她大夏是招谁惹谁了,大过年的麻烦可是一点没少。
拓跋旦是武人心思,这次南下,若是可以一举灭了大夏,自然是好,其余的,他不会用其他手段逼大夏就范。可这北宋就不一样了,煜王是何等人啊?那个以一己之力铲除朝中异己的,声望极高的亲王。
说起来,他们倒是很像。都是那种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卑鄙无耻的人。
“漠北若是退兵,大宋恐怕也没有久待的必要。他们走了,我们也好早日回灵州城。”她说:“着人密切关注哨站方向,若是漠北大军有一丝一毫退兵的迹象,即刻来报我。”
“还有,煜王那边也派人盯着,如此节骨眼,我可不希望大宋那边给我整出什么新花样。”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