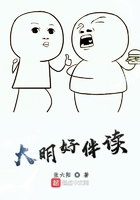教会学校是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世纪中下叶的清代教育领域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影响也十分广泛和深远。教会学校的产生和发展,是伴随着欧美各国对华的政治、军事及宗教文化入侵同步进行的,是在不平等条约造成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不断扩展的,它带有明显的文化侵略性质。同时,教会学校的存在,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材,并在介绍和引进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华传教士的早期办学活动
基督教会在华创办学校发端于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的传教活动。马礼逊1807年来华,1818年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教授当地的华侨子弟,被视为新教创办的第一个专以华人为教育对象的教会学校。这个学校的宗旨,是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同时也向西方(主要是英国)介绍中国。英华书院创办时间很短,所收学生不多,而且属于初级学校,所学课程除教义外,无非是一些粗浅的读写、识字内容,并不能承担起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使命。马礼逊本人的教育活动,远不如他翻译新旧约《圣经》和编印中外第一部《华英字典》的意义重要。因为这些译经和字典,为此后来华的传教士提供了语言方面的便利,使传教活动得以起步。马礼逊死后,在华传教士于1835年成立了马礼逊教育协会,这个协会在推动教会教育事业方面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它以促进英文教学,使中国人取得“西方的各种知识”为宗旨,为此它发起和创办了马礼逊学校。
1839年,马礼逊学校正式在澳门创立,这是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学校,被视为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嚆矢。在马礼逊学校之前,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夫人已于1834年在澳门创设了一所女塾,并在其后不久又附设了男塾。马礼逊学校在1835年到1839年正式开办以前这段时间内,便寄附于这所学校的男塾,并给予该校以经费的资助。据曾在马礼逊学校读书的容闳回忆,该校所收的学生,多为贫寒子弟,有的家长送子女人学,不过是为了得到教会学校的津贴以资赡养家庭,或培养子弟做个通事之类的洋差而已。学校所授课程主要为初等算术、地理、英文及国文。
1842年,马礼逊学校迁至香港,学校规模得到较大扩展,学生由原先的5名,扩大为1845年的40余人,新增三个班,教师也由原来的1人增至2人。马礼逊学校创办时间仍然很短,1850年便告解散,少数学生如容闳、黄胜、黄宽等三人,于1846年随马礼逊学校第一任校长美国人勃朗赴美留学。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五口通商条约》允许外国人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开放城市居住,并可修建教堂。其中,法国在1844年的《黄埔条约》中,还强迫中国承担了保护教学的义务。当年的12月,清朝政府被迫取消了延续已达100年之久的对天主教的禁令,并于1846年宣布归还教会财产。这一系列条约和规定,为西方各国的传教活动开了绿灯。教会学校也在上述五口地区迅速创办起来。
据不完全统计,以上海一地的天主教教会学校为例,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20年里,便先后出现了中等教育性质的徐汇公学(亦称圣依纳爵公学,1849年创办)、圣方济学校(1857年创办)、启明女学等;小学教育性质的学校有圣若瑟学校(1847年)、六童学校(1847年)、新闸学校(1847年)、土山湾孤儿院(1849年)、圣鲁意学校(1850年)、董家渡学校(1852年),学生人数约1500余人。由英美两国基督教会主办的学校则主要有圣约翰预备学校(1844年),A。P。M高等学校(1859年)、L。M。S中学校(1859年)和A。P。M女学校(1860年),学生人数约达600人。除此之外,英国东方妇女教育促进会的女传教士亚尔德西在宁波创设女学,为中国本土第一所教会办女子学校;1850年英国圣公会在香港设立的圣保罗书院、1853年公理会教士卢公明在福州设立的格致书院,均借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形式,取得较好的办学效果。
这一时期的教会学校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而带有明显的配合西方列强政治、军事入侵,借宗教与文化手段软化中国士民的动机。对此,美国学者露懿思曾在《基督教教育在中国之情形》一文中,详细论及:“基督教育之在中国,其起始为1842年……伊时反对外人之举最烈,故外人用种种方法使中国人民信任,而斯时适谋教育普及,实行开放门户主义,化除国籍界限,教会即开学校,初亦不过于宣讲圣经之外,教以读写知识,及算术字母而已。来学者大率为贫苦儿童,学校免其学费,且有津贴书籍事物者,其后逐渐进步,学校程度提高,且介绍西方学术。”这里所说的“开放门户主义”、“化除国籍界限”,实际正是西方列强凭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目的所在。而“谋教育普及”则为达到此目的的辅助手段。
教会学校的扩展与流布
教会学校在华扩展的过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842年以前为尝试性的初始阶段,代表性的学校主要为前述的英华书院、马礼逊学校及古特拉富夫人创办的女塾,集中在澳门、香港及东南亚的马六甲等地。1842年至1860年为第二个阶段,这个时期的教会学校得到不平等条约制度的庇护,获得较快的发展,分布范围也扩展到开放的五个口岸城市;在办学的规模和数量方面,天主教差会超过了新教。1860年至1900年为第三阶段。由于《天津条约》及《北京条约》不仅增开了十个通商口岸,并允许传教士到内地自由传教,这就使教会学校扩大到了沿海主要港口城市,同时逐步地深入到内地城乡各地,教会学校的数量和规模均有迅速的发展。在这一阶段,教会学校的办学手段及学校类型也趋于多样化。由于广泛地分布于城乡各地,因而与中国各种社会阶层及其文化、礼俗接触更为频繁;教会学校借助条约制度所予的种种特权,积极干涉或介入中国各级地方的行政、诉讼及文化教育事务,从而也引起了与中国士民更为频繁的纠纷或争瑞,有的并导致尖锐的冲突。但这一时期的教会学校也出现了教学内容及课程逐步系统化、深化,初级学校为主的学校类型逐步向中等教育增扩的趋势;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了少量高等教育性质的学校,在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方面,发挥了颇为重要的作用。1901《辛丑条约》签订后,教会学校获得了更多的发展便利,但由于经历了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人民频繁激烈的反洋教风波及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教会学校开始转向重点发展高等教育,以期培养少数高级知识人才作为代理人,实现其以华治华的战略目标。而在中小学教育领域,为了更有效地吸收或感召中国学生,并能够为中国士儒所认同,则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在教学内容中也增加了一定比例的中国传统知识。因此,1901年以后可视为教会学校的调整和深化阶段。这一阶段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之后。
教会学校在华的区域性分布,与西方列强在中国瓜分的势力范围有大体对应的关系,并以各国宗教差会作为分割势力范围的主体。自鸦片战争以来,各宗教差会逐步形成了各自较稳定的传教和办学的区域。诸如:北长老会在广东,公理会和圣公会在福州、宁波、上海,巴色会和礼贤会在广东,英长老会在厦门、汕头、台湾,美以美会在福州、江苏、浙江及华中、华北、华西,循道会在两广、两湖,浸礼会在山东、宁波,遵道会在湖南、信义会在两湖,公谊会在四川,内地会在西北、西南,等等。中国除西藏、宁夏、青海之外,几乎所有的省份、均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教会学校。
19世纪60年代以后,教会学校的数量增长很快。据不完全统计:耶稣会在江苏和安徽两省的学校,1878年至1879年有345所男校、213所女校,学生人数分别为6222名和2791名,而90年代末期,学生人数已达1.6万多名。另据1868年的《教会新报》第一期刊记;1866年耶稣会在华的义学及学堂数总共为53所,学生人数为946人;而1905年出版的《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刊记的耶稣会在华所立学校(不包括初等蒙学堂)总数,已达287所,学生人数约为14531人。这些数据因史料来源不同差别大,但学校及学生数量增加幅度很大,却是一致认同的事实。再以基督教教会学校为例,据1922年第五卷四期《新教育》统计:基督教教会学校1876年全国在校生约为4909人,到1889年增到16836人,13年中增加人数近3倍;而至1906年,人数又达到57683人,17年中人数增加又达3倍有余。再据《中国教会年鉴》统计:1912年基督教会学校学生人数已达138937人,这同1876年相比,36年间,学生人数增长了28.3倍。可见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确为教会学校发展的全盛时期。
总体而言,教会学校在华的扩展进程,与中国半殖民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是大体同步的,这说明教会教育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是与列强在华侵略势力的深入密切联系着的。因此。1842年和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以及相应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成为划分教会学校扩展进程不同阶段的里程碑;但就具体的学校而言,由于各国侵华势力的程度不同、各个差会或学校办学方针、办学时间或地点的不同,以及学校内部体制完备化的程度不同,各种学校往往又有自身的独特发展过程,并非一概而论。例如:基督教在华创办的第一所中等教育机构——北平崇实中学(1865年创办),便根据本校校舍的扩建、人员的扩充及学制、设备、课程等的完备程度,划分为六个发展时期:1865年后为创始时期,学校只设蒙学一馆;1885年后为进步时期,学校由长老会出资扩建校舍,人员补增,添设中学;1900年后为复兴时期,原位于安定门内二条胡同的校舍遭义和团焚烧,于1902年在安内大三条胡同购庙宇一所重建;1911年为扩充时期,学校募得巨款,校舍、设备及学生人数均有大幅度的增补;1923年为发展时期,试行新学制,设立初高二级中学和铅印、皮件二科职业教育;1927年进入改组时期,学校围绕教育部立案问题,进行一系列校务调整。
始创于1850年的上海徐汇公学也经历了自己的一段独特发展的历史。这所著名的天主教耶稣会创办的学校在1850年至1860年间,尚处于胚胎时期,教学内容也以初级的圣经知识和国文知识为主。1860年至1900年,为常规发展时期,学校人数有所扩大,学生除了学习法文、图画、音乐等科外,由于是时科举尚未废除,仍以传统的经史、诗赋、文词、书法为主,所培养的学生也多有应举中试者。1900年以后,由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影响日益扩大,新学日渐发达,国内要求振兴实业的主张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该校的课程也改变以往以国文为主,规定法文及其他自然科学为必修课,并对高年级的学生用英文或法文讲授算学、物理、史地等课。同时改组学制,分设中学院和上学院,使学校成为震旦大学的预科。这一时期是徐汇公学的全盛时期。
不同的教育类型,其扩展进程也往往自成一脉。以基督教会所创办的中等学校为例,据美国学者毕范宇在1929年12月《教育季刊》第五卷第四期刊文归纳,便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818年马礼逊英华书院的创办为标志,进入胚胎时期;1856年后进入发展时期,学校类型扩大,女学最显突出。其中,广州的真光女学,北平贝满女学,上海中西女塾最为著称。1898年戊戌政变后进入全面发达时期,学校的数量、规模、设备均有大幅度增扩,出现了像天津中西书院、辽宁文汇中学、太谷铭贤中学、汉口博学中学、上海麦伦书院等一批著名中学。并出现了国人主动接受西方文化的倾向和工读制的办学方式;这一时期的学校类型也有所扩展,出现了实业学校、聋哑学校和盲童学校、师范学校。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教会学校的批评也有所增加,如指责教会学校过分西洋化,忽视国文教学、课程欠系统、科目缺乏实用,教师素质偏低等等。教会学校与政府及民间的磨擦也有所增加。1921年以后,教会中等教育学校进入改革时期,并围绕着“中国化”和“基督化”的主题展开一系列的争议。
总之,教会学校在华扩展的进程,既有配合西方列强政治、军事及宗教文化入侵的因素,又有教会学校自身日益完备化、系统化及教学内容日益深化和中国化的因素。教会学校在华扩展进程,与中国近代教育的萌生和发展大体上保持了同步的对应关系,它的扩展客观上有助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知识的启蒙及传播。
教会学校的宗旨与教学内容
19世纪中叶以来,教会学校的办学宗旨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教会学校的日益扩展,它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变迁、列强侵华政策的不断变化调整、中国士民抵制洋教和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它也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办学宗旨和办学方式,以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并在新的环境下寻求一种最有利于它的生存和最有效地扩大其影响的途径。
教会学校在它创置的初始阶段。其目的“并不在教育人才以促进教育之进步,乃欲以学校为一种补助之物,以助其宣传福音之业”。故教学内容也主要是讲授一些粗浅的《圣经》教义和初级的读写知识、算术字母而已。教会学校最初显然只是传教的工具,而不是为了传播广义的西方文化知识,其创办的动机旨在提供传教的便利。这种简单的办学宗旨及内容、只能发挥极为有限的作用,其本身的存在既不足以引起中国士民的关注,所能产生的影响力也是微不足道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变故,大多有利于教会教育的发展。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的日益扩大,为教会学校提供了日益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的保障。中国国家主权的日益削弱和半殖民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中国士民对外国政治、军事及宗教文化介入的敌视,促使教会学校改变策略,调整办学宗旨,提高办学水平和质量,并以较优厚的物质待遇,来吸引中国人入学,通过培养出一批具有基督精神和人格、具有较高智识和能力的亲西方华人,来参预国政,控制中国各个领域的领导权力,进而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
1890年,中华教育会会长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曾对教会学校的宗旨做了认真的解释:“真正的基督教学校,其作用并不在于单纯地教授宗教,从而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一步给学生们训练”,使之“成为社会上及在教会中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之导师和领袖”。在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时,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便致函罗斯福总统,强调指出:“如果美国早在15年前就做到把中国学生之潮流引到美国来,并使这个潮流不断壮大,那么,我们今天就一定能够通过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们,来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一种最令人满意的又最为巧妙的控制”。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西方各国,显然面临着这样的选择:究竟是以夷制华,还是以华制华,这是东西方力量抗衡的情况下必须认真思考的策略。前者主要通过政治、军事、外交的手段来实现,并且已经获取了最大限度的利益,在权益既得之后,保持并扩大这种权益,则需要借助一种更为婉转、平和且具有长久稳定效力的手段,这就是大力发展旨在促进以华治华政策的教会教育。前述狄考文及詹姆士的言论,无疑是对这一宗旨的最好的表白。在此前提下,如何评价教会学校的作用,也需要变换一下尺度。《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曾指出:“教会学校之重要,并不关乎已设校数及学生之多寡,实可以其毕业生在国内及宗教上所占地位”证明之。教会学校养成的“多数之男女人士今皆身膺重要之位置,并于政治、教育、商业、及基督教会今后发展之情况,咸大有作为”,便是这一宗旨的最佳体现。为了贯彻这一宗旨,教会学校就需要扩大自己的优势,改善教学内容与课程,并且要适应学生今后在国内谋生及升迁的切实需求。
1897年8月,一位中国传教士周之德在《振兴学校》一文中,曾认真讨论贯彻这一宗旨的课程设置标准。他认为:中国国势之不振,概由于教育不普及和国人“多守旧而不知谋新”所至,在中国面临着推广学校、变通法令及寻求富国之策的重大课题之际,教会学校倘若仅以传教为宗,便不合大用;“若仍拘限人材,执守成法,必至无赞助行教之功”,他引用一位美国传教士的言论:“欲吾道通行中国,须备教会多设书院,广集会中子弟,礼聘中西教会通儒,教以圣经、英文、法文、德文、格致、天文、地理、电光、化算诸学、与及中国经史典籍,各种有用之书。令会中人材蔚起,然后简拔才全德备、献身事主者,责以重任,又要培植英杰,上达朝廷,下达草野”。周氏所论,是要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切合中国的现实需求、有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才能为中国国民所接受,进而扩大教会的影响。
进入20世纪,宗教界最终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欲有效地贯彻既定的教育宗旨,首先必须改善和充实教会学校本身。《中国基督教育事业》一书谈到课程设置的指导原则时,便提出了下列要点:其一,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应适应中国学生最深切的精神需求;其二,凡有关于中国人民之幸福者、有益于中国国民者,皆可纳入基督教教育内容之中;其三,要熟察中国文化之优点,而谋所以保存之;鉴别西洋文化之弱点,而谋所以避去之;其四,必竭力研究中国之宗教上、社会上、经济上与教育上之需要,研究一种适合于基督教的社会及中国人民需要之特种教育。在《基督教育》第4卷第1号刊载的一篇美国人的《基督教教育的特色》中,更明确地指出:教会学校的课程和内容,应最能实现学校办学的目的。
教会学校办学宗旨的调整,是为了“造成一种基督教的支配”,在中国创造一种适合于基督教教义的社会制度,是企图“导引中国民族运动之心理,得有圣教之精神,而进入于圣教之羊栈”。应该说,这些宗旨确实包含了促使中国彻底殖民化的意图。但与此同时,教会学校的改善和教学内容的科学化及课程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也为中国介绍了丰富的西方科学技术与文化,有利于促进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像1881年创办的天津中西书院,其课程内容包括:识字、辞句、琴韵、数学、地图、翻译、西法、文法、代数、天文、几何、化学、重学、微积分、航海测量、万国分法、富国策、地学、金石类考等内容。再如美以美会镇江女塾的课程内容包括:圣经、蒙学、算法、地理、游艺、诗歌、体操(第一年);此后逐年增设的课程有:植物、动物、英语、孩童卫生、四书摘要、数学、尺牍、宗教史、美国史、形学、万国通鉴、万国通史;泰西新吏、天方略解、格物入门、策论、地学等等,近百种。这些教会学校课程内容的设置,显然比中国旧式学校丰富,故尔教会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教会学校的类型及办学特色
教会学校的类型及办学章程,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多样化、正规化和系统化,这反映了教会学校在华滋生、发展及趋于成熟的主要过程。
在1840年前后,教会学校主要是蒙学或小学类的初级教育机构,且数量极少,学生人数也不过若干名而已。19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了中等教育性质的学校。在同、光二朝,普通中小学之外,又陆续出现了实业学校、工艺学校以及师范、法律、医学、护理、盲童、聋哑等专门学校。
19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教会学校的教育宗旨趋向于培养少数基督化的领袖人才,以期驾驭引导民众,控制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因而高等教育性质的教会学校开始酝酿并逐步发展起来。最早创办的教会大学,多在中等教会学校的基础上扩展而来。诸如美国圣公会主办的圣约翰大学前身是分别于1865年创办的培雅学堂和1866年创办的度恩学堂,这两个学堂在1879年合并后,遂于1892年增设大学课程;1896年扩建大学校舍,1906年在美国华盛顿立案。又如广州的岭南大学前身为1888年广州长老会香便文牧部创办的格致书院,1893年在美国纽约大学注册;东吴大学的前身则为上海中西书院,至1907年迁至苏州天赐庄,名称东吴大学。也有一些大学是几家差会协同创办的,如1905年开始筹办的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是由英美、美以美、公谊、浸礼四个差会合办,并且也是先设华西协合中学,进而扩升为大学,1918年英国圣公会也参加襄理学务。1909年成立的南京金陵大学,则是由基督会、长老会、美以美会三家合办的,此后又陆续有浸礼会、南长老会等参预协办。
在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教会大学有长足的发展。其中,综合大学除上述学校之外,尚有1909年创设于武昌的文华大学、1908年创设于上海的沪江大学、1911年创设于上海的震旦大学、1911年创设于杭州的之江大学、1915年创设于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1916年创设于福州的协和大学、1917年创设于济南的齐鲁大学以及1919年创设于北京的燕京大学,在综合大学之外,尚有若干医科学院,如1905年创设于广州的夏葛医科大学、1914年设于长沙的湘雅医学院、1906年创设于北京的协和医学校(1915年定名为协和医学院)以及创设于1911年的上海哈佛医学校。文理学院及法律、商业等专科教育则多附设于综合大学之系科,或由综合大学改立出来。如:之江文理学院由之江大学改设而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由金陵女子大学改设而来,协和文理学院由协和大学改设而来,著名的东吴法律学院则由东吴大学原设于上海的法科改扩而成,沪江大学则分设出商学院。
这些大学经费充足,教学设备齐整,并有相当雄厚的师资和图书,因而教学水平较高,同时逐步形成了各自办学的专长和特色。譬如:金陵大学的农林科,华西协和大学的医科、牙科,沪江大学的教育系、地理系与地质系,燕京大学的家政科、教育科、农科,东吴大学的法科等等,均在国内达到一流的水平。
教会学校的办学方式,还注意采用中国原有的学校模式或名称,以期迎合中国士儒的心理。譬如:书院及义学作为中国故有的学校称谓,便被教会学校所沿用。据1868年第三期的《教会新报》统计:1866年天主教在华创办的书院已达12所。基督教1905年时已在华创办的大书院、书院也达12所。而《教会新报》1868年第一期统计的1866年耶稣教义学,在华总数也达19所。这类义学,实际与传统教育中的蒙学、幼学性质相似;这类书院则相当于普通中学教育。
教会学校在行政上,多归属于各宗教差会管理经营。此外在美国还有由各差会的干事与代表组成的托事部,托事部为差会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选聘校长、教授,批准经济预算,并授权在华董事会经营学务。董事会主要由各差会在华传教士组成,间有一二华人,也无实权。差会是西方教会特派宣传与进行某种使命的一种临时团体,一旦使命完成,便无继续存在的理由。因此,教会学校在行政归属方面,尚没有形成稳定的体制,其惟一的出路就是逐步脱离教会的管束,转化为中国教育系统的一部分。这一点导致教会学校在管理和课程设置方面加强了中国化的因素,并且注重迎合中国现实的需求。
教会学校的学制和组织形式,大多抄袭本国学校的模式。英国人办的学校,多类似于英国的公学;美国人办的学校则多类似于美国的预备学校。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教会学校是西方教育的一种移植形式。办一般的中小学,无需任何许可证。但创办教会大学,则需要本国政府注册,取得给以学位的许可证。教会大学生由此可以获得与外国大学生同等的学历资格,就此而论,在华的教会大学也属西方大学模式的移植形式,仅在课程的设置和确定办学宗旨、手段方面,需要因地制宜,以适应中国的国情。
教会学校的经费,主要由教会捐集拨款,也得到少数金融集团的资助。除此之外,学校自己也经常捐集资金,在某些贵族化的教会学校中,学生所付学费高昂,成为学校财政的重要收入之一。例如:著名的上海中西女塾,每月须交修洋、膳洋及琴修洋共达10元,徐汇公学所收教外学生每年学费达120元,上海德文医学校每年的学费则高达150元,这样高昂的费用对于一般中下层家庭来讲,是无力承受的。即使学费交纳较低的学校,一般家庭也不易承担。所以许多教会学校逐步尝试半工半读的方法,解决学费问题。到1910年,一般男校工读学生已占学生总数的40%,女校则为50%。实行工读制,以缓解学生的经济困难,也使一般中等家庭出身的学生有可能入校学习,并有助于改造学生中普遍存在的轻视劳动的积习,但实行起来困难很多,据中华三育神学实行工读制后的介结:学生种菜每小时付大洋七八分或一角,但菜熟了所卖的莱价还不抵工资之半数;在工厂农场做工,仅机器设备的资金就需数万大洋,方能供给一百个学生工读的机会,这在一般的中小学校是无力实施的。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由于教会学校归属各个差会经营,因此教会学校的经营方针或宗旨,必须要与所属差会的政策互为表里。又由于各个差会大多各自行事,零散办学,这就导致教会学校一度存在体制混乱、管理不便等诸多弊病。为了统一协调教会学校的办学方针,并集中财力办好重点大学或中学,除了各个差会协作办学(如齐鲁大学由13个差会合办)外,也需要在广泛的教育领域中协调学务、解决各种教会学校共同面临的难题。在这一前提下,19世纪90年代以后陆续出现了全国性的宗教教育团体。这些团体在调整办学方针、编写教科书及推进教会教育事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酝酿于1877年,创力于1890年的中华基督教育会,便以增进教会在华的教育利益、推广学务为宗旨,并声称要“灌输吾人之学说于中国教育界”。建会后谋求在下列三个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一、编辑教科书以应教会学校的需求;二、谋教授的互助;三、探求及解决中国教育的一般问题。1896年正式成立的中国青年会(原名中国基督教幼徒会,或称公教青年会),则旨在联络教会学校学生、推进半工半读制度,并进而向教外的学校生徒灌输宗教教义。由李提摩太主持的广学会则力图在编译出牍图书、教科书,影响并进而控制中国官僚绅士及生徒方面发挥作用。在图书编印方面,广学会是赞助编译西洋哲学、宗教、社会、历史等类著作的主要机构,这个机构1893年的出版收入仅为800美元,到1898年激增至18000美元,5年内增加了22倍之多。广学会出版的刊物《万国公报》及麦肯齐·林乐知的著作,深受维新派的欢迎,并成为1896年维新派主政的湖南乡试举子的必读书。据统计:仅上海一地基督教中学所用的33种主要宗教课本中,就有17种系广学会编辑出版。可见广学会在教会学校全国性的教材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李提摩太公然声称:广学会刊行书刊是为系统指导中国未来官员的思想。为此,他罗列了一个包括文武官七品以上、教师自府学教授及大学教习以上,以及各省候补官、科举出身的文人和书香门第出身的妇孺在内的总数为44036人的施加影响的对象,建议“把这些人看作是我们的学生,对他们进行系统的教育”。他认为:只要这些上层社会的中国人“深悉各国养民善法,然后愚民办可渐开门径”。作为一个宗教文化团体,广学会的作用已不限于教会学校内部,而是将教育手段施展到广泛的社会领域,这一点也正好说明:一些宗教文化教育团体的成立,不仅在于解决各个教会学校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或协调各个差会及教会学校之间的一般关系,也在于将宗教教育的影响范围由教会学校扩大到社会各个政治文化阶层,有系统、有步骤地开展教会学校之外的社会教育。这一点实际可视为教会教育的一种新的类型。
总之,教会学校在华创办的成就是显著的,教会学校的办学经验、管理模式及章程,为中国近代教育所取鉴;教会学校的课程教材,在外语、自然科学及妇女教育方面所做的工作,也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教会学校也为中国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人才。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传教士期望通过教育,来控制中国的主权,支配中国的教育,并使中国彻底基督化、殖民化,但实际的后果却完全背离了这个初衷。在这一点上,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和爱国主义传统,最终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