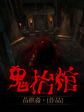言屺将言泺抱上马车后,言岳在外驱使马车。街上的行人看见马车上相府的标志,都自觉退让两旁。车外一片热闹嘈杂,车内的气氛可谓是到了冰点。
似乎早料到了这一点,上车前言岳就把欲进马车七七拉住坐在车外,以防被殃及。
言屺自上车后,就再没看言泺一眼,即使如此,言屺还是气的不行,可又偏偏没处发火,总不能对着尚未清醒的言泺破口大骂吧,要骂也得等人醒了再说。
想到这,言屺又催了催车外的言岳,让他快些。马车的速度是加快了不少,可碰到坑洼处,又颠簸了许多。言屺不得不看着些言泺,生怕她磕到碰到。
可这一看,便再也挪不开眼了。言屺恨不得原路返回,将夏朗一家子揍一顿,好好的姑娘被他们欺负成什么样了。
且不说衣裙上的脏污,一块一块的,就够让人不忍直视了,那脸上的红印更让人触目惊心。好看的柳叶眉不安的皱在一起,言二爷忍不住心软了。
他拿出身上干净的帕子,小心翼翼地替女子擦脸,擦的差不多了,收了手,又凝视着她,狼狈的少女与多年前的小女孩慢慢重合到了一起。
数年前,言屺第一次见到言泺时,言泺还只是个小女娃,小脸上脏兮兮的,警惕的打量着他。言屺第一次感到心软,蹲下身,用手擦了擦她的脸。
“跟我走,好不好?”言屺诱哄着,全然忘记了自己原先是打算将这小女孩托付给别人养来着。
许是言屺少年的皮囊太容易蛊惑人心,小娃娃开口,声音糯糯的,“我跟你走,那你要满足我一个愿望。”“只要你跟我走,我就满足你好不好。”言屺答应道。
“我想要洗个澡,换上干净的衣服。阿姐说过,她不喜欢宓儿脏兮兮的。”说着说着,小女娃抽泣起来,眼泪珠子忍不住的往下掉。
言屺知道,言泺一直都爱干净,府里但凡有一点灰尘,她都会浑身不舒服。思及此,言泺衣裙上的脏污便更显得碍眼了。
幸好,马车里常年备有自己的换洗衣物。顾及男女大防,言屺将将褪下言泺的外衫,换上了自己备用的衣衫,又用披风将言泺裹严实,才将她抱下马车。
大夫已早早在廊下候着,言屺径直将言泺抱进房里,老大夫战战兢兢的替言泺把脉。“如何?”大夫听见言屺的声音,忙不迭说道,“请相爷宽心,小姐的身体并无大碍,身上的外伤将养一段时日便可大好。老朽这就去写药方。”
“慢着,小姐满身是伤,怎会并无大碍?难不成大夫你是个庸医,医术还不如本相这个门外汉?”言屺悠悠说道。
老大夫诊过许多达官显贵,知道里面的水深,当下按下心中的疑惑,顺着言屺的意思答“是老朽诊错了。小姐今日受惊受寒,外伤严重,身体根基受损,没个把两年,难以恢复。”
“去吧。”言屺说道。“爷,你这是?”言屺打断言岳的发问,“等会儿你拿着我的令牌,去宫里请个可靠的太医来,不可耽误。顺便帮爷我请了明日早朝的假,就说身体不适。”
随后不知想到了什么,言屺气道,“小丫头,自己惹出来的事,还得爷来给你擦屁股。”
翌日,早朝结束后,宫里派了人请丞相进宫。彼时,言泺还未苏醒,言屺捧着药碗给她喂药,头也不抬道:“把公公请到厅堂里好生招待,就说本相身体不适,起身还得费些时间。”
一炷香后,言屺才放下药碗,慢悠悠地踱步到偏厅,跟公公离开。走前留话:小丫头醒了之后,看好她,不许她出房间,也不许人探望她。
宫里,“微臣参见陛下。”言屺行礼道。“爱卿平身。”“爱卿今日何故未来早朝啊?”皇帝询问。
“微臣昨日回府后,便感身子不爽,请了大夫来看,只说是气结于心,不慎感染了风寒,怕过了病气给陛下,便请了一日的假。”
言屺身上穿的还是昨日的便服,一夜下来,衣衫上有了些许皱褶,使整个人看着有些憔悴,再加上不时的几声咳嗽,倒真显得生病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