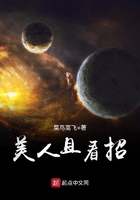玛琳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包括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她都完全不清楚。
事实上在她因为恐惧与伤痛完全展开自己血翼的时候,身体的自我保护本能已经将她的意识与感官完全封闭,隐藏起来。
从医学角度来讲,这叫休克。
——本应该如此才对。
“那么,谁来给我解释一下,这个桃园又是怎么回事?”
玛琳看着空中随风飘舞的桃色花瓣,不觉皱起了眉头,如果眼前的东西是敌人造成的幻觉的话,这个幻觉未免也太过温柔。
“简单地解释一下:这是我家,我家还蛮大的。”
“不够大的话也放不下你这么大个身子。”玛琳叹了口气,抬起头面无表情看着飘在天上的那个白色蛇头,“我该感谢你邀请我来你家玩吗?你家又是什么?”
“嗯,古炎国语解释起来挺麻烦的……”白蛇温和的眼睛转了几圈,似是在思考些什么,“用你们罗德岛博士说过的话进行说明好了——这里算是炎国人民集体潜意识集合的所在地吧。”
“这样,所以这里是桃园。”玛琳伸出手捉住飞到眼前的一片花瓣,那花香沁人心脾,“话说回来你打算一直用这幅模样跟我对话吗?老仰着脖子还蛮辛苦的。”
这话让白蛇一时语塞,在深深地看了玛琳一眼之后,它往天上一飞,消失在云朵中。
玛琳仍然抬着头打算看它接下来打算怎么做的时候,身前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好了,现在你可以低下头来了。”
然后她看到了一个宽袍大袖的白衣男子站在那里面带微笑地看着自己。
“你还真喜欢祖平那张脸啊。”
“唔?没想到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会是这个。”白蛇摸了摸鼻子,接着一挥手地上便多了地毯与酒菜,他席地而坐自顾自倒了杯酒,“你还是一如既往地有趣,连我为什么把你拉进这里都不在意吗?”
“不然呢?”玛琳毫不客气地坐了下来,“这地方是你家,你为刀俎我为鱼肉,不如随遇而安。”
白蛇喝酒的手顿了顿,眼眉微抬:“有时候无畏与无知只有一纸之隔,但是很明显你并非后者……相对的,一个无畏的人也不会被那东西造成的噩梦吓到魂飞魄散——哦,这个是炎国的说法,按照你们的说法应该叫失去意识休克。”
他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重新看向满不在乎的玛琳。
“如果不是我在这把你给拉到这里来的话,你知道你接下来会面对什么样的麻烦吗?”
玛琳摇晃着酒杯,盯着里面琥珀色的液体,随口回答道:“嗯,这点我心里还是有数的,只不过我相信牧会帮我解决这些麻烦。话说回来,酒不错。”
“那个萨科塔小女孩吗?原来如此。”白蛇顿了顿,意味深长地看向她,“那么下一个问题,你究竟在它威压下看到了什么,才能让你如此恐惧到了这般地步呢?”
“呵,这是你的地盘,你自己直接去看不就好了?”玛琳笑了笑,微微呷了一口杯中酒。
“那么,恕我失礼。”
白蛇点了点头,接着双目光芒大盛。片刻之后,他收敛了眼中的光芒,面色古怪。
“要是你看之前跟我说一声我这边也会现场重播的话,能稍微好些。”玛琳长出了口气,微微颤抖的手将酒杯放下。
白蛇却没有回答,只是神色复杂的盯着眼前的萨卡兹人。
沉默没有维持多久,他还是开口了:“……很有趣。我在那里面看到了很多人的死亡,有过去的死亡,也有未曾发生的死亡……它所能唤醒的,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最畏惧的东西。由此看来,你所畏惧的应当是死亡才对。”
玛琳微笑,拈住一片飞舞的桃花。
“但是在这些种种的死亡的画面之中,我没有看到你的死。”白蛇重新端起酒杯,微微抬头,“最后击溃你心防的,是那个萨科塔小姑娘的死状……罢了,这东西看来你自己也不想回忆起来。”
她将花瓣置入酒杯之中,重新倒满:“于是,你有什么结论了吗?”
“你……是圣人吗?”
这话让正在喝酒的玛琳呛到,剧烈地咳嗽了起来,一番折腾后她擦了擦眼角,抬起头:“你这话说得有点好笑啊,难道一般的考虑不是我贫瘠的想象力想象不出自己是怎么死的吗?”
“你又不是没经历过生死。”
“啊,说的也是。不过我也远远谈不上圣人这个水平吧?”
“至少在我经历过的这几千年来,像你这样的人屈指可数。”白蛇这般说道,面带回忆之色,“能将他人的生死置于自己生死之上的,十指之数而已。”
玛琳抿了抿嘴,说道:“太过了,话说你把我拉到你家来就只是为了谈这个吗?那接下来让我问个问题吧。”
“你们情报商常玩的一个换一个吗?”白蛇似乎很有兴趣的模样。
“算是吧,如果你希望这样的话。”玛琳点点头,接着神色一正,“那个叫年的人,是你安排过来的?”
白蛇点了点头:“没错,而且其他事情也正如你所想的一样。”
——也就是说,平江所发生的一切都在你们的掌控之中么。
玛琳微微咋舌。
既然白蛇肯定了她所想的内容,那么无论是万嘉物流的所作所为,还是万嘉物流背后之人的谋划,都是在蛇的眼皮底下搞事。蛇知道一切,却选择纵容他们的行为。
——目的何在?
白蛇语气幽幽地说道:“人向往光明与温暖的火焰,但是只有在真正碰触了被灼伤之后才知道,很多东西看上去美好,实际上很危险。”
“你知道吗,我挺讨厌你这样说话的。”玛琳一脸嫌弃的看向对方,“不过算了,大概能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了。”
“哦?你真明白了吗?”
玛琳翻了个白眼,当场化身谜语人:“如果有人想要玩火,那便让他们去烧,疼了之后自然他们就知道火是不能玩的东西了。强压着不让玩的话反而会让他们偷偷摸摸地玩起来,只要房子不烧起来就没有问题。现在火烧疼了玩火的人,作为管理者就可以告诫他以后不要再玩火了。
“你看,如果你喜欢这种说话方式的话,我也可以。”
“嗯,火候还差了点。”白蛇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评价道。
“那还真是不好意思,毕竟我还年轻,不像你这样已经变成老不死的东西了。”
白蛇一怔,随即大笑起来:“哈,那我期待着你到我这个岁数再跟我说话。”
“免了吧,我只希望我们以后再也不见。”玛琳摆了摆手,拿起一块点心,“好了,接下来轮到你了。”
白蛇歪着脑袋摇晃酒壶,问道:“这次的事件的结果在我这里看来是很正常的,但是在你那里看来,算是被一个意料之外的事件给打乱了才出现了正常解决的转机,是这样吧?”
玛琳点点头表示认同:“没错,这种事情通常被称作机械降神来着,原本解决不了的问题突然掉下来个鬼东西把问题解决了。”
“有趣的说法,这是你们博士说的吗?”
“除了他以外也没人会说出这种无根无源的典故了。”玛琳长出一口气,注视着白蛇的眼睛,“你想知道,如果没有那玩意的话,我打算怎么解决平江这个石铜俑事件是吧?”
“我洗耳恭听。”
“其实非常简单:把石铜俑技术的存在告知炎国的所有感染者,同时也把这个技术的存在扩散给泰拉其它几个大国——比如绝对不会在使用这项技术上产生道德犹豫的乌萨斯。”
玛琳语气平淡,仿佛在说自己打算出门买瓶苏打水一样。
白蛇眼神一凝,语气染上几分情绪:“你打算威胁炎国订下城下之盟吗?”
“我看起来有那么幼稚吗?”对此,玛琳无动于衷,“任何一个大国向来都是不会接受任何威胁的,所以威胁了也没用——我只是会那么做而已。”
“你知道这样做会有多少人死去吗?”
“你说的好像我不这样做就不会有人死去了一样……而且古炎国语不是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吗?”
玛琳浅笑,饮酒,随后又问了一句:“还是说,在你的眼中看来,感染者不在‘百姓’之列呢?”
看着白蛇无言以对的样子,她笑着耸了耸肩:“你看,我们的分歧就在这里了,你们不把感染者当做人来看,而我们认为他们仍然是人,既然是人,就应该重视他们作为人的生命,就应该告诉他们即将面对死亡这件事。
“而那之后,是选择接受死亡抑或是奋起反抗,都只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了。总不能你们一句‘请你们感染者为了我们普通人更好的生活去死吧’就让他们去死了吧?而且一直以来泰拉的统治者们可没什么资格要求感染者为了他们的利益去死。”
“炎国对待感染者的态度——”
玛琳冷笑起来,讲了个笑话:“呵,西边的奴隶主让奴隶饿着肚子住在窝棚里劳役,东边的奴隶主给奴隶吃饱饭住在草屋里劳役,于是东边的奴隶主对奴隶说:我对你们真是太好啦!你们要知足!老老实实为了我去死!呵呵呵。”
比刚才更久的沉默,接着白蛇长出了一口气:“也就是说,这场机械降神实际上救了的是炎国吗?”
“我可一点都没有失望哦。”萨卡兹女人笑着,用反派的笑脸。
“罢了,我只能说你不愧是最接近魔王的存在。”白蛇摇了摇头,深深看了眼前冷笑的萨卡兹一眼,“然后你想知道靖原军变到底是什么情况吗?”
玛琳摆了摆手:“我个人对炎国上层争权夺利的事情不感兴趣,你应该跟惊蛰雨祀她们说,去跟射声营的幸存者说,而不是跟我说。”
白蛇咧了咧嘴:“你倒是会做生意……算了,那这件事的始末就拜托你来转告给他们:射声营里有人知道石铜俑试验的事情,他们打算把这件事情捅给当时的皇帝听,然而他们不知道在这件事上,皇帝是支持石铜俑试验的。所以从行为上来讲,射声营对于当时的皇帝来讲,不忠。”
“就这么简单?”
“朝堂上的事情,有时候没那么复杂,尤其是炎国这种君权大于一切的地方。”白蛇平淡地说道,“总而言之,这件事情会到此为止,内阁会给靖原军变的死难者平反,同时也会停止关于石铜俑的任何试验,并且追究相关的责任人;但是相对的,惊蛰和雨祀这两个人,要离开炎国。”
“这算是什么交换?”玛琳歪头,不满的说道,“我怎么感觉你刚才在忽悠我?”
“现在的炎国,皇权还不能被动摇。”白蛇放下酒杯,表情严肃,“我想要什么,你应该最清楚不过了。”
“那我想要什么,你难道不清楚吗?”
“别开玩笑,你想要的东西不是一两道法律就能解决的,你真正面对的敌人是人心。”话音落下,白蛇抬起了头,看着逐渐摇晃的天空,面色古怪,“你家的那个萨科塔还真是有够厉害的……居然能影响到我这里,罢了,日后如果我们有缘再说吧——和你聊天还挺有趣的。”
“呵,我倒是希望跟你后会无期。”
玛琳说完,只感觉眼前一黑,再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的是牧那张焦急而苍白的脸。
“真是,让我好担心啊你这笨蛋!”话音落下,牧紧紧抱住了玛琳。
“牧,我们回家吧。”
“好,我们回家。”
牧架起玛琳,抬起头,走向罗德岛的同伴们,而在她身后,是逐渐跃出地平线的太阳。
——卷五,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