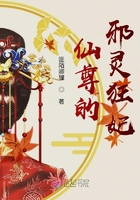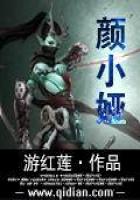“我一直都知道,我一直都希望能够帮爹分担,”薛淼儿垂眸道,“可是爹不让我插手山上的事情,什么都不让我管。或许在爹心里,儿子才能帮您做事……”
“没有,爹从来没有嫌弃过你。”薛天朗有几分慌,“爹是舍不得你。”
没有薛淼儿,这些年来他的思念又往何处寄托?
心爱之人离开得那般猝不及防,以为他们之间才刚刚拉开幸福的序幕,却不曾想,两人的缘分那么快就落幕。
“爹,女儿也舍不得您。您要知道,不让女儿对您好,也是一种自私。我就是想要一个答案,不管什么事情,我不想稀里糊涂的。求求您,告诉我好吗?”
薛天朗喉结艰难地动了动,半晌后长长叹气,道:“淼儿啊,爹真的希望你能一辈子都不知道。但是或许,也是爹想错了。”
“爹,”薛淼儿握住他的手,“女儿长大了,可以和您分担了!”
“爹只是想要你活下来,仅此而已。”薛天朗又是常常叹息,脸上露出痛苦之色,眼中有因为回忆而生出的绝望,捏住桌角的手无意识中已经青筋暴起。
这个沉重的秘密,压在他心头十几年,几乎已经成为他难以承受之重。
今日说起来,他也是万般滋味在心头,有些冲动,所以便关了门,和薛淼儿说了实话。
“淼儿,你要记住,爹今日和你说的这些话,对谁都不能说,要烂在心里,知道吗?”
薛淼儿已经长大,有自己的主见了,如果他再不和她说实话,不知道她还能做出什么样出格的事情。
“我知道。”薛淼儿觉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里,期盼已久的真相呼之欲出。
不知道为什么,她没有自己想象那般轻松激动,反而有一种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压抑紧张。
“淼儿,你娘……”薛天朗的右手抚摸着左手的扳指,眼中露出痛色,“我从来没有和你说过是怎样和你娘认识的,对吧。”
“何止这样?您从来就没有提起过我娘。”薛淼儿道。
她一直以为自己是姨娘所出,没心没肺地长到了十一岁。
十一岁生辰那日,薛天朗喝醉了酒,趴在桌上哭得像个孩子。
他说:“宦娘,你怎么能那么心狠,撇下了我们父女自己就去了!”
薛淼儿就是再傻,也听出了不对劲。
这时候姨娘很慌乱,一边让她回去休息,一边去扶薛天朗,说:“爷,您喝多了。”
不管她如何掩饰,薛淼儿还是刨根究底,到底挖出了自己的身世。
十一二岁是爱幻想的年龄,所以她对自己未曾见面的母亲有过很多想象。
要说多么深刻的感情真没有,但是她很想知道爹娘当年的旧事。
可是除了从姨娘口中知道她娘当年因为难产而终外,并没有知道其他任何事情。
刚开始她以为姨娘有所忌惮,后来才发现,后者真的是知道得不多。
薛淼儿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薛天朗身上,可是每次只要她一开口,薛天朗就情绪低落到无以复加,甚至借酒浇愁,却什么都不肯说。
几次下来,薛淼儿便也不敢问了。
她从小不缺母爱,她是薛天朗唯一的女儿。
薛天朗妻妾有十几个,但是相处十分融洽,都是安分守己,不争不抢的那种;她们都没有孩子,因此都把薛淼儿当成心头肉。
看薛淼儿长大之后天真烂漫、傻白甜的性格就知道,她过往生活中并不缺爱。
薛淼儿对生母的感情,大概就是遗憾而已,要说为之伤心欲绝,那也并没有。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绝大部分靠相处。
薛淼儿听生母的事情,更像听别人的故事,仿佛和她没有关系,她只是发出观众的感慨。
可是她知道她爹很在意。
她记忆中薛天朗有限的几次失态,都和她们母女有关。
所以这次她搬出了生母,就是一定要逼薛天朗说实话。
“我和你娘认识的时候,已经坐着山上第一把交椅了。”薛天朗目光似乎停留在窗棂上,但是又没有什么焦点,整个人沉浸在回忆之中。
那时候他年轻气盛又风头无双,怼天怼地,总觉得自己日后能够大展宏图,甚至建立新秩序。
因为天高皇帝远,也因为他规模其实并不大,所以并没有引来朝廷的围剿,让他很是膨胀。
某日听手下在山下的探子说,有一队江南商队要途径附近,看车辙印记,猜测车上应该装着不少金银,薛天朗摩拳擦掌,骑上爱驹,手舞大刀,一马当先地从山上冲了下来,身后跟着他的喽啰们。
没想到,那些人丝毫抵抗都没有,放下车马就落荒而逃。
薛天朗向来劫财有道,只要对方不抵抗就不伤人,也不劫色,所以他对眼前的状况十分满意,让人清点物品,防止有人中途偷盗,然后运回山上。
可是没想到,马车上竟然还剩下一个姑娘。
那姑娘明眸皓齿,相貌姣好,却因为眼前的情况而吓得花容失色,抱着个小包袱缩在马车一角瑟瑟发抖,口中不住地道:“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薛天朗看着她干净澄澈的眼睛,心忽然像三春的湖水,被风吹皱。
后来他才知道,那叫一见钟情。
他把那可怜兮兮的姑娘带回了山上,知道她叫宦娘,死了父母,下人护着她回乡,没想到路上遇见了他。
“宦娘,你留在山上给我做压寨夫人吧,我喜欢你,以后一定对你好。”薛天朗直抒胸臆。
宦娘起初自然是被吓坏了,但是薛天朗好容易看上了一个姑娘,对她自然十分有耐心,百般讨好。
宦娘眼里、心里慢慢有了他,看他的时候眼睛里像蕴藏了星河一般闪亮。
“你娘多傻,我就是一个土匪,还抢劫了她;就这样,她还是喜欢上了我。”薛天朗自嘲地道,因为回忆到两个人的甜蜜,脸上不自觉地露出几分笑意。
那些美好的过往,镌刻在记忆之中,历久弥新。
“可是她就是不松口留下,她总是说要走,明明她都已经喜欢上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