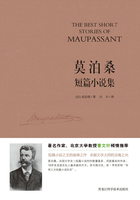贞白端过药碗,把瓷勺搁在案上,看着他这副生不如死的模样,淡声道:“放心吧,没有伤到筋骨。”
看着递到唇边的药碗,李怀信一脸提防。
贞白道:“一口喝了吧。”
李怀信皱眉,什么玩意儿就想让他喝?
贞白道:“我没必要多此一举救完你又毒死你。”
李怀信当然知道,她现在要捏死他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轻松,根本用不着下毒,可谁知道这个不要脸的打的什么不要脸的主意,这又是碗什么不要脸的药。
他发不出声,只能咬牙切齿地用气音道:“拿开。”
贞白有些茫然,她方才检查完他的身体,说了没有伤到筋骨,也就不会成为废人,只需好生静养就能恢复,不懂这人究竟发的哪门子邪火?
她问:“不喝吗?”
喝个屁,他真想一抬手把碗给掀了,再把这个不要脸的掀出去,不,打出去!
贞白也不强求,把药碗搁在了床头案前:“如果想早点恢复的话,明早你自己喝吧,调养身体的。”
说完,贞白转身,坐到了方桌前,背对李怀信,盯着面前的油灯出神,她思绪纷乱,要将这两日发现的线索重新梳理一遍,小曲失踪,王六之死,竹棺还有那两具尸骸,为什么老者身上系着锁阴绳和小曲的生辰八字,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为什么锁阴绳未断,老者的魂魄却散尽了,诸多疑点都解释不通。
还有只有三年命数的小曲活到了现在,她是借了谁的命数?
不是老者的,也不是另一名死者的,贞白盯着火苗的目光蓦地一沉,难道是:王六?
小曲是王六夫妇的命根子,他为了女儿短寿二十年也不无可能,而且他如今死于非命,连魂魄都丢在了乱葬岗里。昨日她在王六灵前查探过,他的魂魄应该是闯入乱葬岗后,被里面的噬魂鸦啄散分噬了,所以只剩个躯体被李怀信带了出来。
贞白想不明白,她曾经一个人无所事事的时候翻过些道术藏册,但也未曾多做留心,因为其中很多有违天道,或教人投机取巧走捷径,若是心术不正,易引祸端,贞白就只粗略一遍看完,用来消磨时间了,所以对这些不是特别明白。
贞白想起李怀信的来历,转过头问:“你知道借命数吗?”
没料到贞白突然发问,又诧异这个问题,李怀信张了张嘴,嗓子烧得说不出话。
贞白起身走近,端起案前那碗药,捏着他两颊撬开嘴就灌了下去,李怀信猝不及防,差点呛着。
药虽苦涩,但入喉湿润,干烧的嗓子顿时好受了许多,他一开口就想骂人,但被贞白捏着两颊,只能把骂人的话和着汤药吞下。
贞白松开手,把空碗搁在一旁:“你知道怎么借吗?”
汤药一半灌进嘴里,一半沿着下巴流进脖子里,打湿了被角,好在润喉之后他能发出点声音:“借命?你倒说得好听,无非就是以命换命!”
“怎么说?”贞白试着去理解他的字面意思:“一生一死吗?”
李怀信冷哼:“我就知道,你不可能是什么善类。”
贞白不理会他的针对,问:“但如果我只借二十年呢?”
“哪有借什么十年二十年的,你想得倒美,是不是你想借个八百年你就拉十个人串起来杀啊。”李怀信道:“一生借一次,你活的那刻他就得死,别琢磨着长生不死去害人,做这种逆天改命的事,就算苟且偷生也不会有好下场。”
李怀信心想,就凭她问的这个问题,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留在世间绝对是个祸害,非除不可!
贞白将那句你活他就死,以命换命,一生一死的话翻来覆去的琢磨。
难道不是王六,否则照李怀信所说,小曲三岁之时,王六就该丧命了。
如此一来,这三个人都排除了,贞白不得不重新梳理,目光若有似无的落在李怀信耳侧,沉思之际的瞳孔散了焦——
李怀信被她盯得心里发毛,这不要脸的落在他脸上那赤裸裸的眼神,肆无忌惮得让人愤怒。
他堂堂大端王朝二殿下,太行道掌教千张机亲传弟子,是何等尊贵的身份,真是色胆包天了连他的主意都敢打!
被人当做观赏物一样盯着非常搓火,可他现在是个全瘫,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李怀信强忍火气:“你看够了吗?!”
贞白正琢磨王六找人给小曲打造的闺房,思路被突然切断,涣散的瞳孔聚焦在李怀信脸上,有些茫然:“嗯?”
“出去。”
贞白一时没反应过来,看着他。
李怀信搬出礼义廉耻来:“男女有别你不知道吗?!”
“什么?”
装什么大头蒜啊,李怀信锉了锉牙:“什么时辰了,你还要跟我窝在一个房间吗?”
贞白适才听懂对方的意思,道:“这是我定的房间。”
她把床都让出来了难道还要把她赶出去?
即便知道男女有别,她还得在此多待两天,没有再开一间房的钱。
哪有做客的给主人下逐客令的道理,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李怀信愣了愣,猛地意识到这个理儿,又猛地意识到自己浑身上下一个钢镚儿都没有,然后还不着寸缕,这处境太他妈憋屈了,他咬牙问:“你到底想怎样?”
贞白拧了一下眉,居然认真的思考起他的问题。
李怀信跟着拧起眉,在心底打算,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屈服。
贞白想好了,从袖中摸出一个钱袋子:“我要这串五帝钱。”
李怀信脸色骤变:“你休想!还给我!”
贞白轻轻捏了捏钱袋:“是遭阴兵撞魂吧,已经碎了,若还给你的话,你身上阳气冲煞,里面的魂魄就会散。”
李怀信苍白无血的嘴唇微微颤抖,这女冠果然知道,所以昨夜给他驱尸气时,掏出了这枚钱袋,是以免伤到里头的魂魄吗?
他恍然意识到,这女冠阴气及重,整个气场就是一块移动中的养尸地,用她来以阴养魂,再合适不过。
“你——”
贞白知道他想问什么,坦言道:“我只是想问卦。”
问——卦?跟冯天?
现在的李怀信虽然很不愿意去说冯天无能,但是他也做不到昧着良心告诉这人冯天算卦精准,可若是他说冯天算不准,这人就不给冯天养魂了呢?
李怀信张了张嘴又闭上了,干脆默认吧,又不放心把冯天放在这人身上,谁知道她什么时候会作乱。
李怀信百感交集:“你要问什么卦?”
贞白目光清冷,须臾才答:“我想问,是谁把我钉在的乱葬岗,我要找到那个人。”
她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那人是谁,不知道人在何方,更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突然醒来,她就被困在了长平乱葬岗。
李怀信心里一紧,她是真的一点儿也不知道吗?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也忒冤了!
他揣测:“是仇家吧?”
“仇家?”贞白低声呢喃,摇了摇头,笃定道:“无恩无怨,何来仇家?”
这可说不准,有时候结下梁子你自己都不知道,比如他在太行山上养的那条小黑狗,跑到菜地里刨死了刚发芽的秧苗,辛苦劳作的小师弟直接把他恨上了,但恨归恨,除了私底下嚼舌根,又不能把他怎么着,而且打狗看主人,也不敢把他的黑狗怎么着,用冯天的话怎么说来着,哦对,仗势欺人,他的狗,就是狗仗人势!
这小师弟没办法,守过几次庄家,撵过几次李怀信的狗,有次惹急了捡起石头砸,这狗跟李怀信一个德性,在太行称王称霸,直接扑过去把人大腿咬掉一坨肉。小师弟哭哭啼啼向掌教告状,要求把那只畜生送走,结果就是李怀信给爱犬撑腰,掌教袒护,然后关了那条狗三天静闭,放出来照样祸害四方。
那小师弟哑巴吃黄连,没地儿说理去。
这条狗私底下给他招了多少怨李怀信不知道,反正小师弟若没有告到掌教那去,他可能依旧不知道。但因为这事儿他自此没太放养小黑,除了冯天带它训练规矩以外,一般都会拴在柱子上。
李怀信没有道破,既然这女冠想找冯天问卦,就一定会好生养着五帝钱里的散魂,只是:“若把五帝钱放在你这,冯天被撞散的魂魄需要多久才可以聚形?”
“不知道。”
“什么?”李怀信对这个答案非常不满。
“至少他不会魂飞湮灭。”
李怀信倏地一震,就为这句话,他决定赌一把。因为好不容易才将冯天这捧散碎的魂魄拘入五帝钱内,却发现它越来越弱,仿佛随时都会消散殆尽。他很害怕,他怕冯天不在了,永远都不在了,从这个天地间消失,自己却连他一缕魂都留不住。
李怀信胃里反酸,眼睛发涨,只好不动声色闭上眼,强忍着心口那一阵抽痛。
一夜共处相安无事,贞白就像入定似的背对他坐在方桌前,到清晨醒来,油灯已经燃尽熄灭,她只换了个一手支额的姿势,李怀信适才卸下内心的设防,呼出一口气,勾了勾手指,惊奇的发现自己居然能动了。他费力的抬了抬胳膊,一只手划出了被褥,格外绵软,他不泄气,又动了动腿,就听见门外一串脚步声,止于房门前,敲了敲:“道长。”
是赵九。
贞白起身拉开门,赵九拿着一袋包子递过来,用纸包卷着,还腾腾冒着热气:“早啊,我知道客栈里有吃的,但还是想着给你带点来,灌汤包,鲜肉剁的。”
贞白接过,道了句谢。
赵九摆摆手,又指了指院外:“我昨天把那谁的衣服晒外边儿了,忘记跟你说,今儿来看见没收才想起来。”
贞白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了一眼:“一会儿还请你帮他穿上。”
“诶。”赵九应下,说:“其实我这么急着就是来告诉你,昨儿个晚上出事儿了。”
赵九跟着贞白进了屋,续道:“昨天我回去,和完面实在困得不行,倒头就睡了,外面什么动静愣是没听见,早上蒸好包子支摊儿的时候,大家都在议论,梁捕头带队去让几家大户挖祖坟,说是这里头可能有一具空棺。”
贞白将包子搁在桌上:“开棺了吗?”
“开什么棺啊,这不讨打吗,人气急了,直接一棍子给梁捕头的脑袋开了瓢,据说流了好多血,那家子因为袭击官差,被捕了,我刚才过来的时候,还看见门口闹得不可开交呢,估计折腾了一晚上。”赵九揉了揉鼻子:“好像是张员外打的,不过今早我看到谢家的轿子也停在外头,有些纳闷儿,你说之前王六夫妻俩为女儿的事上谢宅大闹过一场,但是没有结果,如今官府又怀疑这几家大户的祖坟中有一具空棺,尸体是埋在王六家院子里的那具,我就在寻思,怎么又牵扯上了谢家,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啊?”
赵九一语中的,串出一条线索,贞白蓦地抬首,抓起沉木剑就往外走:“我去衙门看看。”
“哎道长,我也去。”
“等等。”李怀信脱口叫住一只脚已踏出门外的赵九:“你先把衣服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