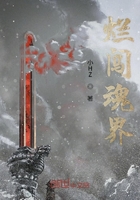焦土之下一道深深的裂痕,五棵青松倒在裂纹处,齐刷刷被闪电劈开,点燃了针叶灌木,顿时火光漫天,烧着了那些从地里爬出来的“白骨精”。
盯着滚滚浓烟,李怀信心下一凛,转头去看冯天,后者已经脸色煞白,猛地拽住了他,落地撤退,他低喊了句:“不好。”
大火烧尽白骨,附骨灵则藏在浓烟里,四处窜散,仿佛毒液融入水中,防不胜防,一触既亡。
李怀信两眼抓瞎,简直要炸,怼冯天:“老天爷帮了大忙了?嗯?”
眼下情形别说帮忙了,简直是要赶尽杀绝。
“卧槽。”冯天五雷轰顶道:“我可能会错了意,跑啊。”
身后浓烟犹如毒瘴一样弥漫开来,浓烟浩渺,紧随着二人的脚步往外铺张,冯天一回头,眼见就要被黑烟吞噬,两条腿迈出了风火轮的架势。
这种节骨眼儿上,他突然想起来乱葬岗之前算的那一卦,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大凶,我这次是不是算准了。”
李怀信很想抡他一巴掌:“你算没算准都是大凶,没有吉卦。”
只要让冯天算命,保准人人都是短命相,五年前的一天晚上,他还胆大包天的算过掌教见不到明天的太阳,然后掌教安然无恙的见了五年明天的太阳,还在继续见。
此道上,冯天一直在打击中成长,早就钉了套护心的铠甲,面对任何人的嗤之以鼻,他是无坚不摧的,没有受辱受嘲的意识,习以为常地麻木了。冯天自己心里也有数,十六岁前也犟过,自暴自弃的时候拿着五帝钱去买阳春面,但朝代更迭,时下用的是大端王朝的货币,五帝钱花不出去,又乖乖地揣回了太行。在他算到大师兄秦暮要在深冬暴毙而亡时,大师兄突破了两重修为出关了,又一次失算的冯天心情沉到了谷底,李怀信终于站出来说了句人话:“你很想那个假正经死吗?你能比我还烦他?我都没想他去死呢,你这算不准也是好事,不然整个太行山都成坟场了!积点德吧,以后别算了,跟我修剑去。”
然后冯天就被李怀信拐带跑了,从此跟三师叔结下了抢夺徒弟的梁子,在太行山闹得鸡飞狗跳。
冯天还在神游天外,突然被人一把拽住,他一时没刹住脚,强行弹了回去,撞在了李怀信肩上:“干什……”话未问完他就愣住了,四下一片寂静,密集的松林换成了旷地,稀松几根光秃秃的树枝,仍旧是鬼气森森的黑。他猛地回头,没有一丝丝烟雾散过来,却仍能看见远处那片松树林,冯天有些茫然:“我们出来了?”
见李怀信点头,他又问:“怎么出来的?”
“跑出来的。”
冯天闻言一噎:“废的什么话!”
李怀信神情几分复杂:“那些东西出不来么?”
冯天观察须臾:“好像是,烟雾也散不出来。”
李怀信蹙眉:“所以设下阵法的那个人不仅是防止我们这样的人进去,更是为了防止里面的东西出来?!”
冯天有些懵:“哪个人?”
“布下镜像界的人。”
冯天四下一扫,灵台猛地清明:“这乱葬岗是被人封印起来的,我们根本没有出去,而是闯过了松林阵那道禁制,到了最里头。”
李怀信的脸色更显凝重,向来自视甚高的他心底掠过隐隐不安,仅仅一个松林阵,就差点将他们困死,若不是闪电雷劫,将镜像界劈出一道裂痕,他们恐怕已经葬身其中了。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老天爷帮了大忙。
眼下冯天担心的是:“里头着火了,会烧起来吗?”
李怀信挑了挑眉:“怎么?你还要进去灭火?会呼风唤雨还是怎的?”
冯天道:“你这种人怎么没烧死在里头。”
李怀信道:“冯天,你父母还健在吧,说这种话是要诛九族的我告诉你。”
冯天就笑:“得亏你不是太子,否则你要是当了皇帝,绝对是滥杀无辜的暴君。”
“你怎么知道我当不了皇帝。”
“老二啊,你们天家,向来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你……”不是嫡也不是长,永居第二的话还未说完,迎面就是一记飞毛腿,冯天敏捷闪躲,奈何对手阴险狡诈,玩了一套声东击西,一巴掌糊在他后脑勺上,冯天嗷叫一声:“你有点度量行不行,老二怎么了,过不去这道坎儿了吗,一提就上手。”
“还没有肚量?换个人喊我早捅破他喉咙了,别蹬鼻子上脸。”
“行行行。”冯天摆摆手,扭过头盯着松林处:“咱俩都差点被困死在里面,那熊孩子呢?一路过来连个影子都没看见。”
“按理说,若是进来了,现在应该不会再活着了。”
冯天倒吸一口冷气,即便他也这般认为,却仍是有些扼腕:“那么尸体呢?我们也没看见啊。”
李怀信一挑眉毛,看傻子一样看冯天:“乱葬岗里全是尸体,你一具一具翻去,有气儿的还能喊一嗓子,找起来相对容易,咱就先指望那孩子命大吧。”
冯天张了张嘴,还未等他发音,便听到土里一阵细细碎碎的声响,越来越近,于地底穿行,仿佛就在脚下。冯天不禁后退了一步,四下逡巡,却什么都看不见。
李怀信道:“在地下。”
“不会又是那玩意儿吧?!”
“埋了几十万大军呢,谁知道。”
突然起风,吹得草木沙沙作响,伴随着地底的声音,灌入耳里,扰乱视听。
冯天打了个冷颤,只觉这越来越大的寒风有些割脸,平底掀起一片尘土,吹到了眼睛里,冯天抬手揉掉,看见李怀信的墨发长袍在寒风中猎猎飞扬。他抬起头,看着黑云被飓风卷走,明月露出轮廓来。
“怀信,不太对劲啊。”
李怀信仰起脸,望着月下黑云翻墨,越压越低,几欲笼罩整个大地。
“是地动吗?”冯天脚下不稳,挪了两步:“有没有感觉到?”
“有。”李怀信回答,俯下身去,目及之处并没有土壤松动的迹象,他伸出手,还未触到地面又缩了回去,转头道:“冯天,把地刨开看看。”
冯天斟酌了一下:“谁知道这里有没有布下阵法,说不定地下镇着什么东西,万一把妖孽刨出来就不好了。”
他潜意识觉得这地方不对劲,压着阵法,却看不出端倪,他虽然学无所成,但学得庞杂,师父言传身教,就算他不开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算见识过,哪怕再浅薄,对阵法的敏锐度还是有几分的。
所以李怀信并没有怀疑他的言论,而是问:“你看出什么了吗?”
冯天摇了摇头,只觉狂风大作,仿佛一双手在将他往前推,被动地迈了几步后,仍旧能感觉到脚下近乎微不可察的动静。显然李怀信的敏锐度更强,他直接抽剑插入土里,剑尖一挑,拨开的泥土被狂风卷走,二人看着小坑微微一愣。
冯天直接蹲下身,摸了摸坑里,确定似的抬起头说:“是树根。”
李怀信拧眉,有些费解:“树根在动?”
“不是。”冯天道:“好像在长。”
闻言,他们四下张望,依稀只能看见周围几颗枯败的小树,只有二里远的地方长了颗粗壮的槐树,离得甚远,按理说,这些树根茎不可能生长到他们脚下来。况且这树根迈入地底穿土的动静不小,好似一条虫子蠕动在床褥底下,五感敏锐的修士定能感觉到这种微末的异样。
“嘶。”冯天抽回手:“不对,这树根聚阴极了,咱去前面看看。”
二人被飓风推搡着往前,寒气灌了满身,几乎侵皮入骨。
一段距离后,他们立在这棵根茎延绵的槐树下,还未细瞧,就被远处吸引了目光。
道路逐渐往下倾斜,凹出一片幽谷,透着茫茫深寒。
夜幕之下,空谷之中,古树参天,巍然苍劲,以目力丈量,似千丈之高。
冯天张大嘴,目瞪口呆的望着古树,根茎盘根错节,密密麻麻直入地心,在土里蜿蜒纵横,延绵不绝。
冯天吞咽了一下,没从惊震中回过神来:“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古槐,得有千万年吧?太壮观了!”
上空乱云飞渡,与那荫翳蔽日的参天古树相得益彰,看尽眼里,李怀信同样震颤不已。
此处地形四面环山,斜坡陡峭,狂风在耳边呼啸,刮入幽谷不泄,藏风聚气。
冯天张了张嘴:“这地方……”
“怎么了?”
“风雨所会,阴阳所合,万物得以生机,古槐屹立,乃天地中心之柱。”冯天抬手往前一指,啧了一声:“没想到乱葬岗里还有这么一处风水绝佳的宝地。”
绝到什么程度?冯天道:“能修皇陵了。”
李怀信又想抽人:“谁他妈把皇陵建在乱葬岗里?”
冯天道:“真龙穴啊。”
李怀信嗤鼻:“多好啊,不如把你家祖坟迁到这儿来吧。”
冯天怒目圆瞪:“我说你咋这么阴损呢,我说能修皇陵又没真的提议,就是打个比方。”
“你有九条命敢拿天家打比方。”李怀信说,“还当着我的面儿。”
“你又不介意……”
“介意。”
冯天嘴角一抽,斜了他一眼,心道:我让着你。
二人顺着斜坡而下,狂风呼啸中夹着呜咽声,响在耳边,令他们脚步一顿,本以为是错觉,细听之下,二人两相对视,李怀信皱紧眉头:“百鬼……”他不确定似的顿了顿,冯天便接过了话:“哭丧。”
百鬼哭丧!
哭什么丧,给他俩吗?!
听着催命似的哭丧,冯天的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他刚要开口,就见李怀信脚下一绊,整个人失去了平衡,冯天欲想拉他一把,不料自己也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双双滚下斜坡,砸进一个大坑里。
背后撞在一处凹凸不平的坚硬上,仿佛摔散了架,后背的剧痛让李怀信咬紧牙关,他深吸一口气,手撑住地面想要爬起来,奈何手心摸到一截纤细的长条物,不似树枝也不似顽石,他轻轻一抽拿到眼前,竟是一截骨头。他猛地弹起身,顾不得后背剧痛,腿脚陷入骨堆中,没过了膝盖,脚底垫着一块头骨似的东西才没有踏空。他望了眼身处之境,头皮猛地发麻。
冯天痛吟几声,坐在骨堆上,看见整个巨大的尸骨坑时,倏地怔住了。
方才他们站在斜坡上,目光全被远处那颗千丈古槐所吸引,没看到斜坡底下这么巨大的一个深坑。
“作孽啊。”冯天回过神,汗毛倒竖,“一场大战死了多少人。”
闻言,李怀信转头望着他,脸色发白。
他能感受到尸山骸骨里的怨气,几乎侵入骨髓般深重。
尸骨坑里堆满了兵刃、铠甲、马骨……,那些烈士的尸骸有些被腰斩,有些被斩下头颅,或断臂残腿,支离破碎,将十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杀戮呈现眼前。
一名名烈士在战场上呼啸着,嘶吼着,浴血杀敌,壮烈牺牲。最后倒在血泊中,死于异乡,连尸身都无人收敛。
他好似记得父皇曾经感叹过:一个朝代的兴盛有多么不易?
能有多么不易?
年少无知的他身处红墙碧瓦,含着金汤勺长大,养尊处优,锦衣玉食,几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所见所闻皆是花团锦簇,后宫的妃子们争奇斗艳,最大的悲愁就是不得圣宠。他也不知道父皇的忧思,每日起早贪黑,下朝后在御书房里对着堆成小山的奏折殚精竭虑,殊不知父皇熬至深夜所批下的每一个抉择,可能都是一场天下动荡。
走神之际,只觉一阵乏力,他好像听见冯天在喊:“怀信,怀信,李怀信!”
耳边嗡嗡作响,寒风裹缠在身上,从每一个细小的毛孔中侵入,眼前黑影重重,一片乱麻的闪过,鼻息间弥漫着血腥味,全是令人窒息的杀伐气,耳边充诉着兵刃相拼的争鸣,还有歇斯底里地、却无比遥远的呐喊:“李怀信!老二!老二!”
真是让人上火啊!
他正要发怒,割了此人的舌头,耳边的声音却忽地一变,那人喊他:“二殿下。”嗓音低沉极了,略显苍劲,他说:“二殿下,走过去,站上去。”
李怀信用力的眨了眨眼,眼前依旧是天旋地转的重影,什么也看不清,他想问谁在说话,你是谁?张了张嘴,却溢出一声痛苦的低吟。
好疼啊,有什么东西正往他身体里钻,仿佛想侵占他的灵魂。
他觉得自己整个人浮在半空,脚下踩不到实地,每一下挣扎,都踏着虚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