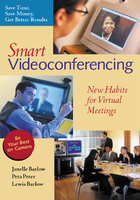果不其然,在司马馗和涧亦的两边的分头行动,各自都是有许多的收获。至于那贪污的黄金,也在安保生夫人的房间地下找到了暗室。
这个隐藏的地下室的空间足足有两个安府那么大。
因为身份的暴露,他们姑且也是住不了客栈,从而临时决定打搅张然的府邸。
当张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受宠若惊这四个字表达是最恰当的。他自然是不能拒绝,忙是吩咐人回去赶紧整理出几个房间来。
赫君还与任长央在衙门处理了一些从三家搜到的赃物后,便是带着东西离开了衙门。
坐在马车里,赫君还依然还是看着手上的账本,他的脸色至始至终都没有缓和过。任长央看了看窗外的大街后,才悠悠道,“在我看来,这安保生贪赃枉法,安少爷似乎一直都是云里雾里的状态。必然是安保生不想让自己的儿子陷入这泥潭中,所以一直都是对安少爷避而远之。”
“即便如此,也是改变不了他平日中的种种。”
“从账本还有这些书信来往的形式来看,安保生不过是个中间人,上下两边都是还有牵线的。至于这慕容晔是不是最后的关键也还是个未知数,不过目前最要紧的还是让安保生亲自写下那些官员的名字。”马车还在平稳而轻快的走着,马车外的喧闹丝毫掩盖不住马车内有些严肃的气氛。
赫君还只是单单发出了一个嗯的音,便是继续埋头看着手中的账本。这里头每一笔账的来源都是令他的情绪一波皆一波的高起,久久无法平静。
贪赃枉法,仿佛是每个地方每一个国家都会存在的毒瘤,即便是拔了,依然会萌生发芽继续从另一处生存。
“安保生出了问题,王爷觉得那些人会对其下手灭口吗?”
终于,赫君还收起了账本,抬头面不改色地直视着从容不迫的任长央,思量间他就动了动嘴唇,“已经差人暗中守着。”赫君还一副早就料想到的样子,很快又是扭过头来,“你觉得安保生被杀的可能性多大?”
马车虽然是封闭的,但是偶尔还是会有冷风吹进来,任长央觉得这风刮在手背上格外的疼,她不自觉地将手臂缩了一缩。那嘴唇何时开始已经有些发紫,“就算安保生不是个关键人,但是从他口中得知的人自然也是重要的人。一个倒,整根绳子上的蚱蜢自然不会继续安然的样子。”
这番话,赫君还不反驳,算是默认。任长央将整件事情捋了捋,忽然间皱起眉头,一种不好的念头从脑中划过,“王爷,你不觉得安保生贪赃这件事情发生的太突然可又很顺利吗?”
“如何突然?如何顺利?”
“从百姓嘴中得知安保生抢夺民脂民膏不假,安保生知道自己在百姓眼中是个不折不扣的贪官,那么他自己会有觉悟亦或者上面的人会给予指示,这账本不该留在安府。可偏偏这账本是留在了安保生的书房,而且是最起眼的地方。虽然我们也是突然搜府,可是据张然所说安保生的警惕性是个很高的人。”这其中肯定是有猫腻在。
任长央分析得很仔细,甚至整个人的心思都是投入其中。却也是忽略了此时此刻赫君还一副看戏子般的盯着自己看,直至任长央发现赫君还没有回应自己,抬头一看,才发现他一直盯着自己看。
猛然间地,任长央才发现自己是太过认真了。这时候她才收起了内心的猜疑,恢复以往的冷淡态度,“我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这时候,赫君还同样也是收回了眼神,那嘴角拂过的笑意消失的很快,“本王不觉得你有其他的意思,只是不想你的分析能力会那么厉害。”
这样一听,任长央表露出了一丝丝不悦,她反而觉得赫君还这样说得有些敷衍。“王爷太抬举了。”她没好气的反驳了过去。
马车突然颠簸了一下,任长央一个不稳身子猛地撞进了赫君还的怀中,她瞬间瞪大了眼睛,那温热的气息令她耳根子滚烫起来。她立即是挣脱了赫君还放在腰间的手,扭过头坐正了身体。
“若是再让王妃撞到哪里,本王就将你的手砍下来!”
驾着马车的侍卫登时觉得后背发凉,二月寒天竟然也觉得有些燥热。他忙是回应,“属下知错,属下保证不会有下次。”
终于,马车到了张府。
两人前后下了马车,张然带着家眷站在门口已经是等候多时,一看两人已经落地,纷纷跪下行礼。“恭迎王爷和王妃,府邸简陋,还望王爷和王妃莫要嫌弃。”
赫君还正准备开口,身后涧亦骑着马已经停住,神色慌张地跨步到他的面前,单膝跪地,“爷,安保生父子被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