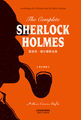1
大地上本来没有故事,哪里出现了人,哪里就有了故事,人在哪里住久了,故事自然就多了起来。
混水河原本也没有故事,后来人们来到河畔,住了下来,就有了故事,住久了,故事也就多起来了。
混水河是一条无名小溪,在地图上绝对找不到,但正如它流经的汪家屯是的的确确存在的,存在于黄土高原北部边缘的一个小小的角落,混水河存在了数千年也说不定。
汪家屯所处的地形,南高北低,东向西倾。村子东面十多里远处,横着一座大山,层峦叠嶂,岚烟缥缈,名叫彩虹山,南北走向,好像一匹巨大的骆驼。如果站在村里向东凝神眺望,你会觉得它似乎正在缓缓地向前行进,你的耳际仿佛响着“叮咚——叮咚——”低沉的驼铃声。村子南面约莫十里远处,平地凸起一个山包,山上没有树木,光秃秃的山顶像个巨大的蘑菇,名叫蘑菇岭。村子西北面大约五里之处,有一座山岗,孤零零地兀立在那儿,显得十分孤寂、冷清,名叫孤山。
混水河从蘑菇岭顶上什么沟壑钻出来,像一柄神奇的犁划破厚厚的黄土层,开拓河道,一路呼喊着奔到孤山脚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孤山脚下形成了一泓浑浊的水洼,名叫孤山洼。站在蘑菇岭顶上,举目放眼向北眺望,孤山洼好像一个巨大的海碗,盛着土红色高粱米稀粥。
早晨,要是天气晴朗,太阳从彩虹山顶上懒洋洋地爬上来,大把大把地将橙黄色的光线投向混水河,河面上激起的细浪碎波翻腾着,泛着红灿灿的光芒。如果从空中俯视,这条小河好像一条全身长满血红色鳞片的怪物,从南向北蜿蜒,缓缓爬行,蛮横地穿越汪家屯,一甩头向西北拐去,然后悄然爬进了孤山洼。
要是冰封大地时节,从空中俯视,混水河却是另一番景象:仿佛一条巨蟒,尾巴藏在蘑菇岭下,在孤山脚下昂起巨大的头颅,通体闪烁着土黄色的光芒。
混水河流经汪家屯的那一段,人们叫它弯道儿,武断地把村庄分割成两半——东汪村和西汪村。
汪家屯的房屋和黄土高原北部绝大多数农村的房子几乎一模一样,好像用一个模子拓出来的:黄土屋顶、黄土山墙、黄土院墙、黄土门楼,低矮简陋,断壁残垣,好像史前遗迹。
冬春两季大部分日子,北风呼啸,沙尘飞扬,天昏地暗。惨淡的太阳没精打采地在黄蒙蒙的天空滑行,鄙夷地俯视着这个被风沙蹂躏着的小村庄。
风沙横行的日子,人们紧闭门户,待在家里。男人们或者睡懒觉,或者脱下衣裤捉虱子,或者圪蹴在炕上抽旱烟;女人们或者看孩子,或者捻线补衣,或者做别的家务。街上很难看到人影,几乎听不到人声,荒寂如坟茔。
偶尔遇到好天气,黄风停息,沙土落地,天空变成灰蓝色,太阳的脸露出几分欢颜。这时候,人们敞开街门,走出来活动。孩子们聚在一起,嬉戏打闹,或玩羊粪蛋儿,或耍泥钱儿。男人们聚在一起晒太阳,抄手缩脖,或站在墙角,或蹲在墙根,海阔天空地唠嗑儿。有的嘴里叼着旱烟袋,有的脱下皮袄扒开毛,兴致勃勃地捉虱子,不停地用两个拇指指甲挤压,或闭起眼睛用牙齿猛咬,发出“嘎巴——嘎巴——”的一阵脆响。不一会儿两个拇指指甲盖儿便成了黑红色,好像染了指甲油,末了噘起嘴巴,“呸呸”吐两口唾沫在指甲上,然后在裤子上随便什么地方蹭一蹭,重新穿上皮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这就是混水河畔的真实写照。
2
汪家屯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人丁不旺,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总共不到三十户人家,大约一百二十人。汪姓是大姓,占全村人口将近一半,其次是刁姓,再其次是张姓,此外还有几户别的姓氏。
传说,最早来到汪家屯定居的是汪琛老汉的祖先。年过七十的汪琛老汉说,他家的家谱记载,汪家第一个来汪家屯的祖先是他祖爷爷的祖爷爷的祖爷爷。汪琛老汉的院子在西汪屯的最南头,街门朝东开,门前有一棵三人合抱粗、五丈多高的大榆树。那棵榆树的年龄,村里的人谁也说不清。就是活到近百岁的汪琛老汉的老妈汪张氏也说不准。她只说小时候听老人们讲,那棵树比村子的年龄还大。榆树长得比较缓慢,那么粗那么高的榆树,很可能有二三百岁。
初夏,那棵榆树墨绿色的树冠上,缀满了金黄色的榆钱串儿,像一顶巨大的皇冠,金黄色和墨绿色互相映衬,在太阳下闪烁着梦一般的灿烂光芒。清风掠过,树上的榆钱儿发出一阵声响,仿佛从天堂传来了美妙的音乐。树冠投下一大片阴影,清凉宜人,是人们乘凉和孩子们玩耍的好去处。
人们常常看到汪琛老汉的老妈坐在那棵大榆树下,给曾孙子们讲故事。
她身穿半新黑色衣裤,盘腿坐在树下的一块破席子上,腿下压着两只粽子似的小脚,锥尖般的脚尖露在外面;膝头上一边坐着一个男孩儿,另一边坐着一个女孩儿。男孩儿是她的曾孙子,女孩儿是她的曾孙女。她那沟壑般皱纹纵横的脸,笑成一朵大菊花,浑浊的眼球放射出愉悦的光芒,银白色的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拳头大的纂,显得干净利落,透出几分仙风道骨的气质。
他们旁边老是躺着一条大黄狗。那是一条很老的狗,名叫大黄,几乎整天懒洋洋地侧躺在地上,闭着眼睛,伸着四条腿儿睡懒觉。别看它成天躺着,它可是这祖孙三人忠实的卫士。那时候,村前村后常有饿狼出没。有一天,老人抱着两个曾孙子在大榆树下乘凉,一只饿狼突然出现在村头,张着血红的大嘴巴,向他们悄然逼近。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大黄从睡梦中惊醒,它一跃而起,精神抖擞,尾巴竖立,愤怒狂吠,犹如无畏的勇士向饿狼冲去。饿狼见嘴边的美餐就要失掉,哪肯罢休,立即跳起迎战。大黄突然纵身一跃扑到饿狼背上,死死咬住它的一只耳朵不放。那饿狼惨叫着拼命挣扎,好不容易才摆脱敌口,夹起尾巴惶然逃跑。大黄却没有去追它,大概遵循着“穷寇莫追”的理念吧,嘴里叼着饿狼的半个耳朵,俨然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站在那儿警惕地望着饿狼消失在山林,吐掉那半只狼耳朵,慢慢地回到主人身旁,躺下继续睡觉,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人们只知道汪琛的老妈姓张,但不知道她的名字,连她自己也忘了自己叫啥。这不能怪她人老糊涂。她是本村人,没有亲兄弟姊妹,十五岁出嫁,不久父母在一次霍乱瘟疫中离开了人世,从此以后,谁也没叫过她的名字。她和当地别的做媳妇的女人一样,在婆家谁也不称呼她的名字,公婆称她儿媳妇,丈夫叫她内人,外人呼她汪贵生老婆;汪贵生自然是汪琛的父亲,早已作古。她是全村年纪最大的老人,同族人称呼她老祖宗,外人叫她汪张氏老奶奶。
“老祖宗,再讲一遍混水河的故事,我还想听!”小男孩儿伸出胖嘟嘟的小手,用劲摇着老祖宗的肩头。
“不,我不想听那个故事。讲金马驹儿的故事吧。我要听金马驹儿的故事。”小女孩儿搂着老祖宗的脖子,红苹果似的小脸蛋紧紧贴在她干瘪的脸颊上,娇滴滴地央求。
这两个小孩都是汪琛老汉独生子汪长命的孩子。小男孩儿两岁半,叫锁柱,长得虎头虎脑,头顶上留着足有三指宽的马鬃,盖着脑门,脑后留着一撮长命发,圆圆的脸盘,宽宽的前额,扑闪着两只机灵的圆眼睛。小女孩儿四岁,叫荷花,梳着两根羊角辫儿,瓜子脸蛋儿,细长眼睛,双眼皮儿,微微翘起的小鼻子,模样看上去好似一个可爱的泥娃娃。
“不!不!我不想听金马驹儿。我就要听清水变混水的故事。”锁柱固执地说。
“不,我就想听金马驹儿的故事。”荷花也不让步。
“不,我不!我就要听混水河的故事。”锁柱摇着老祖宗的肩膀,哭着喊叫。
老祖宗用瘪嘴在两个小脸蛋上分别亲了亲,说道:“好啦,好啦。我今儿不讲混水河,也不讲金马驹。”看来老祖宗要施行中庸之道,避免让任何一个孩子失望。
“那讲啥呀?”小姐弟俩扬起柔嫩的小脸蛋,好奇地望着老祖宗布满皱纹的干瘪脸,静静地等待她往下讲。
老祖宗说:“我们家原来不姓汪。”
“那姓啥?”姐弟俩惊疑地睁圆了眼睛,他们第一次听说自己不姓汪。
老祖宗用枯树枝般的手指往后拢了拢散乱在鬓角的几根银发,轻轻咳嗽了两声,接着说:“姓王。”
“啊!?”小姐弟俩惊疑地喊道,“你糊涂啦,老祖宗。爷爷说我们姓汪,大大妈妈都说我们姓汪。你怎么说我们不姓汪,姓王呢?”
“我没有糊涂。我还机敏着呢。我们不姓汪,姓王。”老祖宗认真地说。接着她绘声绘色地讲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