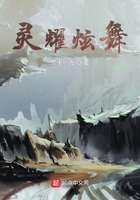两人出了巷子,并排上了街,宋高怀见余篁坦然行走在街上不禁问道:“你杀了绣春帮那么多人,不怕被找上来。怎么还以真面目示人。”
余篁答道:“我之前每次下手还算痛快,都是寻着落单的杀,杀完人就远走,而且我杀掉的那二十八人都是小喽喽,绣春帮也不会太过兴师动众的追寻,简单的查一下,查不到就算了。而且我一般不会再一个地方停留太长,除非是已经定下了的目标许久没有下手的机会。我上次动手还是在涠洲,所以就算当地有绣春帮的人,也不知道我的身份。”
宋高怀一听,姑娘你这不是挺冷静的吗。为什么刚见面就想杀了我。他想到此处便就问起,“那我俩刚见面那时?”
余篁微微一笑,“第一,我藏身的地方很隐蔽,根本没人知道;第二,我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已经大致记住了县西南所有人的长相和特征,你不用惊讶,到了我这个境界,这只是小事而已。第三,你鬼鬼祟祟地在我家门前驻足了许久,很可疑。”
宋高怀听到这里,心里有些疑惑,又问道:“那为什么小周村赵大利就知道你的位置?我能来到这里,还是他说要我与这里的铁匠问个好。而且我在来的路上打听时,问过两个人,一个是在西南主街,一个是在这附近的巷子。他们都很明确的跟我表述了位置。”
余篁也愣住了,她低下头想了想,“我跟赵猎户的交情不深,与他相识与你一样都是为了躲避绣春帮。而且我自打来了这里,也很少露面,就算被人问起,也只是提了句我是铁匠这一托词,事实上也根本没人找过我。你还是第一个。对了,关于赵猎户,我当时与他接触时,他告诉我的名字不叫什么赵大利,而是赵措。”
“赵措?赵大利?”宋高怀脑子更不够使了,你说你一个打猎的,起那么多名干什么?
两人到了一家小铺子,店小二上了两碗凉茶,问道:“二位客官吃点什么?”
余篁随便点了两碗饭,两盘小菜,店小二注意到了余篁,心道这姑娘可真漂亮,不禁又多看了两眼。他吆喝一句,又去招呼别的客人,时不时目光还落在余篁背影上。
两人等着时也没说话,都在各自想这事,宋高怀想着无非是系统干预和有人暗中安排这两种可能,现在来看还是前一种可能性大一些,不然那么多玩家来到幸洲,凭什么他就会被人关注。还有赵措亦或是赵大利这人,一定不单单只是个猎户。
余篁已经习惯了店小二这类人的眼光,也没多想,而对于刚才与宋高怀说的事情她想不通为什么也就不多想了,就与宋高怀闲聊。不多时,小二端来了饭菜,宋高怀寻思着在他了解到的游戏里,店小二和店铺掌柜的都在里面扮演了情报人员的角色,因而也就问道:“店家知道最近芝林县里谁家有麻烦吗?”
店小二将视线依依不舍地从余篁这里移到宋高怀这里,笑道:“一看您二位就是外乡人,咱们芝林县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敢说,但鸡鸣狗盗之辈可是少之又少。连这种人都不常见又能有什么麻烦事儿呢。”小二说着,目光又放在了余篁这边,“不过要说奇怪的事儿啊。”到底是吃这碗饭的,小二说起来也来了劲儿,“县城北面这阵子不是正在拆除旧永华寺吗?您猜拆出什么了?”
宋高怀看这小二有点不顺眼,他娘的你说话就说话,看你这腰弯的,再给你二尺脸就都要都要扎人家余篁胸口里去了,男性大多都有这种心理,见着自己的女伴被别的男人一直打量或是调笑,心理总归就不是个滋味。他一拍桌子,吓得小二连忙把身子挺起来,看着宋高怀的神色也有些不悦,好像打扰了他的好事一般。但他哪里知道,若是他再敢往前一点,余篁的手就要从桌子底下迎上这恨没多长二尺脸皮的店小二了。这种事儿余篁没少干过,登徒子、店小二、甚至是江湖人士,所以也算是驾轻就熟了,力度把握地可以正好让店小二昏厥三天还留不下什么后遗症,就是脸可能要肿一阵子,门牙什么的能保全算是万幸,保不住余篁也不会再给你另一巴掌。除非你仍然死皮赖脸地贴上来,到时候就不是一巴掌的事儿了。
宋高怀玩味地看着店小二,也不想跟店小二一般见识,就说道:“可是那梁上金银,地下古物?”
店小二一个伺候人的,就算别人甩他一巴掌,他不也得笑呵呵地赔不是?刚才那一眼也是鬼迷心了,这会儿不还后怕呢!所以他见这男子不予追究,还应上自己的话,就微不可见地挪动了下身子,将整个朝向都放在宋高怀这边,看也不看余篁了。他笑的谄媚,“这位爷好见识,”说着还竖了个大拇指,“可不就是那梁上有金银,地下有古物。一般要是这事儿放在平常百姓家里,能拆出来东西自然是皆大欢喜,最多被几个无赖远房亲戚讨要些。但也不会太过分不是?但是永华寺是什么地方,收香火的地方,你说这么多器物财宝,被发现在了一座寺庙里,其他人是什么看法。”
“寺里住持还解释说,这些器物根本不是本朝的制式,梁上的财物也不知从何而来。但他说归说,咱们也得信呐?他一个老和尚空口无凭的,但那东西可是搁你们寺里寻出来的。这不,县衙卫当即就把永华寺一干人等扣下了,这事儿吧,往小了说,也就是永华寺贪婪无度,最多也是是老百姓怨声载道,说那老和尚们修禅修到狗身上去了;但是往大了说,现在朝廷抓贪官,抓污吏可都不遗余力着呢,你一个永华寺又怎么能跑得了呢,这番收受香火,又与收受贿赂有何区别。按咱们大天朝国师的话说啊,就是‘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要不是永华寺后面有人说话,怕就不是暂且压扣这么简单了。”
宋高怀抚掌一笑,“这句我知道,是醉吟先生的诗句,是引用当时宣州进贡红线毯的事,对宣州太守一类官员讨好皇帝的行为加以讽刺。我觉得更深层的意思还是借由此来揭露当时统治者的荒淫无度,毫不顾惜织工的辛勤劳动而任意浪费人力物力。后四句应当是‘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秒极。”
“公子好文采啊,若当公子参加科举,连中三元亦是不难。”店小二先是捧了宋高怀一句,随后压低了声音,“但公子这些话在我们下人这里说说也就罢了,可千万莫让有心人听见啊,当朝皇帝文治武功,这种昏话可说不得啊。”
宋高怀对这个小二观感有些改变,好色是不假,但余篁姿色摆在那儿,没人不会不动心。他能小心提醒自己,自己也就乐得接受,就拍拍店小二的肩膀,说道:“夫文人相轻,从古而然,而一时巨擘,皆左袒敛衽。道理我懂,你放心好了。”
店小二这句可就听不大明白了,但后面那九个字他还是知道的,就又说了两句这才去招呼其他客人。宋高怀又犯难了,这永华寺又是个什么套路?怎么一个个的任务都这么大呢,他看向余篁,寻思着问问这永华寺是个什么路数,可是他迎上余篁的目光,却怎么觉得这丫头眼神不太对呢?便问道:“余姑娘,你怎么了?”
余篁眼神错开,有些不敢看宋高怀,低下头小声说道:“没想到展公子还是个饱读诗书的读书人,我自小没有双亲,收养我的老人也没教过我习字,到了师傅那里,我就只知道功法典籍上的字,其他的字,就……就不认得了。”
宋高怀会意一笑,这余篁抛去深仇大恨,也就是个小姑娘而已啊,这会儿的憨态神情自是可爱极了,他不禁摸向余篁脑袋,笑道:“不妨事,早知如此,我现在教你识字也不晚。权当你授我功法招式的报酬了。”
余篁点头如小鸡啄米,她重新看向宋高怀,“那你能先教我写我的名字吗?我的名字是师傅给起的,余是剩余的余,篁是竹子的意思。”
宋高怀以手指蘸水为笔,划方桌为纸,一笔一划地写着‘余篁’二字,一边写还一边说道:“我以为啊,你师傅给你起余篁二字,多半是采自‘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这一句,寓意行道之路难。道阻且长。”他写出一个余字,“若是拆开来看,余字也有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这般千古传唱的美句。”说着篁字也映在桌上,“轻鸥白鹭定吾友,翠柏幽篁是可人。这两个字,无论总结来说,还是拆开来看,意思都是极好的,代表了你师傅对你予以的厚望。”
宋高怀又抖落了一下作为汉语言文学毕业生的优越感。这边余篁小姑娘的崇敬感已经无以复加了。要是将余篁换作陆回雪,那宋高怀在说出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的时候,就已经趴在桌子底下了。
余篁认认真真地看了几遍宋高怀的字,又照着写了两遍,说道:“没想到师傅为我取名字的时候想了这么多。”
宋高怀也是胡说八道的,只是把自己肚子里那点油墨放在嘴上满足一下虚荣心,谁知道她师傅给余篁起名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没准只是看自家门庭竹子太多了,有些多余,所以起名叫余篁呢。
别说,宋高怀还真猜对了。
宋高怀扒拉着饭菜,余篁本就无需吃饭,这当儿也就干脆拿着筷子一遍一遍地写着她的名字。宋高怀心下不禁有些感慨,还有些心酸,余篁除了一身修为和深仇大恨,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知道自己的名字写法就这般欢喜,可见她何曾有过更多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