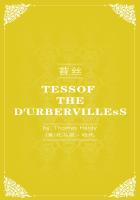白吕去墩庄镇报到的当天并没见到郭子兴书记。他推着自行车进了大院,走上那座三层办公楼,一个比他大不了几岁的高个子干部接待了他,并介绍自己是宣传委员毕萌。白吕便明白,这人就是他的前任。毕萌带着几分热情也带着几分矜持告诉他,郭书记去县里开会去了,明天早晨才能回来,让他先到宿舍休息等候。说罢,就带白吕去了大院东北角的一排平房。毕萌打开尽头的一扇门,把钥匙交给他说,就是这间。白吕走进去,只觉得一股子霉味直冲脑门,看来这屋已经好久没人居住。毕萌站在门口,告诉他几点开饭、食堂在哪里,说罢就要告辞。白吕说:毕委员,我来接你的班,你教教我怎样当秘书好吗?毕萌笑笑说:按照组织原则,咱们两个人的工作交接,应该在郭书记和你正式谈话之后进行,咱们就等他回来吧。接着,他摆摆手便回了前边的办公室。
原来是自己不懂规矩。白吕惭愧地拍一记头顶,便走进去收拾房间。这屋里,有一床、一桌、一把椅子,别无长物。看看地上挺干净,好像是有人提前给打扫了一番。他把铺盖搬到床上,把随身带的一些书籍放到桌上,然后就提着自己带来的暖瓶去打水。从食堂回来时,远远看见一个姑娘正在他的门口向里面张望。等他走近,姑娘回头看见了他,羞红着脸说:“你好。你就是新来的白秘书吧?”白吕点点头说:“是。你贵姓?”姑娘笑道:“贵贵贵地客气啥?我叫池小娇,文化站长,今后咱们就是同事加邻居啦!”说着,她朝旁边的那扇门一指。白吕想,原来自己跟这个小眼睛姑娘住隔壁呀?出于礼貌,也想赶紧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他便邀请池小娇到屋里坐坐。池小娇却抱着膀子直摇头:“俺可不敢进这屋!这两年差点叫它吓死啦!”白吕急忙问:“怎么回事?”池小娇却只笑不答。见她这样,白吕越发疑惑,便走进屋去四处打量。正打量着,池小娇也进来了。她小声道:“白秘书,我把事情告诉你,你可别跟别人说是我说的。”
接着,池小娇向白吕讲,这屋里死过人。大概是三年前她还没来的时候,镇上分来一个大学生当秘书,就住在这屋。郭子兴想试试他的本事,当天晚上告诉他,第二天要开一个大会,让他连夜把书记要做的报告写起来。这人吃过饭就关起门来写,第二天早晨却迟迟不见他开门。郭子兴让人喊他拿稿子来,可是再怎么喊里头也没人答话。把门撞开,进去一看,只见小伙子已在窗棂上吊死,桌上地上全是稿纸,每一张上只有三个字加一冒号:“同志们:原来他不会写这种文章,羞得不想活了。他死后,这屋谁也不愿来住,就连隔壁住的一个干部也搬走了,说是天天晚上听见这屋有人‘同志们、同志们’”地咕哝。小池说,她分来以后,镇领导让她住这屋,她听说了这事之后,也曾在夜间听见过这边有人咕哝。她几次找领导提意见,要求调换宿舍,但一直没得到批准。
白吕听罢这话,头皮一阵发麻。他说:“哎哟,领导怎么安排我住进来啦?”池小娇说:“大概是这院里再也找不到闲房了。这两年,乡镇干部越来越多难道你不知道?”白吕搔着头皮说:“唉,多亏郭书记不在家,不然的话,今天夜间这里又要多一个吊死鬼!”池小娇指着他“咯咯”直笑:“你……你这人真逗!”笑罢又说:“白秘书你也甭怕。老人们说,鬼其实是怕人的,邪不压正嘛!没事儿!”白吕点点头,又跟她说些别的。聊了一会儿,白吕便对这个大院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池小娇说,镇上虽然是党委、政府两套班子,其实只有郭书记一个人当家,正副镇长和党委其他成员大事小事都得向他请示。所以,秘书这一差使,只要让郭书记满意就行。毕萌就是这样干的,这几年无论公事私事,郭书记让他干啥就干啥,所以不到两年就提成了副乡级的宣传委员。白吕说:“那我也得这样干喽?”池小娇肯定地说:“就得这样干,除非你不当秘书。”白吕点点头道:“谢谢你,我明白了。”
池小娇走后,白吕除了吃饭便没再出门,一直在屋里温习那本《公文写作》,防备着明天郭书记试他的活儿。到了晚上,听见从不太隔音的墙那边传来池小娇走动、咳嗽等等一些声响,他觉得初来乍到的自己并不孤单。然而等到夜深了,隔壁没有动静了,白吕便想起三年前坐在这桌子前赶写报告的那位年轻人了。抬头看看曾经挂过死尸的窗棂,身上的汗毛“唰唰”地起立。他为了给自己壮胆,便扬起脸大声喊道:“同志们!”不料,隔壁也随即响起清清脆脆的一声:“同志们!”接着便是银铃一般的笑声。原来池小娇也还没睡。白吕心里一暖,按照一则笑话里的程序又喊:“同志们辛苦啦!”那边果然接了上来:“首长辛苦!”白吕接着喊:“小鬼挺胖哎!”那边回应道:“首、长、胖!”二人一起大笑,声震屋瓦。这时,白吕再也不害怕了,同时也庆幸自己住进了这间别人不愿住的房子,使自己拥有了这么个可爱的女邻。
白吕这时忽然担心,二人这么喊叫,让别的邻居听见了可不好。虽然自己住的这屋是在一排房的尽头,但池小娇的那一间隔墙有耳呀。于是他再不敢作声,看看已是十一点多钟,便上床灭灯睡了。到天明起来,惴惴不安地去瞅与池小娇相邻的屋,发现那门是锁着的。池小娇出来泼洗脸水看见了,说你看那屋干啥?那个温助理整天回自己村里住宿,从不在这里的。白吕点点头放下心来,与池小娇对视了一眼,这一眼让两个人的距离又拉近了许多。
打来早饭吃下,白吕正在门前的水池边刷碗,池小娇一边锁自己的门一边向他说:“上朝了,你不去?”白吕问:“什么是上朝?”池小娇说,每天早晨八点,镇上的所有干部都要到会议室开一次例会,先点名,后是郭书记讲话、派活儿,大家私下里管这叫作“上朝”。白吕笑着说:“原来是这样呀?那我得去,我正等着他谈话呢。”他三下五除二把碗洗好,急匆匆去了楼上。
位于三楼的会议室早已坐满了人,干部们一边抽烟一边闲谈。白吕刚到一个空座上坐下,全场突然鸦雀无声。他抬头看看,原来是一个人极具威严地坐到了台上,毕萌紧跟其后把一个沏好了茶叶的水杯放到他的面前,接着走到最前排坐下。白吕想,台上这人,肯定就是郭书记了,于是心里就有些紧张。正在这时,忽听郭子兴喊他的名字,他便慌慌地站起,像学生那样答了一声“到”。郭子兴指着他说:“先跟大伙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镇秘书小白,白吕。县里统一招考的公务员,刚分到咱们这里的。大家欢迎!”满屋的干部便一边看白吕一边鼓掌。
郭子兴示意白吕坐下,接着说道,他和欧镇长刚去县上开了一个经济工作会议,今天先向镇直干部传达一下。这时,他就让欧镇长读县委书记和县长的讲话。面容清瘦的欧镇长便从最前排起身,到台上读文件,读完又回到下边的位子上坐下。然后,郭子兴便开始了他的讲话。他说,县委县府提出了经济工作的新目标和新任务,全县将要掀起经济建设的新一轮高潮。我们墩庄镇的工作在全县十八个乡镇中一直居上游行列,尤其是雷公山区的小流域治理成为全省的典型,现在要继续做好这篇文章,争取用新的举措创造出新的“亮点”。那么新的举措是什么呢?这几年来,我们在雷公山区栽植了那么多的果树,特别是一百万棵栗子树已经开始结果。为了让农民能够把栗子卖出去,也为了在全省、全国、全世界打出我们的品牌,镇委镇府决定,立即动手在镇驻地建设“中国江北第一干果市场”。这个市场,规模要大,设施要全,初步计划占地五十亩,投资五百万元。
白吕看见,干部们听到这里,多数人的脸上都现出惊愕与疑虑。郭子兴向众人扫视一眼,停顿了一下,然后冷笑着道:“看看你们那熊样儿,歪鼻子斜眼的,又犯愁了是不是?我跟你们说,我郭子兴决定的事,上合领导要求,下合群众利益,是必须办好、坚决办好的!到了今天,快要跨世纪了,工作思路就必须是‘超常规、大跨度’,不然的话,你就永远是小脚太太,跟在别人后头挨批评!所以,今年墩庄镇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建这个市场!大家都做好思想准备,反正到时候要一起上阵,谁给我充孬,我就撸谁的官帽!在这里我也告诉大家,我是一把手,当然就是市场建设的第一责任人。我明天就开始到市里省里跑资金,跑货款,争取能多要一些过来。最后,看看还有多少缺口,再向群众集一部分资。反正不管怎样,要赶在九月底把市场建成,让今年全墩庄镇以及附近乡镇收获的栗子都往这里进,都从这里出。到那时,客商云集,买卖兴隆,税源增加了,镇财政宽裕了,老百姓的收入也多了,上级领导也满意了,皆大欢喜……”
讲完这件大事,郭子兴又说了几件小事,点了一些人让他们分头去办,然后将手一挥宣布例会结束。在众人乱哄哄向外走时,白吕站在那里看见,郭子兴向他招了招手。他带着一脸的腼腆与谦恭走过去,郭子兴说:“你跟我到办公室。”
到了位于二楼东头的书记办公室,郭子兴在宽宽大大的老板桌后面坐下,便对站在那里的白吕说:“小白,你是我专门到县里要来的。为什么?我就冲了新招收的公务员年轻,知识层次高,懂外语。咱们国家眼看就要加入WTO了,镇政府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怎么行呢?是不是?今天你来了,我很高兴。我相信,你会把工作干好的!”
白吕两手握在胸前,带着几分拘谨表态道:“郭书记,谢谢你对我的器重。请你今后多多指导,我一定好好干!”
郭子兴满意地点点头,接着说:“除了干好日常秘书工作,我再给你一个学习的任务。小吕,形势在发展,身为党政干部不学习不行呵,没有高学历不行呵。最近,北京一所名牌大学跟地委学校联办研究生函授班,公共管理专业,最近才在中国热起来的,叫什么MPA,我就报了名。可我干着这个熊差使,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哪有功夫复习应考呀。你刚才也听到了,光是建这干果市场就够我喝一壶的了。别没办法,你就去替替我吧!”
说着,郭子兴就从包里掏出一个准考证给白吕。白吕接过来时,手不由得发起抖来。他本来猜想,今天郭书记还会用写材料这方式试他的活儿的,没想到竟让他替考研究生!他为难地说:“郭书记,我怕是不行,给你考砸了。”郭子兴笑道:“还有十来天,可以复习嘛。喏,这儿是招生简章,你照这上面列的考试课目准备准备,我想是没有问题的!”白吕见推托不掉,只好说:“那我就试试吧。”说到这里,他忽然担心替考会不会被人查出,就瞅着准考证上郭子兴的相片发愣。郭子兴看出了他的心思,说道:“到了考场上,你只管放心做题。我已经托人安排好了,不会有人查的。”白吕点了点头。郭子兴又讲:“最近一段,你就不要在这里了,找一个地方集中精力复习,秘书工作先让毕萌顶着,等你考试回来再接手。你打算到哪里?我到县城给你安排住宾馆?”白吕想了想说:“我还是回家吧。”郭子兴说:“也好。家里安静。我早就听说,你母亲曾经担任过地区领导,这是很了不起的!他老人家现在怎么样?身体好吧?我这里有两棵人参,你拿回去给她补补身体!”说罢,他从旁边的橱子里拿出了两个包装精美的盒子,用报纸一裹就朝他手里递。白吕急忙推挡着说:“郭书记,这参我不能要,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郭子兴说:“我不是给你,是给老人!快拿着!”白吕只好接到了手中。这时,郭子兴便让他回去,并起身嘱咐他,这事不要让别人知道。白吕一边往外走一边答应着。
回到宿舍,白吕越想越不是滋味。他想,我考上公务员,应该是为公众服务的,怎么只给一个人服务,而且是这种不可告人的服务?他猜想,郭子兴之所以到县上要新招收的公务员当秘书,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为了这次考试。怎么办?我该怎么办?白吕想来想去,觉得自己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按照郭子兴的吩咐去做。唉,考就考吧,权当再把某些知识巩固一遍。他看看招生简章,上面所列的考试课目是政治理论、英语、管理学、行政学和综合知识,自己在大学里都学过的,心中便有了几分自信。他将有关的复习资料找出装进包里,推上自行车就回到了支吕官庄。
到家一说,并将带来的人参拿出,吕中贞欢喜不尽,说道:“俺儿到底是有本事,还能替书记考试!”白吕摇着头嘟哝:“我不愿干这事情。”吕中贞说:“你又犯傻!你只管好好地考,给书记考好了,他以后能待你孬啦?”白吕不想再跟娘说下去,就抱着书走进西屋再不出来。
埋头复习了十一天,考试时间到了。白吕按照准考证上的时间要求,直接坐车去了平州,到地委党校报上了名。在党校招待所住过一夜,第二天便上了考场。一开始白吕还有些紧张,恐怕监考老师到他面前验明正身。但时间一点点过去,始终也没见有人这么做,他便安心地做起题来。五门课,两天考下来,把他累得精疲力尽。不过,他自信考得还行。
吃过晚饭,白吕一个人去了平州师院,想到毕业后从没回去过的母校走一走。四年的大学生涯,给他留下了许多至死难忘的记忆。尤其是他的初恋,历经三年却又无果而终,让他一想起来就心痛不已。那个女孩来自茂县农村,面容姣好身段苗条。白吕与她认识,是因为去她宿舍找一个女同乡借书。就在他与女同乡说话的时候,发现对面床上有一个女孩盘腿坐着,在一张一张地数饭票。数完一遍,她用小手拢一拢,接着再数。也不知怎的,就是这个神态深深吸引了白吕。之后他经常到这里找女同乡,借机与这个叫苗珊的女孩攀谈,谈来谈去,终于有一天自己的饭票也由她来数了。当然,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只是数饭票,校园角落里的一次次热吻,城郊河滩上的一次次欢爱,让白吕充分品味了生命的美好。这样处了两年之后,有一回本宿舍男生交流泡妞感受,他才知道了苗珊的特别之处:别的女孩接吻时都闭着眼睛,唯独她是睁着的。一位学兄分析说,这样的女孩特有心计。再与苗珊约会时,白吕便留心这一点。果然,他吻得已经昏天黑地了,可是睁眼瞧瞧,苗珊还在两眼作斗鸡状观察他呢。就在这一刻,他忽然觉得二人间有了距离,一腔热血也迅速冷了下来。临近毕业,苗珊向她摊牌:要么随她到茂县,要么分手,因为她爹妈只有他一个女儿。白吕说,我妈也只有我一个儿子呀,我不能扔下她走远。因为这件事不能调和,二人就真地分手了。那一刻,他们不像别的情侣那样找个地方来一次最后的狂欢或是痛哭,而是坐在宿舍里分饭票。苗珊又像往常一样,盘腿坐在床上,将饭票数了一遍又一遍,然后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
这就是白吕经历的爱情。五年后的今天,他走进这个遍植柳树的校园,目睹明处暗处那些成双成对的情侣,他真是有百般感慨。他在飞舞着柳絮的晚风中站立一会儿,决定到荀柰老师那儿看看去。在师院政治系念书的四年间,他最敬佩的就是这位在华东政法大学念过硕士的年轻教师。他思想敏锐,见解深刻,把每堂课都讲得振聋发聩引人深思。也正因为如此,校、系领导一直视他为危险人物,唯恐哪一天让这家伙给带来麻烦。这荀柰还有个怪癖:三十多了不结婚,整天同一些小女生来来往往。他曾在酒醉时对人讲:独身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当一只公孔雀,随时有向异性开屏的机会。我荀某拥有那么漂亮的思想之羽,不向她们炫耀太他妈可惜了。事实的确如此,荀柰只要有漂亮女生在场,他总是口若悬河妙语联珠,让女生们一个个如痴如醉眼神迷离。因此,他也就有了一个绰号“荀孔雀”。当然,也不是每个女生都崇拜荀柰,像苗珊,就嫌他太邋蹋,衬衣穿一个星期也不换。所以,白吕每当去荀柰的宿舍听他传道时,都是单身独往。白吕忘不了那些个夜晚,夜已阑珊而荀老师谈兴正浓,他将夹烟的那支手满天挥舞,像挥舞着一支启蒙的火炬……终于,大家不得不走了,走到楼下,男生女生们还回眸频频,仰望那个亮灯的窗口。有一次,一个男同学拉着白吕躲进花丛,他们亲眼看见有一个校花级女生悄悄回来,蹑手蹑脚上楼,接着那个窗子便出现了二人相拥的影子。白吕曾因此嫉恨过荀柰,发誓再不去那里,但这嫉恨终究敌不过荀柰对他的吸引,于是他又出现在一堆狂热的学生之中……
久违了,那样的场面,那样的聆听。白吕走上那座教工宿舍楼,敲响那扇熟悉的房门时,心中又出现了当年曾经的激动。他猜想,这扇房门的背后,肯定又是高朋满座热气腾腾,然而当门打开,他却只见到荀柰一个人。屋里,婴儿摇篮上掠着尿布,一股尿臊味与奶腥味扑鼻而来。脸上已有了一些皱纹的荀柰看着他道:“请问你找谁?”白吕说:“荀老师,你不认识我啦?我是八八级的白吕。”荀柰这才张了大口像已经记起来似地道:“噢……请坐请坐。”
坐下后,荀柰问了白吕毕业后的去向,又问他来平州干啥。白吕自嘲道:“你说我贱不贱,给人当枪手考试来啦!”他想,荀柰听了这事,肯定会训斥他一番的,然而荀柰却轻轻一笑:“可以理解,可以理解。”荀柰的这种反应,真是出乎白吕意料。再看看屋里那些讲究而应时的家庭摆设,他问:“老师,你什么时候结的婚?”荀柰说:“前年。”白吕像当年那样跟他开起了玩笑:“你不当孔雀啦?”荀柰听了哈哈大笑:“好,你揭我的短呀?告诉你,我是乐呵呵地当了几年孔雀,可是后来发现,被我的尾羽迷住的女生再多,也显示不出我生命的真正份量。”白吕不解地问:“为什么?”荀柰说:“这是我参加一次同学聚会时明白过来的。你猜怎么着,这几个递来名片,是处级、厅级;那几个递来名片,是系主任、校长;我他妈是什么?我又不能印一张名片,上写‘千名女生偶像’!操,权力意志是宇宙中最根本的一种力量,我怎么把先哲的话给忘了呢?所以,你老师就决定:痛改前非,接受规范,无论如何也得弄个系主任干干!”白吕问:“干上了吗?”荀柰说:“快啦。老主任眼看要退,我觉得我有戏。”
正说着,外面有孩子哇哇乱叫并用手打门。荀柰跑去开了门,一个长相平常的少妇领着一个小男孩进来了。荀柰向白吕介绍:“这是你师母,这是我儿子。”白吕便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师母”。然而师母并不怎么理他,朝他点点头就去打开了电视机。白吕觉得自己应该走了,于是就向老师告辞。荀柰把他送到门口,摆摆手就回到了房里。
走下楼来,白吕转身回望荀柰的窗子,发现那里的灯光与当年相比已经十分黯淡。他走在空旷的操场上,仰望着星空心想:荀柰讲的那种力量真是无处不在威力无穷吗?看来的确如此。渺渺太空中,星球,太阳,星系,黑洞……你争我引,不都是为了一个控制权吗?茫茫人海里,那些大大小小的官位,更是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不然,为何短短几年过去,风流潇洒指挥倜傥的荀柰为何有这么大的变化,甘愿去除棱角接受规范呢?
白吕明白,自己也在受着这种力量的摆布。如果不是这样,那他也不会抛却教师这个职业去考公务员,也不会在今天违心地为郭子兴替考。我,荀柰,郭子兴,还有普天下在这条道上苦苦跋涉的人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物质利益?有这个原因,但也不全是。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一旦权力在手,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于人类来说,这大概是最高级的一种需要,是最惬意的一种享受。
说到底,人类是一种政治动物。
然而,既然是政治动物,既然都想往权力的金字塔上攀爬,那就要有一套共同遵守的规则,不然的话就要混乱,就要互相践踏互相残杀。这套规则,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还远远没有形成。
不过,好的举措已经有了,他亲身经历的就有好几条。这次函授研究生考试,引来了那么多的年轻官员,就是一例。如果不是讲求干部队伍的知识化,“学而优则仕”,那他们干嘛来劳这个神?
当然,这规则也引来了投机分子,郭子兴是,我也是。如果我不想在墩庄镇当稳那个秘书,我何不以“白吕”的名义来堂堂正正地报考?
坏清名,毁纲纪。白吕不由得鄙视、厌恶起自己。他长叹一声,一边摇头一边走出了平州师院。
回到墩庄,白吕见了郭子兴,向他汇报说考完了。郭子兴问他考得怎么样,他淡淡地说:还行吧。郭子兴说:那好,你休息两天再来工作吧。白吕摇摇说:不用了,我该干啥干啥吧。郭子兴点头道:也好,明天你就和毕萌办办交接。
回到只住过一夜的宿舍,白吕看见池小娇的门上着锁,心中惘然若失。这些天来,在复习与考试的间隙里,他是经常下意识地想起这姑娘的,而且每当想起,便有一种与她见面的渴望。今天,他回来了她却不在,真叫人扫兴。白吕怏怏不乐地进了门,蔫儿巴唧地躺到了床上。
躺到傍晚,忽听门外响起摩托声。摩托在门外熄火后,池小娇的问话马上响起来了:“白秘书,你回来啦?”白吕兴奋地应道:“哎,回来啦!”接着一跃而起将门打开,将笑盈盈的姑娘迎进了屋里。到屋里站定,池小娇瞅着他,眼神里满含着渴盼与怨艾:“这些天你到哪里去啦?怎么说失踪就失踪?”白吕咧咧嘴说:“咳,我受郭书记之命,办一件事去了。”听他这样说,池小娇没再问下去,她往椅子上一坐,用指头轻轻敲击着桌面,幽幽地道:“你不知道,这些天我倒盼着这屋里闹鬼了。”白吕明白了姑娘的心思,胸腔中立马回旋起一股热流。他站在姑娘面前张牙舞爪地道:“那我现在就闹给你听——同志们!同志们!”池小娇努起小嘴,用拳头捶着他的胸膛说:“你真是个鬼!真是个鬼!”
闹腾片刻,白吕问池小娇这几天忙啥,池小娇说,她正忙着写论文——自己干着文化工作,总得拿出点业务成果。为了找材料,已经下村跑了两天了。白吕问她论文写什么内容,池小娇说,是关于鲁南民歌“五大调”的。白吕说,那是值得一写,音乐活化石嘛。说罢,他又问材料找得怎么样。池小娇说,不少呢。说着就从包里掏出了一个袖珍采访机。白吕道:“嗬,你还用了现代化的采访手段?”池小娇说:“挖掘民间音乐资料,真得有这玩意儿,手工记录太麻烦啦。所以,我就狠狠心去买了一个。你听听,这是方瓜坡一个老太太唱的。”她把采访机的键一摁,一个虽然苍老但又满带感情的女声便响了起来。机子里慢悠悠地唱一句,池小娇就给解说一句:“这是有名的《四盼》。说一个年轻女人盼望情郎归来,从春盼到夏,从秋盼到冬。你听,这是盼到了秋天:七月初七巧有安排,玉兰花儿开。打扫秋亭夜来香花开,等着那郎回来呀,哥哥来。八月初一雁门开,桂花香儿开。九月重阳菊黄花儿开,等着那郎回来呀,哥哥来……”
白吕注意到,池小娇解说一句,便向他瞅上一眼。那声音越来越温柔,目光却越来越火辣。到后来,白吕竟不敢再抬眼接那目光了。这时恰巧采访机里传出老太太的一阵咳嗽,才让他们二人之间的气氛降下温来。白吕笑道:“你让老太太唱这情歌,真是难为她啦!”池小娇说:“那我唱给你听?”白吕看看表,说:“以后再找时间吧。到开饭时间啦。”池小娇说:“是吗?那好,咱们打饭去!哎,我给你捎着,你甭去啦!”白吕不好意思让她人代劳,忙说:“不用,还是我自己去吧。”接着就去抽屉里找碗。池小娇见他这样,只好回了自己的屋里。
到了晚上,池小娇没再过来,却在自己屋里放那采访录音。她这一次用的不是采访机,而是收录机,所以声音大得足以让墙这边的白吕听见。白吕明白,池小娇这么做可以解释为放给他听,也可解释为她自己在整理资料。老太太咿咿呀呀,唱个不休,是什么词儿白吕听不清楚,但其中的韵味让他感受得真真切切。这时,池小娇那火辣辣的目光也又闪射在他的眼前。他想,古人道:落花无意,流水有情。现在是落花有意,他这流水岂能无情?当教师的这些年,别人先后给他介绍了好几个姑娘,讲才讲貌都比不上池小娇的,可是人家一个个都没把他放在眼里。现在,他才刚来镇上工作,池小娇就明白无误地发出了信号,看来当干部与当老师就是不一样。再想想池小娇这么招人喜爱,而自己年龄已经不小,不接受这份感情也没有道理。想到这里,他心里说,池小娇呀,你别让老太太受罪了,你干脆亲口唱给我听吧。可是,看看时间已经不早,他又不好意思去向池小娇表白,只好在老太太的歌唱中慢慢入梦了。
第二天早晨“上朝”结束,毕萌把白吕叫到办公室,将秘书这一摊向他做了交接。他将秘书职责内的事情大体上讲了讲,接着打开抽屉和橱子,将有关的文件、资料一一做了交代。这时,郭子兴走了进来。他看看二人说:“交接好啦?小白你准备准备,明天一早跟我到省里跑钱去。”毕萌问:“郭书记,这次带什么?再装几箱栗子?”郭子兴摇摇头:“栗子算什么?净惹人家烦。等钱批下来,给他们一点回扣就是。”毕萌点点头:“这样也行。郭书记,这次能向省里要多少?”郭子兴说:“估计三五十万没有问题。”毕萌道:“那真是不错。咱一个基层乡镇,能到省里要来钱,可不容易!”郭子兴说:“当然啦!问问别的乡镇领导,他们知道省政府的门朝哪?可我郭子兴,就能拱到阚省长那里要钱!为什么?还不是咱们前几年小流域治理有了名声,他来开过现场会?”毕萌连声说:“那是那是!哎,这一回能拿到手了吧?”郭子兴说:“差不多。我打电话问阚省长的秘书,说我上次递的报告阚省长已经批到财政厅了,叫咱们直接去找一个姓文的处长。小白,你现在去财政所找龚欣欣,拿两万块钱路上用。”白吕答应一声,便下楼去了。
财政所在大院西北角的几间平房里。白吕进去问谁是龚欣欣,一个小伙子向隔壁一指:“副所长室。”白吕走到那边,发现龚欣欣原来是一位挺漂亮的年轻女人。他说了来意,龚欣欣忽然将脸一沉,盯着报纸沉默片刻才说:“你写张领款条吧。”说着从空白信笺上撕下四指宽的一截纸给他。白吕写好,龚欣欣拿着出去,过一会儿便抱来两沓子现金给他。
晚上,白吕将这两万块钱从办公室带回宿舍,心里老不踏实,唯恐这笔他平生第一回接触的巨款有什么闪失。池小娇过来跟他聊天,听他说要跟郭子兴去省城,笑一笑说:“奇怪,这一回怎么不带小龚啦?”白吕问:“对,带小龚合适,跑财政厅,她可是业务对口呀!”池小娇又一笑:“不光跟财政厅对口,跟书记也对口呀。”从她的笑中,白吕便明白郭子兴与小龚有些暧昧。他不好多问,加上心里想着明天出门的事,与池小娇的谈话就不那么热烈与投入。池小娇看见他这样子,坐了一会儿便回了自己的屋里。
第二天早晨白吕刚刚起床,司机老商就过来喊他上车。他提了装着两万块钱的包跑到办公楼前,郭子兴早已坐到车上了。他上了司机旁边的座位,回头向郭子兴愧疚地笑笑:“郭书记,我来晚了。”郭子兴脸无表情,说道:“知道来晚了就好。”白吕坐下后,心里忐忐忑忑难受得很。
车子开出去一百多公里,他们在一个县城的饭店里吃过早饭,便接着往省城进发。行程中,郭子兴的手机不时响起,他从从容容地做着应答。又一个电话打来,郭子兴忽然不那么从容了。他说他正往省城去,电话里却响起一个女人的高声追问。郭子兴烦躁说:“没有,没跟她一块儿!你又瞎想什么呀?”说罢就将手机盒盖“啪”地合上。可是,几秒钟后铃声随即响起。郭子兴看看号码,打开手机高声说:“你这女人怎么这样?我说没有就是没有!”说罢干脆将手机关了。想不到,他的手机关上,老商的传呼机又响了。老商看看,偏一下头说:“余大夫的。”郭子兴说:“不要管她!”过了片刻,传呼机又响,老商看看,便将机子递给了郭子兴。郭子兴看看上面的内容,咬着牙骂道:“这个熊女人,真要撒泼呀?”说罢,他打开手机拨了拨说道:“余红你怎么这么任性呢?我说没有就没有!我这次只带了白秘书,不信你问问他!你等着!”说罢就将手机递到了白吕手上。白吕没经历过这种事情,迟迟疑疑地把手机举到耳边,里面就传出一个女人气汹汹地追问:“白秘书?你是白秘书?我问你,车上到底有没有龚欣欣?”白吕说:“没有,真地没有。”余红说:“哼,你们合起伙来骗我!我不信,我打电话到墩庄查去!”说罢就挂了电话。白吕把手机还给郭子兴,但没敢跟他说余红要到墩庄查的事情。郭子兴将手机往座位上一扔骂道:“操,干个工作怎么就这么难!前有高山,后有追兵,这不是要我的命么!”白吕不敢吭声,老商说道:“没事,她过去这阵就好了。”
可能是余红查到了龚欣欣的下落,直到进了省城也没再接到她的电话。他们到一个中档宾馆住下,吃过饭已是下午三点。郭子兴顾不上休息,便带车直奔省财政厅。进了大院,郭子兴让白吕在车上等着,他独自一人上了楼。过了两个多小时才下来,上车后跟老商说去凤凰饭店。老商一边发动车子一边说:“晚上请客?还是四星级的?”郭子兴说:“有五星级的,那就到五星级的,可惜省城没有。就这样,人家还不愿去呢,我软缠硬磨才叫人家答应奶奶!”老商说:“钱批了吧?”郭子兴说:“文处长说还没定下,这明明白白是要拿一把嘛!”
到了凤凰饭店,白吕进去一看,那种金碧辉煌让他惊呆了。他踩在织着巨幅凤凰图案的地毯上,感觉像腾云驾雾一般。随郭子兴去总台订餐,听小姐问是订六千六的,还是订八千八的,白吕大吃一惊,竟下意识地把腋下的包夹紧,恐怕被人抢去。他去看郭子兴,郭子兴也是额上冒汗踌躇不决。人家小姐倒有风度,一直微微含笑看着他们,直到郭子兴咬咬牙说出“八千八”这三个字来。
把标准定下,一位身段奇妙的女孩便带他们去看房间。那里,其摆设更加高雅。看见屋子那么大,老商嘟哝道:“能摆八张桌子为啥只摆一张?”郭子兴说:“摆八张桌子,那不成了咱墩庄的饭店啦?”
看罢房间,郭子兴便带他们两个坐在大厅里等,看那些达官贵人和花样美女出出进进。郭子兴用满含艳羡的眼神看了一会儿,回头问道:“老商,想不想天天住在这里?”老商笑着说:“咱能有这神气?郭书记你还差不多。”郭子兴笑一笑,又去看那些高级男女。
一直等到六点多钟,要请的客人来了。白吕看见,他们三男一女,个个神气得很。郭子兴弓着腰一溜小跑迎上去,捧起这个人的手晃一阵,再捧起那一人的手晃一阵。最后又打算捧那个半老徐娘的手,人家却避开了他。文处长拍他一掌道:“到底是乡镇干部,连规矩都不懂!女人不先伸出手来,你敢去握?”郭子兴红着脸说:“对不起对不起!山沟里来的,请多多包涵!”
来到包间,大家落座后,小姐便问喝什么酒。郭子兴去问文处长,文处长淡淡地说:“拿一瓶马爹利吧。”小姐问:“是喝金王还是喝普通的?”文处长说:“金王要多少钱?”小姐说:“一万。”听见这话,郭子兴大惊失色。文处长瞅着他笑道:“郭书记,露怯了吧?估计你也没带那么多钱。好了,本处长不让你犯难,就喝五粮液吧。”郭子兴大汗淋漓,结结巴巴地说:“还是喝妈……妈爹吧。”财政厅的几个人一起大笑,那个姓苏的副处长指点着他笑得岔了气:“你,你还喝爹妈呢!”那个女的笑着向小姐挥手道:“别跟他啰嗦了,拿五粮液去!”
酒一一倒上,菜也上来了。郭子兴羞羞惭惭地敬起酒来。他敬过三杯,又叫白吕敬,白吕便也敬了三杯。之后,郭子兴这么敬那么敬,三瓶酒便倒光了。这时,文处长也有了酒意,当郭子兴再敬时,他拍着硕大的肚子说:“老郭,你以为我这肚子就差你这几杯五粮液?实话告诉你,我这肚子价值百万!你信不信?你不信我算给你听听!喝你‘爹妈’一次就是一万,喝十回是多少?一百回是多少?一百瓶你爹妈值多少?不是值一百万?”这种带着辱骂的酒话,连白吕都听不下去了,而郭子兴依旧笑嘻嘻地道:“是,是一百万!”文处长又说:“老郭,你也培养培养你的肚子!来,你喝!我告诉你,拨给你的钱,底数是五十万,你喝一杯我就多给你一万!怎么样?你喝不喝?喝不喝?”郭子兴将桌子一拍:“好,我喝!”接着就一杯一杯地往肚子灌起来。财政厅的三个人给他计着数:一杯,两杯,三杯……郭子兴整整喝了十杯。文处长挥着手说:“好,那就是六十万!明天你回去,三天内我给你带帽拨下去!”郭子兴眼神迷离地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等客人走后,小姐把账单拿来,白吕和老商看看是一万两千八,都傻眼了。他们让郭子兴看,郭子兴已经趴在桌上打起了呼噜。白吕问小姐为何加了那么多,小姐说是酒水和服务费。白吕知道跟她争辩也无用,只好点钱给她。小姐拿着钱走了,老商看着她的背影恨恨地说:“就是操她十回也不值这么多呀!”
这时,二人想同郭子兴回去,却无论如何也叫不醒他了。无奈之下,白吕只好将他背起,由老商扶着,狼狈不堪地走了出去。白吕清楚地看见,在大厅内外,谁见了他们都笑。
回到住宿的宾馆,把郭子兴背进房间,老商倒了水想给他喝,然而二人把他扶着坐起,他不睁眼也不张嘴。白吕说:“坏了,郭书记八成是酒精中毒了。”老商听他这样说也冒了汗,忙说:“那赶紧送医院吧,出了事咱们可担不起!”二人于是又费力地把郭子兴弄到车上,几经打听,去了一家医院。在急诊室值班的医生看了看说,已经很危险了,要赶快抢救。说罢就让护士给他洗胃、挂吊瓶。老商把白吕扯到门外说:“白秘书,我看得把事情告诉欧镇长和余红,叫他们连夜过来。”白吕说:“你说得对,快打电话吧。”老商便到郭子兴兜里找出手机,先打给镇长,再打给余红。二人听后都是万分吃惊,说立马上路往这里赶。
急诊室里,被抢救过的郭子兴酣睡了一夜,天明时医生再来看看,说已经脱离危险了。这时,欧镇长和余红也来了。余红一来就扑到郭子兴的身上哭,结果把他给弄醒了。老商和白吕惊喜地跟他讲历险记,郭子兴听着听着也哭了。见他们两口子哭成一团,白吕不由得也红了眼圈。
早饭后,听医生说没事了,一帮人便决定回去。余红、白吕陪郭子兴上了老商的车,欧镇长自己在另一辆车上。郭子兴可能是体内的酒精还没消除干净,一路上多数时间都在睡着。余红一手抓着丈夫,另一手就拍打着白吕的车座向他诉说。她说小白你不了解,老郭真可怜呀!你看看,为了工作,把命都豁上了,这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可就是这样也感动不了领导,人家光叫他在乡镇受罪。老郭在乡下干了七八年了,当那么个熊官儿,几百口子跟他要吃要喝,害得他整天吃不安稳睡不踏实,遭罪呀!讲政绩,老郭比谁也不差,给市里县里都增了光添了彩,可一年一年就是提不起来,你说邪门不邪门?说一千道一万,就是那些管官的官太腐败了!不跑不行呀,不送不行呀,上边没人不行呀,上边有人可是根子不硬也不行呀!他奶奶那个腿!他娘那个大花叉……
听余红絮絮叨叨讲了一路,白吕也对郭子兴有了几分同情。他想,当个乡镇一把手也真是不容易,上上下下,哪一条不得操心?就说昨天晚上,为了多要点钱拼死喝酒,这真堪称壮举呢。说到提拔,凡是在仕途上混的人,谁没有那样的愿望?郭子兴在乡镇工作多年,按常规说也该提一提了。
进入山邑县境内,余红推推郭子兴说,到家了,醒醒吧。郭子兴坐起来看看窗外,喟然叹道:“咳,算是捡了一条命回来!”余红说:“你跟我回家,好好歇两天再上班!”郭子兴说:“好,今天就不回墩庄了。”
进了县城,老商把车开到一个居民小区,停在了一座楼下。白吕与老商将郭子兴扶到楼上,这才发现位于三楼的书记住宅既阔大又豪华。他还没顾上细看,老商便喊他走,他只好下楼上车,回了墩庄。
身为秘书,白吕晚上也必须在办公室值班。坐到九点回到宿舍,池小娇却又敲门找他,说是请他修改她那篇刚写出初稿的论文。白吕接过去粗看一遍,虽然他不太懂音乐理论,但能看出文章的结构不妥,语言表述也有些不太准确。他向池小娇指出来,池小娇歪头一笑:“那你快给加加工呗!”说罢就走了。白吕泡上一杯浓茶,静下心来,将那文章从头改起,直到下半夜才把它完成。
第二天八点,干部们一如既往地在会议室集合起来,欧镇长正要代替郭子兴做例行讲话,郭子兴却突然来了。但他还是让欧镇长先讲,欧镇长便把郭子兴的省城历险记向大家讲了一通,而后把他好一番称颂。郭子兴这时向他摆摆手,站起来说:“活着干,死了算!谁叫咱是共产党的干部呢!”他接着讲,这次去省里要来了五十万元,就用作干果市场的启动资金,过几天就奠基开工。白吕心想,文处长不是答应给六十万么,怎么还是五十万?
散会后,白吕回到办公室,郭子兴满面春风地过来说:“小白,我昨晚打听过了,考研的试卷已经判完,我的成绩过线了!”白吕听他这样说,心里有些反感,但还是笑着说:“好哇,祝贺你呀!”郭子兴说:“好是好,可我哪有时间学习?干脆,你就给我包到底吧,今后无论面授、考试,还是毕业论文,都由你代劳算了!怎么样?”白吕虽然不愿意,但他又不敢推托,只好点头道:“行呵。”
晚上,池小娇到他宿舍,他就把改好的论文给了她。池小娇看过后说:“哎呀,到底是大秀才,飞机上挂暖壶——高水平!小白,你让我怎么谢你?”白吕笑道:“你爱怎么谢就怎么谢。”池小娇瞅着他说:“那好,你把眼闭上。”白吕就顺从地闭上了眼睛。这时,池小娇就猛扑过来,在他腮上狠狠亲了一口。白吕吃惊不小,一边推她一边说:“礼太重了,太重了!”哪知池小娇却紧抱住他不放,在他耳边小声说道:“重吗?重吗?我还想把我全都给你呢。”白吕一听,这话他虽然爱听,但觉得来得过于突然。就说:“这么快?连个过程也不要?”池小娇这时将身体稍稍离开,两手抓着白吕的肩膀,泪汪汪地瞧着他说:“怎么没有过程?在我来说,这过程也太长太长了!你不知道,我来镇上这两年,遭了多少骚扰,受了多少委屈!我刚来的第三天,郭子兴就让我半夜十二点到他屋里。我不去,他就干脆来敲我的门!敲一次不给他开,敲两次还不给他开,就彻底把他得罪了。从那以后他瞅见我就来气,经常在大会上批评我工作不行,动不动就给我小脚穿!可是,无论他怎样,我也还是不屈从。我想,我池小娇就是要清清白白做人,早晚要找一个我爱的人,把清清白白的我交给他,然后跟他相濡以沫白头到老!我盼呀,盼呀,可是这个人一直没有出现,直到半个月前你来到这里!白吕,你不知道,我是多喜欢你,你不在的时候我是多么想你……”
池小娇的诉说,让白吕十分感动。他没想到,眼前这个娇小的姑娘竟有着那么坚强的意志与操守。他想,能跟这样一个人共同生活一辈子,也真是我的福气。但他转念一想自己的情感经历,比照一下池小娇,不禁又自惭起来。他说:“小池,我敬佩你,也感谢你。可是,可是……”池小娇说:“可是什么?”白吕低头道:“你清白,我可不清白了,我在大学里谈过一次……”听了这话,池小娇先是现出片刻惊愕,而后却摇摇头说:“我不在乎,不在乎,只要你知道我的清白就够了。”说罢,她抬手将灯拉灭,站在白吕面前呼呼急喘。感受着久违的女性气息,白吕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将池小娇搂到怀中,和她一起倒在了床上。
池小娇直到凌晨三点才回了自己的屋里。白吕困乏不堪,倒头睡了过去。似乎是刚刚睡了一会儿,耳边却又响起池小娇的声音:“醒醒吧,该吃饭啦!”他睁眼一看,原来太阳已出,池小娇已端着两份饭走进屋里。他急忙坐起身问:“哎呀,你给我打饭,就不怕人知道?”池小娇却莞尔一笑:“知道了更好!”看着她的表情,白吕明白了池小娇这么做的用意。他只好点点头说:“好,不怕不怕,随你的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