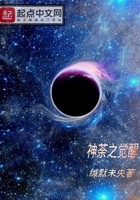回营路上,吴升将自己被龙卷风卷走,越过燕山,掉到雁门关南边,正好被运粮的玄武营第二曲的魏龄小队解救的事情告诉了徐飞。随后魏龄小队将“捡获”襄武营士卒的事情报了上去,在前天,都护汤允恺亲自在演武场接见吴升,大大嘉勉了一番,同时提拔为什长(也就是小队长)。由于襄武营编制已经不存在,便让吴升进入玄武营。
今天,正好吴升小队奉命到雁门关西侧修补下水井,却没想到这个下水井侧有个凹陷进去的山洞。吴升一时好奇,便带队进去摸索了一番,发现是个死洞。正待出去,便听见徐飞隐隐约约的呼救声。于是吴升叫人找来夯城墙的大石锤,几下就砸开了这堵墙,救出了徐飞。
吴升说完,兴冲冲地又道:“飞哥,你是第二个襄武营幸存的人,我已经叫手下通知汤帅去了,你等着,汤帅一定也会在演武场为你举行一个欢迎会的!”
此时的徐飞坐在满载泥土和工具的板车里,正狼吞虎咽地吃着烙饼卷熏肉,腮帮子鼓动得正欢,完全没空回答他。
吴升笑容满面,继续一个人说书似的唠着嗑,跟着徐飞座下板车,往雁门关西侧自己的驻地走去。
走了一会儿,前面迎面驰来两匹马,一匹马上骑着一个人,另一匹马空着鞍。那人大叫:“哪位是今天找到的襄武营兄弟?”
“在这里,长官!”
吴升听了,满面红光地大叫起来,他见这人身上是区别于一般士卒的铁叶甲,所以开口便称呼长官。
那人笑嘻嘻地打马过来,看见穿着虎皮的徐飞,便冲他抱了抱拳,说:“这位兄弟,汤帅请你到都护府一叙。”
徐飞苦于嘴里塞满东西,无法应答,只得急匆匆地往下硬咽,却急切咽不下去,食物噎在嗓子眼里,半晌说不出话来。
“这位长官怎么称呼呀?”吴升凑上去,讨好地笑道。
那人皮笑肉不笑,半是勉强地回答道:“鄙人包德旺。”
吴升又笑眯眯地问:“包长官在哪个营高就啊?”
包德旺笑容僵硬起来,看了吴升一眼,又不好发作,不冷不热地回答道:“鄙人在都护府里任职。”
“哦,是护卫大人,失敬失敬。属下玄武营第六曲,什长吴升。”吴升忙不迭地点头哈腰。
徐飞有些奇怪地看了吴升一眼,这小子和以前不一样了,好像多了点什么,又少了点什么。
包德旺没有再看吴升,对着徐飞,又恢复了那种居高临下的微笑,说:“这位兄弟请上马,跟我去见汤帅。”
吴升看了看徐飞,又凑上去笑着说道:“我这位兄弟刚刚从山里捡了条性命,身子有些虚弱,包护卫看看能不能等他回营休息片刻再……”
“大胆!”没等吴升说完,包德旺瞪眼大吼起来,把周围人都吓了一跳,“这是都护大人的命令,谁敢拖延,就是杀头之罪!”
吴升有些发愣,他刚回来的时候可不是这般光景啊。一时手足无措,只是低头道:“属下不敢。”
徐飞这时已经咽下食物,拍了拍手,跳下车来,对包德旺说:“护卫大人息怒,我这就跟大人去。”经过吴升身边,拍了拍他肩膀,说了句:“谢谢你救了我”。
徐飞歪歪扭扭地控制着马,一路走过雁门关内大大小小的营房,鼓台,武场,兵器房,来到了一个青砖砌就的房子门前。
“这位兄弟,请。”包德旺跳下马来,伸手做了一个请进的动作。徐飞下马后,抬头看了看红漆写着的“都护府”三个大字,和厚铁皮包着的铜环大门,走了进去。包德旺跟在他左后方也走了进来。
两旁的卫士将门缓缓关上。
包德旺一路无话,脸上也没了刚见徐飞时那满溢出来的笑容,只是急匆匆地带着他走进了中堂,向右一拐,穿过一个短短的走廊,又进了一间小小的,没有窗户的屋子。
“请进。”包德旺再次伸手。
徐飞心里暗暗警惕,一步跨进房内,包德旺在外面把门关上。
房内正中间太师椅上,坐着一个五十多岁的高大老者,穿着便服,花白头发,眉头间隐含忧色,脸颊和眼角爬满了皱纹。
徐飞单膝下跪,朗声道:“襄武营第五曲什长徐飞,见过都护大人!”
汤允恺道:“你起来吧,老夫叫你过来,就是想问你一些事情。”
徐飞起身,心里迷惑不解,身为拄北军首领兼雁门关都护的大人物,会问一个无名小卒什么事情?
汤允恺望了望门外,似乎有些不放心,徐飞用余光看了看四周,发现这间屋子里只有他和汤允恺两人。
汤允恺咳嗽了一下,压低声音严厉地问道:“你在燕山地洞里,见到了什么?”
徐飞愣了一下,对方紧紧盯着他的眼睛。
若是十天前,徐飞在这目光逼视下,必然会觉得窘迫不安而移开眼睛,或者低下头颅。可是短短十天内经历了六次生死关头后,徐飞心志的坚强早已远非凡人可比,被一个大统领这样盯着,他其实并没有什么感觉,如果强行要说一种感觉的话,那就是:
恼火。
徐飞恼火的是,为什么同是襄武营残卒,吴升回来就得到当众嘉勉,而他回来以后就要像犯人一样受审?他恼火的是,步军三营在雪地里浴血厮杀时,都护坐在城里闭门不出。等士兵九死一生回营后,却莫名其妙地表现出不信任来。他稍稍抬起头来,看了一眼汤允恺,却并没有说话。
雁门关都护顿时觉得自己的威严受到了这个无名小卒的挑战,心里暗暗骂了张望几句。但他不动声色,把语气放缓,尽量摆出和颜悦色的神情来,把问题重复了一遍。
徐飞这才惊觉自己刚才对雁门关最高长官有些太无礼,忙低下头去,把自己如何掉进地洞,在地洞里见到墓碑等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说完,汤允恺半晌没有作声,徐飞又抬起头来,只见这位老都护一脸震惊,嘴里喃喃自语道:“原来如此……”他见徐飞望着自己,忙从失态中恢复过来,正了正身子。说道:“徐飞,你听着,”汤允恺表情异常严肃,“这件事关系重大,你不能把它告诉给任何其他人,要烂在肚子里,知道吗?”
徐飞愕然,呆了一呆。
汤允恺见他这种表情,突然厉声说:“你已经告诉别人了?”同时眼神闪过一丝杀意。
徐飞被杀气冲得一激灵,说:“还没有。”
汤允恺眯着眼睛,似乎放下心来,说:“那就好……那就好……”说着站起在房间来回踱着步子,徐飞只得在一旁静立,看着都护大人的脚步来回在阴影和阳光处穿行。
“你,能保守这个秘密吗?”汤允恺缓缓问,没有回头。徐飞看不见对方的表情,只是不由自主浑身绷紧,他感受到了危险。
但是他没有做声,他仍然不知道这样保密的意义何在。况且,他已经在那十二块墓碑前许诺,会将他们的埋骨之地告诉他们家人。如果依从汤允恺,岂不是要让他食言?
尽管那是对素不相识的死人的诺言。
徐飞不愿违背诺言。他选择沉默。
汤允恺见状,眼中杀意更浓,语气却转而温和起来,劝说道:“既然你还没有告诉其他人,本帅就告诉你,这是许多年前一桩天大的秘密,事关本朝多名重臣,和大成朝的气数。”他故意顿了一顿,看到徐飞有些惊讶地抬起头来,继续缓缓说道:“你若是将消息泄露出去,被别有用心的奸人利用,那么大成朝会有翻天覆地的危险灾祸!你可知道?”
徐飞觉得自己刚从死亡中脱身,竟又卷入如此凶险的漩涡中,不禁冷汗涔涔。他思索片刻,抱拳道:“请问汤帅,那十二墓碑下,所埋究竟何人?”
汤允恺却冷冷说道:“不该知道的,你最好不要知道!”
徐飞被他这一套话激起倔强之气,站起身说:“那么我也没必要发誓保守一个我不知道的秘密。”
汤允恺眼睛眯了起来,一拍扶手,厉声说:“大胆!”便站起身来。
房门被踢开,包德旺一个虎跳冲了进来,手握刀柄,杀气腾腾地看着徐飞。
徐飞没有动,从包德旺的身手可以看出,自己躲开他的砍劈没有问题,他此刻只感到一股莫名的悲愤。
“都护大人,”徐飞再度抱拳,言辞恳切地说:“非是小人不遵将令,只是我已经在地下对那十二块墓碑许下承诺,将此事告知他们家人。小人得以脱险,也是冥冥之中依仗这十二人的阴魂保佑。如果都护不愿告诉我事情真相,而是一味强人所难,那恐怕小人会让都护失望。”
汤允恺没想到一个小小什长在自己面前竟然如此硬气,脸都涨得血红,胡子不停抖动。他目露凶光瞪着徐飞,而后者也毫不畏惧地坦然与他对视。房间里的气氛越来越剑拔弩张,包德旺的手已经在缓缓拔刀了。
“报~”一名传令兵的急促脚步打破了这气氛,传令兵飞奔进屋,单膝跪地,气喘吁吁道:“辫奴人大军,开到关下了。”
汤允恺大惊,他顾不上管徐飞。便带着包德旺急急向外走去,临出门,他回头看了徐飞一眼,说道:“好自为之。”
徐飞拱了拱手,等了一会儿,也踏出门槛。
汤允恺上了北面城墙,只见关下的皑皑白雪中,一大片黑压压的辫奴人正缓步朝雁门关推进,他们中有骑兵有步兵,列成了十二个方阵,看上去极有章法。
“大概六万人。”早就在墙上观看的郭行俭对汤允恺说。郭行俭又望了望北方远处那一缕已经燃烧了两天,快要断绝的红色狼烟,接着说道:“看情形,前关应该已经失守了。”
“嗯,”汤允恺点了点头,又观察了一阵,脸色松弛下来,指着下面的辫奴人大声道:“我不明白,是什么给了他们这么大的勇气,让他们敢来进攻雁门关?”
他爽朗地谈笑着,拍了拍身前坚实稳固的垛墙。
“难道是这半生不熟,不知道从哪儿偷来的阵法?”
“还是这些和筷子一样的云梯?”
城墙上驻军都被主帅乐观的情绪渲染,笑了起来。
远处有一些高高的黑影在靠近,那就是汤允恺所说的“筷子云梯”了。可是随着这些黑糊糊的东西逐渐从远方迷雾中缓缓开出,显露出真正面目,便有眼尖军士叫起来:
“那不是云梯!”
“这是什么怪物?”
骑着白色骏马,头戴银色面具的林文靖此刻正在雁门关下,图烈汗身边。他看到关头似乎起了不小骚乱,便躬身对图烈汗行礼,道:“大汗,彼军已经动摇,这正是使用‘井栏’的时机!”
图烈汗闻言,手一招,号角吹起升调,那些几乎于雁门关墙头齐高的井栏开始加速朝关墙开来。井栏骨架和护板均由粗壮柏木、杉木造成,刷涂了防火泥,外面还覆盖着坚韧的牛羊皮,每个井栏高十丈,长宽各两丈,下粗上细,内部分为三层。底层为推动部分,里面有十名大力士负责推动,井栏底部亦装有四只直径超过七尺的超大木轮,用来减小推行阻力。中层为驻兵层,可以容纳二十名士兵,顶层为接战层,装有一块活动的,末端有钩爪的厚实木板。而最顶上也装有护栏,无疑是用于箭楼和瞭望之用。
看着这些巨兽般的高楼碾着积雪桀桀压来,汤允恺心里突然一阵恐慌,他第一次觉得这厚实的城墙没那么可靠了。但片刻后,他冷静下来,开始指挥防守。
“敲鼓,全军进入接战状态!”
“准备长竿钩枪火箭,还有石头!”
“多派点弓箭手来,越多越好!”
一连串命令发布下去,汤允恺心中稍定,他望着那些设计精良的战争器械,心中浮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林文靖,是你吗?”
“你果真投靠辫奴了吗?”
汤允恺心里暗暗叹了口气,偶尔飘落的雪花将他的思绪又引回三年前那个冬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汤帅,行俭,这情报可靠吗?”
二十五岁的瘦高青年身穿闪闪发亮的鳞甲,披着白色大氅,骑着白色牡马,疑惑地问道,人马呼出的雾气弥漫在雁门关下。
“这个请文靖放心,我安排的‘钉子’非常可靠,辫奴人一定会穿过碣石原,在那里伏击定可大大斩获一笔。”郭行俭骑在黄色马背上,笑着说道。
“我们在关内摆下酒宴,等待文靖奏凯而还!”
林文靖眼中的犹疑之火熄灭了,毕竟他没有理由不相信眼前这个雁门关最高长官。他简单地行了一礼,便拨马回头,领军消失在茫茫雪地尽头。
雁门军中有不成文的规定,要是想得到大家认可,无论是武将文官,都要有实打实的军功在身。而像林文靖,郭行俭这样的幕僚谋士,获取军功最快的方法就是“打草票”。“打草票”意思是到关外,寻一个小部落,掳掠一些牛羊物资,和一群辫奴妇孺回来,这样几乎不用进行真刀真枪的硬拼,也没有什么危险。这次是林文靖第一回出关“打草票”,目的就是积攒军功。
在他出去后,汤允恺和郭行俭交换了一下眼神,长长吐了口气,小心地问道:“没问题吧?”
“万无一失。”郭行俭眼睛望着北方,冷笑着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照这么说,你直接顶撞了都护?”吴升坐在自己小队的车仗前,听着徐飞回来抛出的劲爆消息,眼睛吃惊地瞪得溜圆,“怎么会这样?”
徐飞摇摇头,神情严肃,他没有把原委告诉吴升,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好友卷进这件事来。
“吴升,我只是不愿做他交给我的一些事情罢了。”
“哦,”吴升一时说不出话来,抱膝坐在他对面,皱着眉头。过了一会儿,突然说:“要不我跟王统领说说,看看能不能把你调到运粮队,这样成天跑运粮,他就不能刁难你了。”
徐飞吐了口气说:“不用,我不违军规,不犯军法,堂堂正正做好本分事情,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吴升叹了口气,说:“飞哥,这世道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这当官的有权力在手,随时随地都可以让你难受,可没那么简单啊。”
徐飞注视着吴升,说:“吴升,你好像和之前不太一样了。”
吴升呆了一下,随后苦笑一声说:“飞哥你也发现了,我比以前更加会察言观色,更加奉迎那些官儿们了,是吗?”
徐飞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吴升把手摊开,又合拢。双眼聚焦在某个不存在的点,缓缓说道:“那天你受伤了,我去给你要煤炭配额,张统领不理我,还讽刺你可以投降辫奴。”
徐飞眉头一皱,眼中迸出一丝火焰似的光亮。
“我当即与他吵了一架,然后他就把你的配额减半了。后来营里兄弟们一人凑了一点,给咱们凑了一麻袋木炭。”
吴升平静地说着,语调没有一丝波动。
“那天夜里我想了很多,之后也一直在想。后来我想通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权力就是寸步难行,就要处处看人眼色,仰人鼻息。军中的权力,虽然伴随着血与谎言,但我一定要得到它,让它为我所用。”
徐飞沉默着,缓缓出了一口气。
“飞哥,你可能理解不了我,你从小光明磊落,武功又强,什么都不怕。但是我真的不想再像那天一样,站在大家面前哭哭啼啼;不想和人争吵后担惊受怕;不想被人拿着当剑使,随后又抛在垃圾堆里。”
吴升把脸埋在双手里,肩膀微微抖动。徐飞安慰似的拍了拍他的背。
“我明白,吴升,你不用再说了。”徐飞看向吴升,目光里有些晶莹,“你救我性命,我很感动,我理解你。”
就在此时,外面突然喧嚣起来,有人大叫:“吴升!你们小队,去找大石头,速速运到北墙头去,快!”
“是!曲长!我立刻就办!”吴升一个激灵从地上弹起,拿着身边的手推车就往外冲,招呼着手下:“张虎!赵林!岳大柱!你们几个,快推车去西城找石头!”
“头儿,仓库没有石头吗?”
“那你们谁去仓库看看!其他人分头去找!”
……
看着吴升手忙脚乱地吆喝起来,徐飞也站起来,帮着把绳子、凿子、扁担这些工具搬上手推车。
关内越来越嘈杂忙碌,就像一锅被煮沸的开水。徐飞见吴升忙不过来,便自告奋勇地帮着拉车。满满一车石头异常沉重,平时两名军士才能拉动,而徐飞独自一人肩上绑着几条粗大的麻绳,奋起神力,竟能拉着车飞跑起来,看得玄武营军士目瞪口呆,纷纷互相询问这是何人。
吴升跟着徐飞跑着,一路上碰见武场的部队集合、看见一队队装备严整的弓弩手跑过、看见从北墙方向抬来的一具具尸体和伤兵,伤兵的哀嚎声、靴子的梭梭声、时不时响起的军官怒喝声、运物资车轮的咕咕声,奏响了雁门关的守城协奏曲。
运了好几趟,手下说仓库石头没了,吴升突然想起一事,说:“今天早上的下水井!那个洞里不是有一面被拆掉的石墙吗?”说着便推着大车朝西城跑去,徐飞闷头跟着,他也想再去那里看看,可能会发现什么线索。
到了洞里,却只见那墙又被人给砌回去了,要不是岩石边上白色的浆灰还没干,吴升真怀疑上午自己是在做梦。
“奶奶的,”吴升骂了一句,“这修墙的动作好快。”便掉头往回走。
徐飞心下凛然,想着:“动作好快。”脑海里又浮现出方才汤允恺的话来“多年前……一桩天大的秘密……”他不禁开始琢磨。
“这暗无天日的地缝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让他如此紧张?”
路上的伤兵越来越多,吆喝催促的军官们也越来越多,不时还会有一两支羽箭从北墙那边飞来。
“辫奴人攻进来啦?”吴升有些惶恐地说。却立刻被一根马鞭狠狠抽在背上,一名穿着红色皮甲的督战军官朝他吼道:“不想活了?瞎嚷嚷什么?”
吴升低下头,连忙说了句:“对不起。”打算继续跟着车跑。拉车的徐飞却停了下来,把麻绳撩在一边。几步就走到那军官跟前,下巴顶在他鼻子上,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你敢抽我兄弟?”
那军官见这人虽然披着一件肮脏的毛皮,看上去像卖苦力的,双眼却如猛虎一般饱含着杀气,他环顾四周,见没有人注意这里,口气软下来,说:“他刚才说话扰乱军心,我提醒他一下。”
徐飞说:“我们是玄武营的,不是车夫,你说话注意点!”
那军官忙点头道:“没错,”随后向吴升说:“这位兄弟,刚才对不住了,我性子有点急。”
吴升忙点头说:“没事没事,互相体谅。”徐飞这才作罢,继续拉上运石车。
他们路过校场,只见那里气氛异常凝重,士兵们站的整整齐齐地,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碗,一名将领端着碗站在高处对他们说:“家中有兄弟的,前进一步。”
一排人站了出来。
那将领又道:“有子女的,前进一步。”
后排不再动,刚才出列的一排又有一部分悉悉索索地站到最前面。
那将领举起碗,众军也举起碗。
将领仰脖一饮而尽,说道:“祝你们得胜而归”。话音飘在雪地里,似乎有些模糊。
众军也纷纷饮尽碗中酒水。
徐飞回头和吴升对望了一眼,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他们心知肚明,这是军中在选拔敢死队,不知道又要执行什么必死的任务了。
送完石头回营,忽然听到营帐里一声有点耳熟的声音:“徐飞呢?他在哪里?”徐飞掀帐进去,说道:“我在这里。”
那人正是包德旺,他站起身来,说道:“汤帅有令,襄武营徐飞编入敢死队,火速去校场报到!晚食前不到校场,立斩不赦!”说完,把象征着军令的令牌在众人面前一晃,擦着徐飞肩膀出帐去了。
徐飞和吴升站在原地,如受雷劈,动弹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