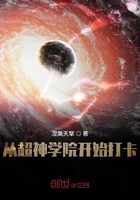卯时,赵云出去了便一直没有回来,恶狗倒是不急不躁,安心地坐在屋中角落读着《闭息法》。过了好大一阵,直到临近辰时,赵云终于回来了,进了屋看着恶狗,脸上浮现出一丝歉意。恶狗看着赵云表情心中有数,像他这种声名显赫的将军对自己这样一个无名之辈感到歉意,大约只有一种情况:承诺过的事情做不到了。
也是正常,赵云刚刚出去将近一个时辰,一定是府中事物有所变化,毕竟自己刺的是荆州之主的嫡长子,能死能活可不是赵云这样一介主骑郎能说了算的。这世上有一种人,他们尽力活着,活不下去时也不畏惧死亡,恶狗就是这样一种人,生无望,欣然受死便是。于是将《闭息法》收回怀中,从座上站起,与赵云平静地问道:“将军不能放在下走了?”
“这个……卯时已过,错过了换防,确实有些麻烦了。”听赵云言语支吾,恶狗更确定了自己的判断:“那是将军动手,还是在下自己动手?”
“什么动手?”赵云不明就里。
“将军不放在下走,在下也绝不会招半个字,以其遭受酷刑之苦,在下这条命交出来便是。”恶狗眼神有些黯淡,仿佛对这世间的光明已不再留恋。
“本将军何时说过不放你走?”赵云言语之中带着不悦,甚至有些怒气,对他这种武将而言,那些“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之类的道义代表着某种不容羞辱的尊严,这种尊严自然不是恶狗这种无名之辈能体会的,否则,他也不会问出那种话来。
见着赵云反应,恶狗才知自己言语多有不敬,遂抱拳请罪:“在下见将军进门面有苦色,以为事态有变。多有得罪,还望将军海涵。”
赵云并未与他在意,那似有似无的歉意又浮了上来,解释道:“我说了卯时放你,但因府中事务耽误,错过了时辰,自然惭愧。主公又决意今日离城,也等不了下一个换防时辰。本想将你混入甲士之中,但我随主公进府只带了二十名亲卫,又有寅时公子遇刺,离府多出一人,可不是件小事,也是一时苦恼。”
恶狗听他话里,以为赵云苦于杀他有违道义,放他又没有良策,为此两头为难,遂说道:“无妨,在下进来州府,出得去便出,出不去也早有准备。”说完,拔出短剑就要自刎,赵云抢前一步制住了他的手,说道:“倒也不必如此,你先听我说完。”待恶狗将剑收起,赵云又道:“你的事我已禀明主公,主公说若你肯帮个忙,他有办法带你出去。”
“何事?”
“为我军打探一件事情。”
“还请将军详述,如此事不利我主,在下交出项上人头也不可答应。”
“近几日会有一批粮草运抵襄阳,城中交付之后再运往军屯。你能否充当我军几日耳目,探取这批粮草动向?”
事情听起来与马家毫无关系,也并非什么难事,但正因为并非难事,让恶狗直觉此事有些诡异,思索一阵,将心底的疑惑说了出来:“以将军之尊,城中布置几个耳目并非什么难事,何需临时求助在下?”话一问出,恶狗敏锐地察觉到赵云脸上那丝歉意之中又隐隐见着了一抹难色,也是酝酿一阵,方才与他坦诚:“实不相瞒,我等入城之时,本是派遣侦候一十三人潜伏城中,专候此事。岂料方才卯时北街大火,一十三人尽在火中毙命。如今,我在城中断了耳目,甚是被动,故而问你。”
恶狗是个规矩人,在他看来世上诸事需得有借有还。赵云放他一马,让他可以继续借着马家的命,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恩情,虽然不是马家那般如山的恩义,但也是要还的。“如将军所说粮草正旦之前到达襄阳,此事在下可给将军一个详细。如正旦之前未到,请恕在下无能为力。”
“可。”赵云欣然接受,那丝歉意也随之消去:“如此,只待出府之际,我令一名亲卫卸甲,藏身主公轩车之中,你换上亲卫甲胄,随我左右,带你出府。”“谢将军。”恶狗伏地谢恩,心中却是起了一丝波澜。他刚一答应,赵云便告知了出府的方法,这是早就有了对策,只待他答应。当然,要藏一名亲卫在轩车之中,不可能是赵云能做主的。只是他所在意的情义,在一些人物那里不过一种交易……也罢,能活下来便是,没有什么比留着命报答马家的恩情更重要了……
与占巴一道北城门出了城,行至沔水河畔,矢呼交代道:“我有些事情,需得前往新野,你回去草堂,带几人过来,襄阳留一人与阿芽联络,其余人安排在襄阳到宜城之间。你不可再进襄阳,布置完以后就留在四公子身边,把握各点之间的往来。”“带哪几人来?”占巴问道。“带几个死了你也没那么难过的吧。”说完,矢呼深深叹息一声,又意味声长地拍了拍占巴的肩头,转身而去,只留占巴寒风之中独自茫然……属下面前,矢呼无论何时何地,看上去永远都是镇定的,其实今日清晨见过芽以后,他内心早已忐忑不安。倒不是因为得知蔡琰欲杀马良,毕竟“戌组”的行动本就指向蔡家,蔡家也不是什么脓包软蛋,其中尔虞我诈、暗藏杀机再正常不过,这种事他见过太多。但芽说马良似乎暗通“寅组”,他有些不能接受,毕竟,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他也见过……
新野城中一间宅子的地下室里,一阵高傲的脚步声传来。虎遍体鳞伤,被人从地上拉起,扔到那座固定在地上的铁椅子上,他瘫软地靠着椅背,倒是让打他的人省了捆他的气力。虎费劲地撑开肿胀的眼睑,往那脚步声的方向看了一眼,用仅有的余力勉强将笑容支撑得猥琐,有气无力地说道:“姐姐来看我啦?”说完话,那肿成一个大包的眉弓仍是不忘吃力地往上抬了抬。“你还真是打不服啊。”寒鸦冷笑道,冷艳的脸上见不着生气,保持着第一次出现在虎眼前时的那份端庄从容。随即,寒鸦吩咐属下退去,室中只留了她与虎两人。见此情景,虎又不安分了,嘴上抹起油来:“这才是嘛,那些个外人早该支走了,就留我跟姐姐共处一室,何其美哉?若是獾姑娘也在,那更是美上加美。”
“你莫急着嬉笑,且听我先与你说件事情。”寒鸦虽然冷漠,但她语调始终那样舒缓优雅,仿佛从她口里出来的每一个字都透着淡淡的清香。这样的声音入了虎的耳朵,自然是心神俱醉,那抹了油的嘴更是闲不住:“姐姐声音就是好听,能说出这么好声音的嘴巴,亲一亲芳甜可口,回味无穷,终生难忘啊。”寒鸦也不搭理,就站他面前冷眼看着他,虎自己觉得没趣,也不闹了,稍微正经了些,问道:“姐姐有何事要与我说的?”
“襄阳那边得来消息,‘丑组’首领失踪多日,十有八九已经遇害;前几日,有许都商人满城寻一位姓马粮商不着,跳井自杀;今日清晨,‘寅组’据点突起大火,连首领在内一百零五人全部烧死。这几件事都是你们‘戌组’入了襄阳之后接连发生,可是与你们有关?”
“我说我的个好姐姐,你看我这样子像是知道的么?”
“猜你也不知。”寒鸦停顿了一会儿,那副从容的表情并没有什么变化,但虎隐隐察觉到她似乎是在思索着什么。只见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说道:“能做隐门十二支的首领皆不容易,需得不惧严寒酷暑,不受食色诱惑,不屈威武压迫。‘丑组’失踪的首领女冰,年过五十,风霜雨雪,毫无怨言,终生守身如玉;‘寅组’烧死的首领弥崎也是严于律己,任劳任怨。他二人一生兢兢业业,赤胆忠心,最终却一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一个死的惨烈,被烧成一具黑炭,走得无名无姓,连个祭奠的人都没有。活着时,躲在影子里;死了,也跟烂在泥土的落叶一般,一生到了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怀念,仿佛世上从来没有来过那么一个人……”寒鸦合上了双眼,略显刻意的隐藏着眼中滑过的一丝伤感。须臾,又睁开那双冷漠的明眸,说道:“得知他二人下场我很震惊,也很悲伤,为我自己悲伤。我寻思,我已三十有五,此生已过半程,或许有一天我也难逃他二人同样的下场,但无名无姓,遭人遗忘未免太过悲凉……”她的语气仍是舒缓,声音依旧婉转,只是这份舒缓与婉转当中隐约多了一丝让人心痛的哀伤。
可虎这样一个愣头青,哪管她什么情绪,只道她是用刑不中,又来怀柔,反正他是软硬不吃。有这么一个风姿绰约的美人姐姐在面前,身子动不了,嘴上也先占占便宜再说。遂嬉笑道:“谁说的,姐姐香吻那么甜,我能记一辈子,我怀念你啦。”“你莫要嬉闹。”寒鸦冷冷的口吻当中较之前已然少了些许生硬。“我可真诚啦,现在是脸肿了可能看得不明显。”虎尽力挤弄着臃肿的眼泡,猥琐地撅起煞白的嘴唇向寒鸦做了个亲嘴的动作。“实话与你说,那日你亲我,是我平生初次与人亲近,至今我亦久久不能平静……”寒鸦冷漠的眼神渐渐褪去,那双明眸微微流露出的光宛如夜晚藏在云层里的月亮,羞于示人,却又用一圈圈斑斓的月晕告诉着人们它就在那里。
虎再怎么愣头愣脑此时也察觉到了寒鸦神色的变化,那游刃有余的猥琐当即散退了去,紧绷的身体写满了不安,紧张地问道:“什……什么意思?”
“我要你娶我!我不要孤独终老!”
寒鸦的话声音不算大,却一字一顿清晰明了,连语气都破开了那层舒缓与优雅,从她口里吐出的每一个字都掷地有声,铿锵有力!只震得虎瞠目结舌,呆呆的半天不能言语。懵过好大一阵,回过神来,当即犯了怂,慌慌张张从椅子上艰难爬起,“扑通”一声摔倒在寒鸦脚下,张皇失措地紧忙道歉:“姐姐,首领,我……我开玩笑的,您别当真啊!小的不懂规矩,要是有什么地方冒犯了姐……首领,还望首领大人有大量,不要跟小的计较!”
“你若娶我,我把獾许给你做妾。”
“真的啊?”虎忍不住一喜,不过瞬间之后还是怂了下来:“可是……这……这不是什么妾不妾的事儿,我……我就是来搞搞情报,回去好给主人有个交代,撑死了也没想情报没搞到,搞一对妻妾回去啊。我这是来干活的还是来提亲的啊?回去还不给他们几个嘲死。”
“娶了我,要什么情报我给你。”
“不是……首领,您听我说啊,我……我是‘戌组’的,您是‘辰组’首领,这要成了亲,是我算‘辰组’的还是您算‘戌组’的?都挺麻烦的,对不对?还是算了吧。”
“你是‘戌组’留在我‘辰组’的通传。”
“还能这样?我……我……”等了虎支吾半天也没“我”出个什么来,寒鸦蹲下,轻轻抚了抚他的脑袋,温婉与他说道:“等你养好了身子,我们就把这门亲事办了。”说完望他轻轻一笑。这一笑,不冷不艳,似和风拂面一般令人舒坦,倒是让虎的慌张神色褪去不少,只是他依旧那副怂样,又给呆在了那里。又听寒鸦唤了一声:“可以进来了。”话音方落,便见獾带着两名男子踏着那条石梯走了下来。“把他带到房间去,给他把伤口处理了,让他好好休养一阵。”领了寒鸦吩咐,獾领着两男子将虎从地上搀起。虎浑身无力,任由他们搀着,口里结结巴巴地嚷着:“不是……我……我……”“不是什么呀不是,我什么我?你当我愿意啊!”獾满腔怨念,极其不耐烦地打断了虎,一挥手,两男子一人扛起虎一条胳膊,架着他就往石梯上去。虎通身伤痛,弱弱挣扎两下也是白费力气,几乎是带着哭腔,张皇的连声嚷嚷:“别……别……强抢民女,不,民子,不,男子啊!强抢男子啊!”他那声音又惊又怕,全然不再见那份随时随地都能将猥琐发挥得游刃有余的潇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