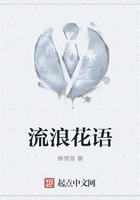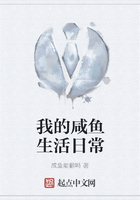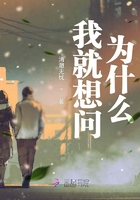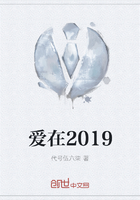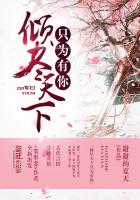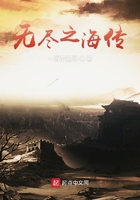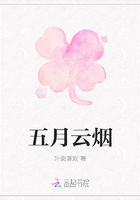21
正月十五,西陵下了场大雪,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我这年放了两挂100响的小鞭,一挂是爷爷买的,另一挂是用金爷给的压岁钱买的,一直留到十五。阿玛春节什么也没给我买,也没给家里置办什么东西,家里也没人敢问他这个“公家人”的工资都拿去做了什么,他整天早出晚归,似乎总是很忙,但到了饭点儿一定会准时出现。
我没敢象宽绰人家的孩子那样拿竹竿挑一串一千响的大鞭炮,噼里啪啦,电光火石般一气呵成,让心随着鞭炮一起在一瞬间爆炸,而是费了大劲,把小鞭一个一个从拴炮的捻子上解下来,凑成一捧,装在兜里,然后点一根香,一颗一颗地点着放,这样,放鞭炮的乐趣就比一整挂一下子炸掉地放要长久许多。
下雪那天,我揣着心爱的红鞭炮,点着一根绿色的香,走出村子一路往西。大雪覆盖了墨绿的松林,枝杈的顶部一层白,仿佛是戴了白色的帽子,环陵公路北侧靠山一边,是一座座的帝陵,后陵,妃子园寝,每一处后面都有一座小山,就是“靠山”。路上没什么人,也许乡亲们这时都猫在家里呼朋唤友,招待宾客,北方的冬天,万物萧索,是农闲季节。
从泰妃园寝过去是泰东陵,里面葬的是雍正爷的孝圣宪皇后,她是钮钴禄氏,四品典仪官凌柱之女,和我们一样也是镶黄旗。按照清朝规矩,皇后在皇帝以后薨的,不能打开皇帝的地宫打扰他,而是要为皇后另建山陵。所以在清东陵,因为慈禧老佛爷比咸丰帝多活了近半个世纪,所以也给她在葬咸丰的定陵边上单独建陵,即定东陵(定东陵还葬了东宫娘娘慈安);过了泰东陵就是雍正爷的泰陵,再往西就是雍正的孙子嘉庆帝的昌陵,再过去就是嘉庆的后陵昌西陵,里面葬的是孝和睿皇后,又一个钮钴禄氏,镶黄旗,一等侯恭阿拉之女,她从妃晋为贵妃,是嘉庆登基后他阿玛太上皇乾隆爷亲自封的,在乾隆爷驾崩后两年,再晋位皇后。她的阿玛恭阿拉就从承恩公升为一等侯。
我看着雪花款款地飘落,飘落在大殿顶上,宫墙上,殿前的青砖上,汉白玉的石桥石栏杆上,红墙上的黄瓦因有了白雪覆盖,一条一条,上白下黄,更加整齐分明,就像钢琴键,我想这宫墙的琉璃瓦如果能如琴键般奏出曲调,那一定是一曲天籁。天子听的音乐不应该是天籁么?而在这新年伊始的正月里,那些在另一个世界的皇帝,皇后,妃子们此时又会忙些啥?他们会和我一样也沉浸在过年的欣喜中?也会对新的一年充满了憧憬?也许他们已成了仙,每天都似过年般快乐自在?从来没有一个时候,象在这正月里,我感觉和这些逝者有这样一种亲密,他们此时似乎已不再是那些高高在上,可敬却不可亲而遥不可及的皇帝,皇后,皇贵妃,恰恰相反,他们不过是一些和我,我们西陵人沾亲带故的一些老祖先,如果他们在天有灵,此时看着他们凡间的子孙后代忙着迎接新的一年的来临,是否也会被我们感染呢?也许,我此时的感受,比当年内务府大臣成年累月不厌其烦地祭奠时来得更真切吧,虽然我没有什么可以拿来祭奠皇帝和他们家眷的东西。
一路向西,我高兴时就掏出一个小鞭,用香点燃,然后迅速扔向半空,听那爆竹在脱手的瞬间爆炸发出的脆响,空气里余留一缕淡淡的硫磺味,那是我洋溢的喜悦。
我一个人在空旷的田野里疾行,仿佛要奔向一个明亮的远方,过了年就是新的一年的开始,又长大了一岁吗,那会怎么样呢?
天地间有些昏暗,雪片纷纷扬扬地落下,似乎要急切地奔向大地,织成一块巨大的白布,把大地捂得严严实实,让人间陷入一片静寂。雪飘落的地方,是西陵白色的石桥,灰色的神道,红色的宫墙,黄色,绿色的琉璃瓦,那一座座寝宫里长眠的人们,在这漫天飞雪的日子,似乎睡得更香,更无需被人间的事烦扰。如果死亡的静谧属于另一个世界,那么这雪天的安宁也属于另一个世界。
我大踏步地,一口气走出十里地,就到了西陵最西边的那座陵,道光帝的慕陵。这里离东边几个陵都很远,再往西就没有其他的陵寝,所以格外安静。最初,按照雍正帝规定的昭穆之序,阿玛葬西陵,他儿子葬东陵,他孙子再葬到西陵,是穿插着来。道光的阿玛是嘉庆,葬在西陵,按说他自己该在北京东边河北遵化的东陵,结果东陵的地宫修好后,道光爷亲自前往检视,发现靴子底湿了,怀疑地宫漏水,结果一来二去,发现工程出现疏漏和贪污,结果修陵不力的官员罚俸的罚俸,削籍的削籍,发配的发配,数十万工匠,百万夫役,花了七年,二百万两银子盖的那座宫殿就地拆除,然后道光也不顾曾祖父雍正定的规矩,又到北京西南的易县,西陵地界儿重新找了一块万年吉地,又花了二百多万银子盖了一座新的陵寝,是为慕陵。
但在西陵,关于道光帝最早发现地宫渗水,不时因为他打猎路过那里顺便检视发现的,而是他先故去的孝穆成皇后(还是镶黄旗的钮钴禄氏)半夜给他托梦,梦中皇后在一个大海里呼救,好像要溺水了,道光爷醒后十分不快,随继发现东陵的地宫渗水。
数九寒天,我却走得浑身大汗,到了慕陵,发现兜里的鞭炮已被我一路放光了,香也只剩下奄奄一息的一小截。我走过神道,发现宫殿的大门(祾恩门)是开的,进去就是棱恩殿,(再往后,就是一个巨大的圆坟头,这是慕陵和所有清代帝王陵不一样的地方,其他的帝王陵都要盖宝城,就是用砖围出一座小山包,宝城顶上盖一个明楼,明楼里有一只大赑屃,上面驼一块碑,碑的两面分别用满汉语记述了皇帝生前的功德)。
我走上月台,跨过宫门,走到祾恩殿院里,这里空无一人,没有游客会在这个时节跑到这里观光,看门的人此时也不知躲到哪里取暖了,只留下一座空荡静寂的院子,坐北朝南的是一座单檐歇山式金丝楠木殿,东西配殿也是金丝楠木,虽然门窗不涂任何色彩,只是木头深褐色的本色,但却有一种古朴厚重之感。这座祾恩殿全部用金丝楠木,为找楠木料,修建时差点拆了北京的几座殿,造价之高,用料之奢,可谓国内古建之孤品,慕陵的造价超过了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定东陵,可称清东西两陵之最。
大雪已把院子的每个角落用白色覆盖,仔细听,我似乎能听到雪花落下的声音,如果真有这声音,那应该是这天地间唯一的声音,我忽然想起爷爷跟我讲过老子《道德经》里的那段话,大音希声,此时我似乎有点明白这希声的大音大概是什么样的。爷爷还给我说过这话的前面几句:“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白若辱,此时我也似乎明白了,就是最白最高洁的东西,往往会被忽视,甚至会象脏东西被人嫌弃。只不过,我此时看着这面前的洁白的雪景,心里十分开心,只是怕有一点杂色打破它的统一和谐。我大概是在很久以后,才明白雪下来时才是最美,然后就会慢慢变脏,再后来慢慢化掉。世间有一种风景,设在那里就是被人用来砸碎的,无论它是如何的巧夺天工或鬼斧神工。比如东陵西陵那些皇帝后妃的陵,盖起来就是让人挖开盗的。也是在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些《道德经里》的话,其实是爷爷在说给他自己。但那个正月十五,我还没上学,不识字,不太清楚这些话的意思,也不知他为什么会时常念叨这些。
但我隐约地知道,爷爷的字“慕远”,似乎是和这慕陵的“慕”有些关系。按规矩,皇帝陵要由他即位的新皇帝来定,可是道光帝就在慕陵竣工,他先逝的两位皇后从东陵移来时祭酒,并在大殿月台上写了几句话:“奉朱笔,敬瞻东北,永慕无穷,云山密迩,其慕与慕也。”随后,唤年仅四岁的四子奕詝和六子奕?过来教读朱谕,然后藏于殿内东暖阁。道光三十年,道光爷薨,奕詝即位(就是咸丰帝,慈禧的丈夫),他重读遗训,思念前番,心领神会,在道光帝去世后的第一个月下旨“所有龙泉峪陵名,应敬称慕陵”。
关于道光帝最显赫的正史,我是上学后才知道,就是他因为拒绝和英国人贸易,打了鸦片战争,结果打输了,割让了香港。总之是一件耻辱的事。但是如果道光爷知道大清是个体制落后,技术落后的独裁国家,除了欺负自己的百姓,本没有和红毛英吉利对抗的本钱,也许他会同意和英国人贸易,贸易本来是平等的,利国利民,可惜道光爷不这么想,他把英国人当成蛮夷,根本不屑得搭理他们,视其为无物,也屡次拒绝英国来谈贸易的使团,在他眼里,大清是天朝大国,世界中心,可惜他认为的东西都是假的,大清原来是那么不堪一击的银样镴枪头。而且,按照祖制,有失国之尺地寸土者,的皇帝是不能在自己的陵里置记载功德的圣德神功碑的,所以大清自道光后,所有帝陵都再无此碑,大清的败相,大概也是从道光那时一步步显现出来的。
可是虽然道光爷有点心虚,但还是要和自己的祖先扯上关系,所以才有,“敬瞻东北,永慕无穷”这一句,因为他父亲嘉庆帝的昌陵,曾祖雍正帝的泰陵都在慕陵之东北,那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不是一个太值得称道的皇帝,但我有一颗敬我祖先及其丰功伟业的心。那么,有了这样的心,我也还算是有理想有抱负。“只是,我觉得这更象是一个平庸的人为自己找的一个慰藉,似乎”有理想“这件事就可以把”平庸“这件事掩盖了。
但我不知道爷爷的字“慕远“的远,是指的哪里?那是一个地方?一个状态?一种境界?他就是这么小小翼翼地艰难地活着,却似乎又不愿意就这样活着。他是一座桥,一座连接当下与未来的桥;他也是一份默默的独白,里面都是关于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阐述。
我站在慕陵前殿空寂的院中,一片片悠悠的雪花落在那曾经站立过道光皇帝和他两个儿子的月台上。我的兴奋劲渐渐褪去,忽然有些茫然。
世间总是有一个叫“命“或”命运“的东西,谁也不能改变,包括皇帝。西陵的“五鬼闹慕陵”,说的就是这件事。话说道光帝来西陵祭祖后,骑着马,带着一名涿州的御风鉴(风水先生)祖先生,还有大臣,侍卫,护陵王爷,由泰宁镇总兵保驾,从泰陵北山起上云蒙山,先看西北的来龙,后望东南的去脉。西北的来龙气势很壮,从大同的浑源的恒山向东南,伸向广昌,广灵的飞狐口,向东直达云蒙山,百里山峰,形成天然屏障,可作为靠背。道光帝很满意,随即将这北边的“穷独山”改名为“泰宁山”。然后来到华盖山,东华盖山为辅,西华盖山为弼,东西相抱,耐藏风聚气之所,远处有两座小山一座向西低头,一座向西北低头,象征一文一武躬身朝拜,道光帝甚是满意,祖先生也大加赞赏一番,而后又进言道:“这里山行布局虽好,就是有一点,西华盖山东南角有两块巨石,似是一僧一尼,据卑臣所观,僧尼对立,恐怕犯五鬼。万岁不可不虑。”道光帝摆摆手说:“朕乃真龙天子,福大命大造化大,一正压百邪,一福压百祸,慢说是五鬼,就是七鬼八鬼的,又有什么可怕的呢。”结果,到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中以法国人为首的德,意,日,英五国,在占领北京后,一路杀到西陵,把慕陵礼部祭祀用的金盘银碗等皇家御用物件一抢而光,导致后来几年再给道光帝祭祀,只能用一部分木制的器皿。应了慕陵犯五鬼的先兆。其实关于命这个事,我的理解是,如果道光不讨厌洋人,可能还不算悲剧。只是他是最不喜欢洋鬼子,生前英国人几次派使团想从广州登陆拜访地方大员,谈判通商事宜,道光帝就是“三不”:“不见,不理,不谈。”到最后,清政府采用对使臣驻地断水包围的野蛮方式,逼迫英国使臣离开。不理睬洋人,并没能阻挡洋人用枪炮来打通贸易,而且,在他死后仅仅五十年(道光三十年是1850年),洋鬼子(还不止一国)就直接闯到到他长眠的“万年吉地”来“见”他,还抢了他御用的东西(如果把坟扒了就更是耻辱),这是大清的命,也是道光帝的命,所谓“性格即命运。”他如果不是那么刚愎自用,封闭狭隘,他的大清可能就走上了和英国一样的君主立宪国家的道路,与西方发达文明国家为伍,不会有庚子之乱,也不会有大清完蛋后的百年动荡与生灵涂炭。不过皇帝的性格决定国家的命运,也是专制制度之一大特点,黎民百姓本不姓爱新觉罗,也就是猪狗不如地苟活,任皇帝一人为所欲为,主宰自己的生死。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说的就是这生出了两千多年专制君权的一块天地。而《道德经》里说的刍狗,就是我们西陵人说的“乌叉”,那些用来祭祀的牲口,没错,普天之下,祭活人的和祭死人的人和牲口,都是“乌叉”或刍狗。有一些人,叫做“庙堂”,比如爱新觉罗们的先皇故人,身前身后都是被供奉着,而大多数人,生下来就是刍狗,是当“乌叉”的,大清就是这样一个国。
祾恩门后的院里,正殿边西边放着一个石雕的大香炉,雪花盖在白色的石头上,浑然一体。此时只有前殿院里的我,和后寝大坟头下躺着的一个死去了一百三十年的皇帝,阴阳相隔,却咫尺之遥,这真是一件奇异的事,就好像一个第一次生孩子的母亲看自己的孩子,只不过和我面对的是个叫“皇帝”的逝者,而我们家祖先,是祖辈儿给他守陵祭奠的,虽然我没受过什么“皇恩”(到我爷爷那辈儿就民国了),但我似乎应该是和这个死去很久的皇帝能扯上一点点关系(就象每一个西陵内务府和八旗的后代),就象任何一个农村的孩子,想到家乡第一个会想到村里的一棵老树或一条河流,或者一个大城市,比如北京的孩子,想到家乡的或许是天安门或者他住的那条胡同,而我的家乡,就是遍布了大大小小宫殿般的帝后陵寝,我的祖先们全部的工作,就是拿着朝廷的俸禄,象伺候活人一样定期给这些死去的人做东西吃,定期跟他们诉说后人们绵绵不绝的思念,因为:“国之大事,在戎与祈年”,因为“事死如事生”。这在今天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人世间大约没有这样长久的陪伴,可是长相思守,对我们西陵人来说却是几辈子的事儿,虽然陪伴的对象有些奇怪:死人,皇帝(两个都对)。我在懂事时其实就知道我的祖先,虽然也是尊贵的内务府,却是陪在死皇帝身边,而不是象北京那些“真正”的内务府大员,是伺候活皇帝的贵族,就象西陵每一座陵,还不如紫禁城的一个小院子大,但却是缩微版的紫禁城,然后再有模有样地把活皇帝那套班子,比如内务府,礼部,工部,护营按比例缩小后搬过来,这对我来说,似乎更像是一个“过家家”的游戏,至少清朝的国家的决策是从住在紫禁城的皇帝下达的,而不是来自睡在西陵的皇帝。可是我们的祖先,从雍正到光绪,大半个清朝,都是在这“过家家”中过日子,这是他们存在的全部意义。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存在。一个把仪式当做生活,或生活的主要时间都是在仪式中度过的,不管他们曾经多么锦衣玉食,悠哉游哉,都不能不让第一次接触西陵陵户的人觉得奇怪,而我,就是来自这么一个奇怪的家庭,一个陪伴逝皇帝,天天面对死亡,(无论那个死亡是多么高贵,神圣)的家庭。我的家庭的意义,也是逝皇帝给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过去,或说,我们的历史就是虚无,我们在别人,皇族成员生命终结后而开始了自己生活的意义。当然还是那个道理,这个逻辑之所以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或过去的主子)认为死人应象活人一样被对待。除了我们西陵(和东陵)旗人,还有没有一种人生,是要由死人来赋予意义?而这个奇怪的问题的结点,还不是因为那些死了的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整个大清都是皇帝的,安置几千个旗人在他死后给他看坟算多大的事儿?他死后,如同他活着时一样,要证明他其实还存在于世。除了皇帝,一般人不会这样处心积虑大费周折地在死后还要享受生前的排场,还要怕让人给忘了。可是连我一个几岁的孩子都能区分生死,那些皇帝们难道不知道死而不能复生吗?如果不能复生,为什么不象普通人家那样埋了完了,还成天让人做好吃的好喝的歌功颂德地干啥?
这些问题,并非不是一个孩子无法想到的,至少在那年正月十五,在飘着雪花的道光皇帝的坟地里,我开始有了这些问题。
好在这些离经叛道的问题只是一闪而过。我只是一个学龄前爱玩的孩子。我的注意力又被大殿一侧的石头香炉吸引了,“既然跑了这么远过来,总要做点什么”,我琢磨着,况且皇帝毕竟还是上三旗旗人的旗主。我把石香炉上的积雪揉成块儿,把手里剩下的那一小截香插到香炉的雪块上,想了想,觉得除了再背一段岁末的祝文献给这位相信“一正压百邪,一福压百祸”的可笑的皇帝,真的也没其他游戏可以玩儿,何况这次没有其他孩子,只有我一个人,就当是自娱自乐吧。
西陵再没有赞礼朗,读祝官,承祭官,和陪祭执事至少每月两小祭,每年四大祭地去缅怀这些先人,这些皇帝,也再也没像我的老祖那样的官员在白色的素帛上写祝文,但我就阴差阳错地降生在这里,就歪打乱撞地学会了一些古老的礼仪,这一切,也许是巧合,也许也不是,也许是荒唐的,或许也不是,就象生命中(包括皇帝的生命中)发生的所有的事。不过既然我来了,就当是哄一个孩子(皇帝,那些所有有权势的人,都需要哄,只不过如果你相信皇帝们死后有知,那也可以哄死皇帝,就象我们的先人那样,给他们做吃的,说我们想他们,因为他们的离世而有多么悲痛,翻来覆去)。我又想起一段当年西陵内务府岁末祭拜的祝文,于是在对着祾恩殿的门,俯首小声念出来,好像怕别人听见:“节近履端,因时饯岁,敬陈柏酒,鉴此芯芬,伏惟尚飧。”这段祝文,一般是皇帝的后人,也就是后来的皇帝来时念的,不过此时只好由我念出来了。
念完,我绕到祾恩殿后,那里有几级石台阶,台阶上面是到后寝的一个三联的石牌坊门,进去就是个硕大无比(直径估计有二十米)的砖砌的坟头,坟头上面是黄色的琉璃瓦,我没有进这个院子,在门口驻足了一下就走了。
23
出得慕陵,似乎已近黄昏,忽然一群绵羊,大概只有十几只,匆匆地从陵前的广场走过,羊蹄子踩在雪上发出沙沙的声音。那个年代农村刚实行责任制,家里养羊,不仅要有魄力胆识,还得有买羔子的钱。这些人就找个羊倌,让他统一放羊,早上出村,穿过松林和陵区,一直向北面,西陵的的靠山云蒙山,羊到山脚下一路走一路吃,晚上羊倌再把羊赶回村,羊会认得自家的院子。羊的主人,按头数一年跟羊倌结一次钱,那会儿大约干一年,就是城里一个公务员一个多月的工资,几十块钱吧,但比普通种地的收入要高一些。
羊过去,后面跟着羊倌,他手里拿了根棍子,棍子头上栓了个胶皮条,做成根鞭,他头上戴了顶破旧的棉帽,已露出里面的棉花,山上穿着一件黑不黑,蓝不蓝的旧棉袄,扣子都不是同一个颜色,上面全是土和泥,脚上是一双肥大的黑色棉窝子,腰里系了个红色的布条,是全身唯一闪亮的颜色。我认出了羊倌,他是我们村的唐叔叔,大概三十来岁,可有点显老,也许每天都要风吹日晒地赶羊,看上去象近五十岁的老汉。唐叔老姓塔塔拉氏,那是满族最老的姓,他祖上和内务府旗人不一样,是京畿调到西陵的护军(西陵旗人主要是内务府和京畿调遣的八旗两类)。
我见到唐叔,依然按老礼儿,赶紧站住,双手下垂,喊一句“唐叔好”,唐叔抬头看看我,有点迷茫,随后认出了我,说一句:“翅飞出来玩啦。”就没再说话,继续去追赶他的羊。
不知怎的,每次在路上见到他,我心里会有点惋惜或难过,因为大家都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他,或谈论他,而我的阿玛,就直接用最恶毒的叫法,背地里管他叫“活死人。”这一切,源于他七十年代,在我出生前,他二十多岁时的一次可怕的经历。
那大概是夏末的一天,年轻的唐叔去云蒙山里砍柴,结果一下失踪了,整整三天三夜,村里发动了几乎所有人去找他,甚至惊动了镇民兵部(也就是我阿妈复原后任职的那个地儿)和镇派出所,连警察们都被派出去搜寻,大约是在第三天的傍晚,唐叔在自家的院子里被发现,似乎刚刚醒来,他和所有的人说他是早上出去,只进山转了大半天,却根本不知自己已消失了三天,也无法说清自己怎么会在自己家院子里醒来。
然后他讲的经过就有些可怕:他在进山时碰到一个年轻的村姑,还挺水灵,村姑告诉她自己姓“胡”,叫“胡艳丽”,说自己就住在山里,请他去她家坐坐,唐叔还觉得纳闷“这方圆几十里的大山,怎么会有人家,即使有,自己时常来山里打柴,怎么没见过呢?”但姑娘就是盛情邀请,他只好跟她去了,结果真的就到了一个小茅屋前,进得屋来,姑娘给他端茶送水,还拿了烟请他抽,最后送他出门时,还让他把烟带走。
唐叔和所有人(包括派出所警察)说这段经历,为证明自己所言非虚,说:“她给的我香烟都带回来了”说着就去上衣兜里掏,结果连他自己都傻眼了,他掏出的是一把整整齐齐的秫秸杆,切成与香烟大小粗细相仿。这下所有人都惊了,大家纷纷议论,唐叔是碰到狐仙了(就是四大门的黄爷),它说它自己姓“胡“,又是个妙龄女子,那不就是一个修道的狐狸精吗?再后来,唐叔带村民去山上找那座草屋,结果可想而知,那个屋子根本就不存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就是唐叔认为他是当天来回的,可他已消失了三天,所谓”山中一日,世上千年“。
这件事大约是七十年代忠义村发生的最离奇和轰动的事,一直到现在,去忠义村问这事,村里的人都知道,我小时后就知道。唐叔“一举成名”,大家看唐叔,仿佛觉得他遭遇了某种不幸(不过大白天见鬼还是一件恐怖的事)或是身体有了什么残疾,对他都象对异类一样,又有一些怜悯。
我小时在对这事好奇的同时,却不知道为什么阿玛要用“活死人“去形容唐叔,他只不过是遇上了狐仙,又没有被附体,事发后人也是好好的,为什么要背后这么称呼他?更何况出事时阿玛还在部队上,他也是后来才听人说的。本来大家都是一个村的,难道只是因为一个念过大学,当了农村小干部,另一个是个放羊的?不过也许就是这样,在阿玛眼里,西陵这些老乡不过就是些农民,一些没啥本事土了吧唧的农民。我也是在以后,把上辈子欠下的打骂都受了以后,才慢慢明白:其实暴力不仅是肢体或语言的,它也可以是精神上的,那就是蔑视。皇帝蔑视臣子,当官的蔑视人民,有钱的蔑视工薪阶层,当爹的蔑视孩子,都是暴力,这种暴力,在一定场合下就会变成肢体和语言的残暴:反过来,一个人决不敢打骂自己敬畏的人。
暮色已经苍茫,雪后的西天有一大片密布的彤云,在落日的余晖中变成一片暗红,深皇,青紫。往村里走的路上,关爷不知又从哪儿冒出来,嘴里哼着京韵大鼓“金乌西去坠远山,玉兔东升上雕栏,万籁无声人寂静,野鸟归林巢内眠。我不言宋江坐楼杀了阎氏,再表那婆惜显魂活捉那小张三…”,仔细一听,是“活捉张三郎“里的词,这是一出鬼戏,讲的是被宋江杀了的阎惜姣,死后芳魂不散,朝思暮想情人张文远,趁夜色去访张三郎,二人回味当初甜蜜情景至鸡鸣天亮,张文远被女鬼吸引,魂飞魄散,和阎婆惜共赴黄泉。
我不清楚正月的这个大雪的傍晚,关爷在这僻静空旷的山野里晃悠什么,象一个飘来飘去的我不知如何形容的东西。自从上次我和一群孩子演练祭陵时撞见他,被他喝彩,似乎已很久没碰到他了。但我还是礼貌地问他好:“关爷您好,您新年吉祥。”关爷听到,马上高兴起来:“哎呦哎呦,翅飞啊,你上回那些词儿可说得够溜的,嘴皮子快,脑子也快。先皇他们听了肯定喜欢。”我正纳闷他怎么又扯这些古怪的话,他接着说:“我这儿可也有不少的歌词儿,我看你口齿伶俐,哪天找我,我也教你几句。”我愣住了,我没想过要学什么歌词,老一辈满族人唱的八角鼓,大鼓的词儿对我一个孩子似乎太遥远,我就问他:“您说的是鼓词吗?”他看着我,诡秘地一笑,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不过,”他顿了下:“你可得小心点,别冒犯了大人,要不有你吃瓜涝的(惹麻烦)。”我想这关爷怎么总这么神经兮兮,我对长辈一向是尊重的,怎么会冒犯谁呢?”关爷没有再说,继续哼着他那出鬼戏:“天堂地狱两般虚,要在人的行为是非曲直;凡事离不开因果二字,总有那讲今比古说书唱戏…”一转眼,就消失在林海深处。
24
到了清明,天就一天天暖和起来,杏花也一树一树地开了,还没到犁地撒种的时候(那是要到五一节后),村里的大人小孩们开始准备各种玩艺儿:大人抓鸟,小孩儿放风筝。爱玩,会玩,让日子过得有意思才是最重要,天天为了一口嚼谷(吃的)奔命,那不是旗人的活法:这一点西陵和北京的旗人几乎是一样一样的,从大清到民国一直到现在。其实,这“玩儿”也许才是陵户们真正身心投入,乐此不疲的事情,往大了说,玩儿出个花式儿,那是一种境界,是一种格局,虽然都是农民,但旗人骨子里还留着锦衣玉食,阳春白雪的贵族遗风,和后来搬到陵区的汉族佃户为了每年打那几斗米没日没夜地忙活是不一样的。
说起这风筝,光绪爷在世时有工匠专门为宫里做风筝,每月到了时候这些工匠就能领到内务府发的“老米“,那是一种做熟后有一股焦香的米。宫里收了这些风筝,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玩儿,如果皇上年前把风筝赏给某位大臣,就预示着他来年春风得意,平步青云。
天气晴朗的日子,各个陵前的空地上就会飘起几只五彩斑斓的风筝,那些风筝都是按照老习惯,是在腊月里大人农闲在家没事儿时给孩子们做的,到了清明寒食,孩子们就拿出来放,叫“放晦气”。那些风筝,在孩子们牵线奔跑中一下就腾空而起,有大金鱼形的红风筝,还有正十字形的孙悟空,当然最多的就是沙燕儿。这些风筝很快升高,没过一会就由大变小,成了悬在遥远的天际的一个小斑点。
我喜欢看这些漂亮的风筝在天上凝住的样子,它们怎么会飞得那么高?好像比云蒙山还要高,如果有一个人趴在风筝上看这地面上的人间,他看到的会是怎样一片景象?是不是和我看风筝一样小?
我又想到我自己,我的未来,似乎我应该是和这风筝能扯上一点关系,因为我的名字叫翅飞。据说爷爷当年和阿玛商量要给我起这个名字,想到的也是会飞的,就是满族的神鸟海东青(康熙爷当年曾有诗云:“羽虫三百有六十,神俊最数海东青。”)这是一种猎鹰,百鸟之王,飞得高,看得远,满族人在关外时就有养海冬青的传统。入关后,紫禁城里内务府有专门为皇帝饲养海东青的鹰户,住在北京怀柔和承德接壤的山里,除了每年要向皇帝进献海东青,还要让训熟的海东青去抓野鸡,每年有定额献到宫里。不过关于未来这件事,我了解甚少,也不知道自己长大后会做什么,想做什么。春天的时候,最重要的事还是能放一回风筝。
爷爷虽说懂书画,做风筝还真有点难为他,主要是风筝的骨架,弯曲折成形状是要拿烛火慢烤,烤软了再用线扎紧固定,这些都是费眼费手的活计,爷爷年纪大了不说,他过去放的风筝,也都是人家送的或买的,自己不做。但爷爷不愿看着我每天眼巴巴地看村里别的孩子放风筝,就给我糊了一个正方型的“屁帘儿“,因为方形只要四根竹条围边,中间再用两根竹条,象画叉一样交叉,蒙上纸就好了,不需要加热竹条折弯,所以做起来会容易许多。
风筝做好那天,我别提有多高兴了。一手拉着爷爷,一手举着风筝,就跑到村外的泰妃园寝的广场上。爷爷迎风帮我举着风筝,我拉着线开始跑,爷爷松手后,风筝摇摇晃晃扑腾了几下,就掉地上了。再试,还是这样,连续几次,都飞不起来。爷爷拿着我捡起的风筝,仔细看了看,说:“线不行啊。”因为风筝线要解释,还不能太重,重了风筝就起不来,我们因为没有尼龙线,用的是一种很粗的棉线保证结实,但结果就是太重风筝飞不起不来。期待变成失望似乎没有用多少时间,我暗想:”放晦气的时候却放不走,这难道是有什么不好的事儿要发生吗?”我没敢把这个念头告诉爷爷,怕他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