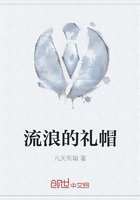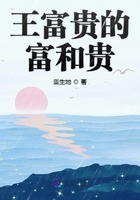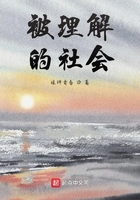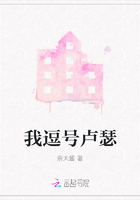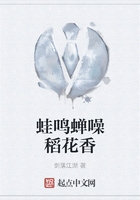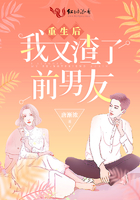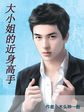鹿尾儿
1.
两岁多那年,我跟着爷爷从田头走过。我就对爷说:“爷爷,我长着长着就不长了”。爷爷有点严肃却又亲切地说:“那怎么行,你得长大,长大了去看世界”。
那不就是世界么?好大的一片红墙黄瓦,雕梁画柱,我指指那片金碧辉煌的宫殿,似乎很热闹的。爷爷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轻轻吐了一句:“那是另一个世界,是他们死后去的地方”。
我不太明白什么样的人能够住在这样气派的,比我们村里的小灰瓦房气派的多的地方,当然我更不知道死是什么东西。“什么是死?”我有点懵懂,爷爷想了想,答道:“就是你要一个人,去另一个世界。”“那和长大有什么区别呢?长大不也是去看世界么?也要一个人么?”爷爷轻叹了口气,说:“长大你就明白了”。
爷爷带我走过的田头是个不高的坡,周围苍松密布,都是上百年的老树,我长大后才知道这里是华北最大的松林。就在这一大片松林中,有一小块田,是我们家的,在我记事起就种些玉米,山药,勉强够一家人的口粮。松树漫山遍野,一望无边,密不透风,真正的林海,而我们穿行在这人迹罕至的幽林中,就像几条在大海的珊瑚丛中游水的小鱼。
透过松树向坡下看,有一片宽阔的广场,广场上是一片气派堂皇的亭台楼阁,红墙黄瓦,飞檐走兽,虽然气势磅礴,却有些孤单,因为它们周围并没有其他的建筑,没有街道,甚至没有行人,如果不穿过这片茫茫林海,外人谁也不会发现这里有这一片外形像极了北京故宫的古建筑群。它们工整,肃穆,透着一丝不容侵犯的威严,让人敬而远之,不敢走近。
但是对儿时的我,那梁柱上的彩绘,那石栏上的雕龙,还有屋顶的琉璃的飞禽走兽,却是新奇不已,百看不厌。我上小学前,已能一个人跑到这个离村百米之遥的广场上玩耍,那里永远空无一人,万籁俱寂,只能听到松涛阵阵,和气流划过遥远的天上的鹞子的翅膀时的声音。它们也许是守护着下面这一大片宫殿,也许是盯上了林间跳动的兔子。
宫殿的后面,远处,是一片连绵的大山,一年四季都是深青色,它们同样沉默,肃穆,威严。
在这太行山的东麓,易水河畔,一条弯弯曲曲的环陵路,连接起了十几座帝陵,后陵,妃子墓,阿哥墓,路和官道接上,穿过易县,涞水,到了北京西南的高碑店,然后就是北京,统共不过260里。清朝那会儿,每月到了时候,朝廷的钱粮车,装着银子,插着黄色的龙旗,就从北京出发,几天后到达西陵,给驻扎在这里的东西王爷府,内务府衙门,承办事务衙门,关防衙门,礼部衙门,工部衙门,兵部衙门的两三千旗人送来他们的晌银,收这些银子,是朝廷从北京,关外,精挑细选派来守皇陵的旗人的特权,世世代代,旗人管这雷打不动的收入叫“铁杆庄稼老米树”。
这里是西陵,葬了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和宣统位清朝的5皇帝,9位皇后、57位妃嫔、2位王爷、2位公主、6位阿哥,共计80人。我们家,就是祖辈侍奉这些皇帝的陵户中的一户,我们村对面,和村墙只有一墙之隔的,就是泰妃陵,我们侍奉的,是雍正帝在那里面长眠的21个妃子。
2.
我爷爷姓章,老姓章佳,名文思,字“慕远”,是镶黄旗在旗的,雍正爷(和后来的皇帝)不光是皇帝,也是我们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的旗主,一般只有这三个旗的人,才能在内务府当官,因为这一层,比一般的官员都要跟皇帝亲,是真正的龙族。
那时爷爷还活着,听他说我们住的那个村,叫“妃衙门”的,是这片山谷里最早的村子。比最早搬来这里的雍正爷还要早。当然,最早这里是内务府营房。内务府,就是皇帝家的管事儿机构,皇帝家的人的婚丧嫁娶生孩子,过年过节给皇后妃子的给赏等事,都由内务府掌管。因为葬的是妃子,所以不能叫“陵”,只能叫“福地”或“衙门”。叫衙门还有另一个意思,乾隆皇帝生母孝圣宪皇后的陵寝(泰东陵)修建时,内务府营房、八旗营房、工部营房和礼部营房同时动工修建。但是,修建官员为了中饱私囊,在此四处工程当中,偷工减料。如内务府营房规格不整齐,东、南、西三面围墙整齐,北面围墙则凸凹不平。同时将八旗营房和礼部营房、工部营房修建在一起并且缩小规制,且不平整。泰东陵马槽沟更是明显地偷工减料。这些事情被清廷知道后,乾隆皇帝派孝圣宪皇后的义子刘墉前来西陵审理,刘墉对偷工减料之事非常气愤,于当天半夜三点在泰妃园寝内务府营房(就是妃衙门)设立公堂,审理此案。审查结果是开除了百余名有关官员。
我们村内务府,礼部,八旗兵的房子全是当年朝廷拨专款修建,规制相似,只是大小有别,象我们家因是官员,按规矩正好分到一套占地一亩三分的一个院子。院门朝西,正房也朝西,所有人睡觉都头朝西,因为雍正爷的泰陵在妃衙门西边,西向尊贵,也表示守陵人对他的遵重,这是朝廷定的规矩。
院子坐东朝西,走进我们家院子东门,院子中央原来有一根下粗上细的的四五米高的棍子,这是索罗杆子。表示满族人对老天的敬畏,从关外带来的习俗。早些时候每家每户院子里,哪怕在故宫的内殿,院子里都立索罗杆子,又叫“祖宗杆”,传说是老杆王(努尔哈赤)上山打猎用的索拔棍,立这杆子是用来祭天的。
正房北墙,按旗人的老礼儿,供祖宗牌位,就是刻有章佳氏的先人名字的一块木板。牌位旁,是一幅山水写意画,左右贴两幅对联,靠里的那副写的是:“世间好事忠和孝,天下良图读与耕。”靠外的那副写的是:“放怀天地外,寄情山水中”。这两幅对子,都是我笔帖式的老祖(爷爷的阿玛)亲手写就,也是我爷爷最新欢的。而那张山水写意,据说是帝师(溥仪的老师)梁鼎芬来西陵为光绪爷的崇陵植树那会儿画成,然后亲自送给我老祖的。山水画其实包含了“西陵八景”里的四景,分别是:1 易水寒流(易水就是当年荆轲离开太子丹去刺秦王的地方,在西陵正南十里,而《二十四孝图》中王祥卧鱼的故事也发生在易水河,民间传说因荆轲刺秦王视死如归,对燕太子的一片侠肝义胆,和王祥卧冰求鱼以养母的孝心感天动地,所以易水河至今四季常流,严寒时也不冻冰,2云濛叠翠(因陵寝西边十五里地的云濛山,山下有宝塔两座,山峰高耸直刺青天,悬崖峭壁,层层翠绿而得名),3华盖烟岚(说的是泰陵东南的华盖山,4奇峰夕照(因于泰陵北十里的影壁山,每当红日西斜,傍于峰巅,迸射金光万道。所谓“高峰插云,环山拱塞,春秋晚霁,落日段然”。
当年我老祖,我爷爷进到北房,看到或面对这幅山水,就仿佛一个指挥员站在一幅详细的军事地图前:图上,西陵周边的山山水水,一目了然,那是把他整个的世界和那世界的今夕,都放在墙上,放在了心里。说它是地图,还是因为图上的山水构成了这世界的中心与边缘,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山与水在哪里连接,又在哪里分开,一切都是清清楚楚,让人了然于胸。屋里装裱了这幅大写意的山水,就如同行进的车上装了GPS和坐标尺,而决不会迷失方向。
除了画卷的内容,画的作者也给我的长辈一种非常踏实的感觉,哪怕是在最动荡的年月,只要看到这画,想起画家,他们就会暗暗地生起信心与希望。这是因为梁鼎芬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除了和皇室这一层亲密的关系暗示了我们内务府的地位,还是因为梁师傅是个忠臣。光绪驾崩,陵墓迟迟未能修建,及至民国,终于辗转开工,最后却没钱在宝顶(即坟头)植树(按规矩,皇帝的陵四周和宝顶上都要漫植松树),梁师傅自己买了许多瓷瓶,在冬天下雪时搜集了光绪帝宝顶上的积雪,来往于崇陵和北京之间,带上盛有雪水的陶瓷酒瓶,挨家挨户敲门,到大清亲贵和遗老家去拜访,以一瓶雪水为礼,请各亲贵大臣们为崇陵栽树募捐。如果给的钱和其身份相称,就含笑而别,否则就是一顿数落,直到给够为止。冬去春来,梁师傅和礼部官员选定吉日,将凑钱买来的白皮松,一棵一棵,在崇陵栽植,明楼祭台左右的十八棵罗汉松是他特意种的,寓意十八罗汉守护先帝。他种树时一丝不苟,头戴管帽,脚登官靴,几乎和在正式场合无异,三年下来一个人共植松十万余棵。光绪爷梓宫下葬那天,他护送棺椁下了地宫,最后瘫坐于棺床旁,想永伴先帝,被随行大臣强行拉起。民国八年,梁师傅去世,终于葬在崇陵前百米的地方,守护先帝,遂了他生前之愿。我老祖就是梁师傅给先帝光绪陵寝植树时认识得他,并因钦佩他的为人,请他为我家画了这幅山水。这段事儿,爷爷时常和我提起,最后不忘总结:“梁大人,忠臣呐。”忠孝廉耻四字,在我们家,从来不只是停在书里。
北房,按旗人规矩,是四大门儿的画像,供四大门,就是供狐仙,黄鼠狼,蛇,刺猬。我们叫狐爷,黄爷,长爷和白老太太。长爷(蛇)画像是一个老头。不知因为这里是先皇和先皇后长眠的地方还是因为风水的缘故,四大门在西陵一样不少,也很灵。一旦四大门显灵,现在就叫灵异事件,西陵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些事也影响了一些人的命运,只不过西陵除了这四大门,还出现过别的东西,缠绕了我半生。
我爷爷曾开玩笑地对我说:“要是在大清,你生下来就是八品。”爷爷的阿玛,也就是我的老祖,是笔贴士,正八品。这个这官放到地方,能算个副县长,在西陵给皇帝办事的官里,就不高了。当年在西陵办事的人位置最高的,当属涛贝勒,光绪爷的弟弟载涛,后来大清没了,50年代,涛贝勒,因是旗人,又留洋学过骑兵,马骑的好,一番辗转,就给八路当了马政顾问,那是后话。笔贴式这个词儿是满语,是顺治帝入关时带过来的,满语是“有学问的人”。爷爷的阿玛讲了一口纯正的满语,负责办理文件,和奏章的满汉文翻译和写祭奠祝文。光绪29年(1903年)慈禧老佛爷祭西陵,到泰妃陵,和平时驻陵内务府一月两次的小祭的祝文和记录都由他来写。
皇帝的陵,和他们活着时住的北京故宫的布局一样,都是前殿后寝,只不过没那么多间房子。而西陵各陵的内务府,也是按每个皇帝活着时设内务府,伺候皇帝起居的规制,死后各陵,各妃子府依然设内务府,不过他们要做的是祭祀,这道理和伺候活着的皇上没什么不同(守帝陵是八旗兵和绿营,这个和跟保卫活着的皇帝也是一样的)。这些个规矩,应是遵从《礼记》里“事(侍)死如事(侍)生”那条,就是说先人死了得象他活着时一样侍奉。祭祀是西陵内务府,礼部等官员最重要的工作,或存在的全部理由。这一条的出处,应是出自《左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也就是说,我爷爷的阿玛给皇帝守陵祭祀,做的就是国家最重要的事之一了。对这一点的理解,大约贯穿了我老祖的一生,也影响了我爷爷:他们从不怀疑自己做的事,自己所处的位置,那种责任,那种权威。
内务府官员一共八名,分别是:郎中,员外郎,主事,尚茶正,尚膳正,内管领,副内管领,笔贴式。从(陵寝)宫门里的大殿(隆恩殿),东西配殿到明楼(明楼下面就是皇帝的“寝宫”(或地宫,即墓穴)都归内务府管。我爷爷的阿玛,是笔贴式,八品,素金顶子。
2.
宣统逊位后,我们村改名叫“忠义村”,因为村里原有一个供奉关帝爷的庙而得名,(满族人信关公,据说是顺治入关后,康熙爷为笼络人心,说关公给他托过梦让他统治中原)爷爷的阿玛,还在村的西门,南门上题了两幅对子,西门上联是:村落新成仍是当年梓里,下联是:禾麻遍植居然今日桃源。南门上联是:近水依山无异伊颖之地,下联是:耕田鑿井同游熙皡之天。
我爷爷跟我说起这两幅对联时,总是若有所思,然后长久地不说话。
我们家开始败落,也是从他那代开始的。他生在民国三年,光绪爷的崇陵的建造开始建造那年。光绪爷生前,慈禧太后想随时废了他,就一直不给他建陵,他死后三年大清就没了,他的陵还是民国政府出钱建的,而光绪爷的灵柩就在西陵行宫停了五年,直到1913年,袁世凯才按照《优待清室条件》拨款修建崇陵,终于在当年12月13日完工。
大清没了,俸禄也没了。民国政府虽说也答应养着我们这些陵户,好让我们依然像大清时侍奉先皇,但实际发的俸越来越少,一般陵户的口粮,从十成到五成,到二成五,到一成二厘五,再然后就没了。大清律规定旗人不能经商,不能务农,因为那都是不体面的,所以我们什么也不会,所谓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民国政府在西陵划了些地给陵户,但我们不会种,只能学着汉人种,或租给汉人种,但是因为一亩打多少粮食都搞不清楚,西陵外面易县的汉人听说旗人不懂农事,都纷纷跑进来租旗人的地,收的粮多缴的租少,旗人陵户收到的粮勉强养活一家人。有些陵户实在没办法生活,就出去逃荒,再也没回来。
我爷爷那时常和懵懂的我说起这些往事。他出生时是民国三年,那时清朝虽然没了,但民国政府每年还给守在这里的陵户一点点费用接济生活。他小时念过几年私塾,识文断字,本来他的阿玛是想把他送到京师,但后来民国政府也不再管这些旧王朝留下的人,家里再没办法供他念书,他就和祖辈一样继续留在西陵,只不过从负责皇帝家族事务的官宦子弟,变成了最普通的一个农民,我们家第一代农民。
对于这件身份突然发生转变的事,我听他经常念叨的话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地里刨食儿,不丢人。”旗人好面子,重礼数,凡事都有个“讲究”,(尤其在西陵,祭祀的规矩和程序,吃饭,见人打招呼,凡事都有规矩,是一丁点儿的都不能出错。)不丢人,不给自己丢人,不给家族丢人,这是头等的大事,只是小时的我,看到的同村的乡亲,完全看不出祖上风光的贵族子弟的样子,而是最普通的农民,不明白都当了农民还有什么讲究,好像“讲究”只属于祖上的贵族。
爷爷平时下地,就穿着当年北方农民常见的那种四个兜的蓝布“干部服”,头上是蓝色的布帽子,脚上是一双胶底儿的绿色解放鞋,衣服年月久了,都洗得发白,但永远是干净齐整,一尘不染。而回到家里,饭前饭后,都要漱口,听他说过去家里都是用茉莉花茶沏的茶水漱口,漱完了嘴里还留有余香。饭前漱口,是把嘴清理干净,以表达对美食的尊敬。而他们喝的茶,好多都是从京师买的好茶,就是两个字:”讲究。“我们的院子里房前窗下,种着各种牡丹,芍药,还有月季,都是爷爷弄的,他没事就会打理那些花草,听他说,有些花儿是名贵的品种,过去只有王爷,贝勒家才种,他年轻时还养过鸽子,据说那些鸽子是他的阿玛托亲戚从北京的端郡王载漪的儿子大阿哥溥儁(就是让老佛爷立了要替代光绪爷后来又废了的那位)府偷出来的蛋孵出来的,什么满天星的铁牛鸽,全是名贵品种。
爷爷见到村里或附近村的同辈人,都会双手抱拳三作揖,那也是老辈儿的礼数。而遇到陌生人,他脸上总是挂着谦和的微笑,无论年纪大小,都称人“师傅”(“师傅”过去也不是随便叫的,皇帝的老师或有大功劳的人才能封为“太傅”或“少师”),能戴上三眼花翎,封号里带师或带傅的,整个大清也没几个人。话说请安这事儿是旗人从小在家就培养的,早上起床后,晚上睡觉前,晚辈都要到长辈屋里磕头,更不要说逢年过节的大日子了。到了我这辈,虽然早不兴磕头了,但是每天的定时问候却少不了,这是爷爷教给我的。虽然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而每天去爷爷屋里问候,他总是显得很高兴,一面也叮嘱一些注意冷暖,好好念书的话,这样的往来,其实就是老辈儿的规矩,年复一年,从来不曾间断。
3 ((打小跟爷爷下地干活,我们的地离家不远,在泰妃陵边上一片松林环绕的一个小土坡上,从那里可以看到妃陵后陵和帝陵。地不大,就种了些玉米,豆子,还开出一小块,种了些大葱。爷爷说,玉米豆子是给一家人吃的,大葱是为我种的。
爷爷扛着锄头从田间走过,我就在他后面跟着。我的任务是帮他提茶壶和茶杯,其实我背了两套,一套是个竹壳暖水瓶,装热水,外加一个军绿色旧搪瓷缸子(搪瓷的东西九十年代后就慢慢见不到了,只有在比较落后的农村才继续使用,比如我们家);另一套是一把蓝地粉彩福寿缠枝花卉纹的细瓷茶壶,听爷爷说那是官窑,嘉庆年的东西,只有内务府的官儿才能用。我们家到我爷爷,已传了六代,爷爷说那把壶等我长大了,就给我用,我那时没有想,难道论辈分,不是应该先给他的儿子,也就是我阿码用么?
爷爷看到庄稼边上的杂草,就一点点用锄刨掉,我有时帮他拔草,爷爷心疼我太小,就让我在田头坐着,我就坐在茶壶和暖瓶中间。我们家的那把壶,底色为亮蓝,确切说是深蓝里带绿,颜色非常鲜艳(那种蓝色,我是长大,进了城后才知道那叫蒂芬妮蓝(当然是洋人的叫法),才明白在十八世纪的中国,皇室和贵族就在日常器皿使用各种鲜艳的颜色。壶的正面背面都有一朵粉色的大牡丹,牡丹的花瓣,由深粉到浅粉再到白,几种颜色过度非常自然,就像真的花,和这把壶配套的,是一个同样颜色和图案的三寸长的茶杯,带盖带托的三件式。干活累了,爷爷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个手绢,小心翼翼,一层层慢慢打开,最后露出里面包的几枚残缺不齐的碎茶叶,就是当时几毛钱一斤的,最便宜的,也是我们家,我爷爷唯一能买得起的,茉莉花茶叶沫子,却有个响亮的名字:“高沫”,和我们这些旗人有某些精神上的相似。爷爷把高沫倒进那把壶,用旧暖水瓶的开水焖上,等待茶叶慢慢舒展开。然后,他又从暖壶里倒了些白水,到那个军绿的搪瓷缸里,用白水先漱了漱口,腮帮左边鼓两下,右边鼓两下,轻轻吐掉,爷爷说这样可以去掉嘴里的膻腥,更好品出茶叶原有的味道,过去他的阿玛,也就是我八品的笔贴式老祖还活着的时候,吃好吃的,喝好喝的前,都要先漱口,这是规矩,不能坏了。这时茶叶已慢慢泡开,爷爷小心地把茶叶倒进盖碗,吹了两下浮起的高沫,又左手端托,右手用盖,浅浅地由外向内,在水面上划了两下碗盖,脖子微微前倾,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啜起来,他喝茶时眯起眼,好像在微笑,又望着远方,陷入沉思,仿佛这高沫勾起了他的许多回忆。我想,这套喝茶的仪式,爷爷的阿玛,我的老祖,一定在迎来送往那些大清来西陵的各种官员过程中驾轻就熟,他也一定是这么教给爷爷的。大清亡了近一百年也许不重要,我们家只能用当年内务府造办处做的精致茶壶装几毛钱一斤的茶叶沫子也许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仪式保持下来,由一个曾经的贵族,现在的村夫保存下来。很多年后,爷爷归西,中国的一个民窑瓷器都炒到成千上万元时,我回到这片土地,我忽然想起爷爷让我把家里这么贵重的瓷器背到田间地头上来喝茶的场景,我想,爷爷那时也许不是为了喝茶,而是作一个表白,一个无声的宣告,我不清楚他那时的心里装的是什么,是失落,是惆怅,是愤怒,还是无奈?也不知道这表白,是对过去的还是当下的?是向列租列宗,还是向这面前这片长着玉米的土地,这时刻提示他的当下境遇的世界?还是向他自己?他不说,他也许不敢说,因为他生下来就知道什么叫“驱除鞑虏”,就为了保住性命,随着他内务府镶黄旗的阿玛改了汉姓,他甚至从来不曾想过离开这陵区去别处生活,虽然我们有不少北京在旗的亲戚,北京也只有二百多里之遥。他是一棵沉默的老树,就象西陵的百年古松,但是他让我看他在田间喝茶的样子,我看着端着这细腻的官窑茶杯的袖子,洗的发白布料几乎透明看不到原色,我透过这正在生长的玉米,望着它掩映的帝后寝宫的黄瓦红墙官,这世界上最尊贵的人用的窑瓷和他们死后的家园也许从来没有,至少在不到一百年前没有想过会和庄稼地及衣衫褴褛的农民为伍,没有想过这曾经禁牧禁伐禁止外人入内的皇家官山禁地,已沦为一个河北贫困县的一部份,这一切似乎如此地格格不入,又是那么自然而然。
“村落新成仍是当年梓里,禾麻遍植居然今日桃源。”爷爷轻轻地念叨起我们村西门这副对联,对联的作者就是他的亲阿玛。“翅飞,你知道这是啥意思么?”爷爷问我,我摇摇头,望着他,爷爷说:“这是老祖在告诉我们,咱们这里是个好地方,多少年都是个好地方,这是皇帝亲自选中的地方,你看有那么多皇帝都在这,咱们能在这守着,多不容易。”我听懂了,我想想,问爷爷:“您说,我和您一样,也是旗人么?”这个问题,也许对我和他都有点突然,爷爷沉默了,他端详着手里的细瓷茶杯,然后头慢慢垂下,又抬起头,望着远处,他摸了摸我的头,喃喃自语:“旗人,旗人,也许你长大了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了,不过最重要的”,他停下来,又接着说“最重要的,是要想明白,自己想活成什么样的人。”
一只花喜鹊,在老松树上喳喳地叫,一上一下,摆动它长长的尾巴,风从树梢顶端划过,发出呜呜的声音,低沉而浑厚。爷爷在这片林子里,是这土地上的主人,是他回忆的主人。虽然他的家族,我的家族,属于历史演进中失败和被淘汰的一方,但他有他的经历,和对这些经历的回忆,他因为这回忆而令人尊敬,那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他过去的生活,他知道的关于皇帝家的故事,他自己作为贵族后代的故事,那个远去的荣耀。他要把这一切,展现给一个只有五六岁的我么?丰盈与匮乏,尊贵与卑微,征服与被征服,荣耀与耻辱。他带着我来地里,我陪着他,我是他唯一的观众和见证人。我忽然想:在这里,一切都包裹于永恒的静谧中,没有噪音,我们与世隔绝,与世无争。我来到这个世上,也许就是为了和爷爷坐在这很多祖先走过的松林,为了或远或近地看着,凝望这西陵的黄瓦红墙,听爷爷讲并不遥远的往事,那些故事的主人公,因为埋在我们咫尺之遥的地方而更显真实,这些故事,这里发生的一切,从来都不曾间断,这就是永恒。我出生在一个大陵区里,一个最高级的坟地里,那里的每一个建筑,甚至每一棵树,都是为故去的人而设,都在提醒活着的人关于死亡,而我的先人们存在的理由,也是因为这些死去的人,要“照顾”他们,要最少一个月两次的祭奠他们,我们为此挣到一份粮晌,过着体面的生活。
儿时的我,不谙人之生死,只是知道这片皇陵就是我出生的地方,一些人的终点,另一些人的起点,本是一个点。(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六道轮回,如果知道,那么那些故去的人在这里转世再次回到人间,似乎也不是不可能,更何况西陵的人和皇族都或多或少地能扯上关系,皇帝家人投胎到自己远房亲戚家也很自然。)一切都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抗争或拧巴的,都是这么清晰明了按部就班,就如同我们家正屋墙上曾经挂的那幅山水画,如果不是生在西陵长在西陵,也许我是不会在小时就能想透这个事儿。
爷爷那时六十多岁,而我还没上小学,在田里干活累了,他就坐下,一边拿着那把壶,慢慢地喝两口茶,一边给我讲西陵的那些往事。他讲得最多,我听得最多的就是是梁鼎芬。似乎爷爷的记忆停滞在大清刚没了的民国初,西陵最后一个“入住“的皇帝光绪爷(溥仪的坟后来,90年代末也迁来,但那只是个小坟包)的万年之地的营建,都要由一个倡导民主共和而不再是贵为天子和掌管这个国家的帝王来负担。这种巨变,对遗老遗少们是一种“千古江山,舞榭歌台,总被雨打风吹去”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