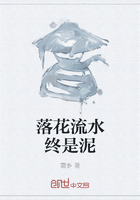杨仞笑道:“你没怎么听过停云书院,也不知柳空图是谁,还敢说自己在江湖上行走过?我看多半是吹嘘。”
“我不过还没记起来罢了,”许念哼了一声,眼珠转了转,忽而故作讶声道,“啊呦,我忽然想起来了,我从前在江湖上曾见过你那本刀谱的,当时却是被我随手撕了,哈哈,撕得粉碎。”
杨仞恍若未闻,只顾低头吃肉。许念随口咒了杨仞几句,撂下碗筷,到院落中晒太阳去了,过得片刻,但见杨仞也提着长刀来到了院中,便怪声怪气道:“杨帮主又要练刀呀,你可是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该当好生歇息才是,练刀这般辛劳,何不让你的帮众去练?”
杨仞一笑:“许老头,我就要离镇了,你现下还不害死我,以后可没机会了。”
许念摇头道:“你才刚满二十,还不懂得人世间的诸多乐事,这时害死了你,你临死时便没那么怕,没那么不舍,最好是再过几年,等你刚懂些世事人情,正意气风发的时候,最好是正觉得天下无处去不得、无事不可成的时候,偏偏害死了你,那才叫称心快意。”说着说着,语调亢奋起来,低笑不停。
杨仞听得怔住,随即哈哈笑道:“老子现下便意气风发得很,反倒怕你活不到几年后。”想了想,又道:“许老头,你已经这般老了,何不去做几件好事,到临死时也能安心些。”
许念道:“我老人家死也要作恶,做好事么,呵呵,下辈子再说吧。”
杨仞点点头,也不多劝,摆开架势便要练刀,瞥见院中野草在春风中晃来荡去,忽紧忽慢,宛若舞蹈,不由得心中一动,道:“天地间生机勃勃,也非只人之一物才有性灵。”
许念道:“不错,天地间生机太多了,须得多害灭一些才好。”
杨仞见他无时无刻不忘作恶,如此恒心毅力,倒也不禁有些佩服,便道:“嗯,那你今日又想害谁?”
许念多年来已在心中将他认识的每个镇民都害死了几百遍,闻言嘿嘿一笑,道:“今日我要害镇西的孙寡妇。”
杨仞笑道:“好你个许老头,原来人老心不老。”
许念皱眉道:“胡说,我是要害她,又不是要娶她。”
杨仞道:“是吗,那你干么脸红?”说完不等许念接腔,便径自练起刀来。许念抬手摸了摸自己脸颊,瞪着杨仞,半晌才恶狠狠道:“你练一辈子刀术,也只能用来割草!”
杨仞自顾自施展刀招,渐至心无旁骛之境,许念也不再说话,倚靠着枯树看着杨仞练刀,九年来两人常常如此,一动一静,便在这小小院落里打发了许多时光。
两个时辰过去,杨仞收刀站定,忽听许念道:“杨小子,这九年来你为何不换个住处,却一直住在我这里?”
杨仞一愣,往常自己练完刀术总会被许念嘲笑几句,今日这老头儿倒似有些反常,当即答道:“自是因为你这里租银便宜。”
“不对,”许念摇头道,“我知道周屠户找过你好几次,让你租住他的宅子,要的租银比我还少。”
“嗯,”杨仞点了点头,道,“也是因为你是唯一一个肯叫我杨帮主的人。”
许念闻言怔住,片刻后冷笑两声,却欲言又止。
便在这时,远处的街上隐约传来一片喧哗,似有不少人正自吵闹殴斗,杨仞听得皱眉,他虽知镇上迟早要出乱子,却也没想到这么快就闹将起来,等了一阵,喧闹声渐渐消隐,杨仞道:“我出去一趟,到春风酒楼探探消息。”
许念闻言脸色骤变,道:“莫要去,那春风酒楼可去不得。”
杨仞道:“为何去不得?”
“我也说不清,”许念似被问住了,挠头道,“我方才一听见‘春风酒楼’四字,心里便觉不大稳当,那酒楼多半是个险地。”
杨仞奇道:“春风酒楼在镇上开了许多年,你从前也不是没去过,为何今日忽然说是险地?”
许念神情迷惑,沉吟道:“方才听你提及停云书院之后,我似乎记起了一些从前的事,却与春风酒楼相关……”
杨仞道:“多半是你从前去那酒楼作恶,被揍过一顿。”想了想,又道:“不过那酒楼新换了一个姓龙的掌柜,古里古怪的,不去也罢。”
“不光那酒楼去不得,最好也莫要在镇上乱走,”许念压低了嗓音,神神秘秘道,“你可知我近日里为何不出门?”
杨仞一怔,回想过去九年,许念早睡早起,每日都吃满三顿饭,饭后从屋门口一路紧走到镇外的野地上,双手掰住一棵老柏树扭动周身,舒活筋骨,连喝三声“好!”,再慢慢踱回镇上,照他自己的话说,他得养足了精气,好去害人;可是过去几日,他倒确然没迈出过宅门一步。
想到这里,杨仞便道:“定然是你见到镇上来了许多陌生武人,便不敢出门了。”
许念哼了一声,道:“傻小子,那是因为我多日前便察觉到,这镇子与往年不大一样了。”
杨仞道:“有什么不一样?”
许念冷笑道:“如今若要在镇上胡乱走动,只怕迟早会被这镇子毒倒。”
杨仞愕然道:“好端端的一个镇子,怎会将人毒倒?你是说有人在镇子里下毒么?”眼看许念点了点头,当即问道,“什么毒这般厉害,我只要在镇上走动便会中毒?”
许念寻思了一阵,迟疑道:“这毒非同寻常,似乎是叫作惊……惊鸟还是惊什么来着,我一时记不分明了。”
杨仞笑道:“惊你个鸟,你少来唬我。”说完见许念眼神乱闪,神情中似颇有惧意,回想起吃饭时许念曾吞吞吐吐地问自己为何要走,不由得叹了口气,道:“许老头,你既这般害怕,不如别待在镇上,我便带你一起走吧。”
许念一愣,摇头道:“我才不走,我这把年纪,还能走到哪里去,更何况……嘿嘿,等镇上变乱一起,兴许我还能趁乱害几个人,那倒也美得很。”
杨仞正要再劝,忽而又听见院落外传来打斗吵嚷之声,这回却似是从四面八方响起,顿时心中一凛,提刀快步走到院墙边,跳上墙头张望,惊见临近的周屠户家中不知何时进了两个白衫方巾的男子,各持一根笔状武器,正与周屠户激斗。
杨仞心想:“这两人书生打扮,以笔为刃,想来便是停云书院弟子了。”又见周屠户挥舞一把屠刀,刀光霍霍,进退中步法颇为精妙,不禁更觉讶异:“原来周屠户武功这么高,我以前倒是不知。”
随即跃下墙头,又走到门边,透过门缝望去,不远处有个身形肥胖的华服公子,正领着数名书生走过来,只听那胖公子道:“凡是各派武人,以及家中藏有刀剑的,通通都先制住了。”那几个书生道了声“是”,便朝着旁边一户人家走去。
杨仞见状暗忖:“我住的这处宅院已是镇子的偏僻角落,他们既已搜到了这里,看来是想控住整座舂雪镇。”一边转念,一边走回院落中央,但见许念呆呆伫立、若有所思,便道:“许老头,你进屋歇歇吧,免得站断了你的老腿。”
说完便返过身来,提刀盯着院门,心知过不了多久那帮停云弟子便要闯进门来,暗道:“我与停云书院素无恩怨,他们既是武林中的名门大派,且看他们究竟意欲何为吧。”
他心中计较已定,便静静等候,哪知过得良久,门外脚步声远远近近,却始终无人进门。
又等了一阵,杨仞再度跃上院墙,望见周屠户倒在了院中,两个书生站在一旁,衣衫却已凌乱破裂;便在这时,其中一名书生忽然转头张望过来,一瞬间与杨仞对视。
杨仞心中一紧,随即心想:“去他娘的”,便又朗声笑道:“幸会阁下。”
那书生似是怔了怔,而后却转开头去,不理会杨仞了。
杨仞跳回院落中,颇觉迷惑:“这可奇了,难道他们怕了老子?”此时已近黄昏,天上阴云渐凝,不一会儿春雨濛濛洒落,他走到门边,打开一道门缝瞧去,门外却已空无一人,周遭也再听不见争斗声。
他重又闩住了门,回望见许念兀自茫然站在雨中,丢了魂魄似的,也不知在想些什么,直到天上滚过一声雷,许念忽然醒过神来,仿佛才察觉到下雨似的,嘴里胡乱咒骂着,快步进屋避雨去了。
杨仞也进了屋,这回不待他开口,许念便自去默默地生火烧饭,等到两人坐下吃饭时,许念忽道:“杨小子,你再说说停云书院的事吧?”
杨仞道:“说什么,有什么好说的?”
许念道:“说什么都行,你就随便说点。”语气中竟似有求恳之意。
杨仞点头道:“好吧,那你可知道停云书院现任的山长姓甚名谁?”
“不知道……”许念摇了摇头,随即又道,“哼,我是一时想不起,不是不知道。”
杨仞笑道:“那我帮你回想回想,此人姓燕,名叫燕寄羽……”
话音未落,骤见许念混浊的眼珠一瞬清明,浑如换了个人似的,不禁皱眉道:“许老头,你又发什么疯?”
许念脸色煞白,低声道:“出大事了,镇上要出大事……”
杨仞讶道:“什么大事?”问完等了半晌,许念却只反复呢喃着“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再没有别的话。
杨仞天不怕地不怕,心想再大的事也无非就是个“死”字,便也不再追问,径自大口吃喝来。
许念眉头紧皱,忽而颤声道:“不成,我须得找一样东西。”说完饭也不吃了,站起来在屋里四下翻找。
杨仞见他找得极是仔细,不放过任何犄角旮旯,不禁问道:“你要找的东西很要紧吗?”
许念冷哼道:“武林中再没比它更要紧的东西了。”说完便快步出门,又到隔壁杨仞住的屋子里搜寻;杨仞除了那把“清河”长刀再没什么值钱家当,便也任由他去。
直到春雨止息,夜色愈浓,许念仍未找到,颓然站在院落中,沉吟道:“没在屋里,那么一定就在院子里了……”
杨仞好奇道:“你究竟在找什么,说出来我也帮你找找。”
许念叹了口气,道:“我须得先找到了,才能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么。”
杨仞一怔:“胡言乱语,哪有这种事?”
许念也不争辩,拿了烛台,在院子里不住乱走,杨仞环顾院落,但见满地野草,一株枯树,除此之外便只有一口干涸多年的水井,忍不住道:“许老头,难不成你要找的东西是在井里?”
许念浑身一震,当即走到井边,竟似要跳进去。
杨仞吓了一跳,道:“老疯子,你要自尽吗?”快步走近,又道,“还是我下去瞧瞧吧。”
许念道:“也好。”
杨仞刚要下井,忽而回望许念,笑道:“许老头,等我下去了,你只消设法填死井口,便能害死我了。”
许念冷森森道:“嗯,你怕了?”
杨仞哈哈一笑,随即跳入井中,双臂在井壁上撑了几撑,很快下到井底。
许念趴在井缘向下张望,忽听杨仞惊呼道:“井底有个暗门!”许念皱眉回想片刻,冲着井底大声道:“你进去暗门,前行十丈,往左边石壁上摸索。”
杨仞闻言一脚踢烂那道狭小木门,走进门后的暗道,到了十丈外,果然摸到石壁上有一处凹陷,其中却放着一个细长物事,触去仿似一管竹筒。
杨仞带着竹筒回到院中,借着许念手中的烛台看去,那筒口封得甚为严密,也不知筒子里是什么。
许念见杨仞扭头看向自己,便道:“我一见到竹筒便记得了,这里面是一封书信。”
杨仞道:“书信?是你写的么?”
许念怅然道:“是刀宗云荆山写给我的。”
“刀宗写的?”杨仞一愣,“嗯,难得你还知道刀宗的姓名,他写了什么?”
许念道:“这信中写的,便是修成‘意劲’的关窍。”
“意劲?”杨仞道,“意劲又是什么?”
许念道:“意劲是刀宗所创武学,刀宗的刀术便是以意劲催动,那是极为神妙的。”
杨仞道:“能有多神妙?”
许念默然回忆良久,才道:“我依稀记得,云荆山的刀术中有一式名为‘刀云’,一旦施展开来,周围十数丈方圆内刀意弥漫,任何人踏进刀云之中,只要稍稍呼吸,便遭刀劲入体,割裂脏腑,荡灭神魂。”
杨仞道:“喔,原来如此。”
许念颔首道:“杨小子,你既要离镇,便请将这封书信送出去吧,就送与……”说到这里,忽见杨仞猛然间哈哈大笑起来,不禁怔住,皱眉道:“你不信?”
杨仞笑道:“你方才说的那些屁话,老子一句也不信。”
许念道:“你为何不信?”
杨仞道:“一来我不觉得世间会有意劲这种东西,二来即便真有,刀宗又为何要将如此重要的书信交给了你?”
许念闻言长叹,神情一瞬悲戚,随即转为深深悔恨,侧过头去,良久不再开口。
杨仞以前从未见他露出这般神态,瞧着绝不似作伪,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便只默然沉思。
却听许念又叹道:“你若不信,不妨打开竹筒看看,说不准看过之后便能修成意劲,那时你自然便信了。”
杨仞一怔,想了想,摇头笑道:“老子才不修什么意劲,乘锋刀法天下第一,已足够我练的了。”
“你小子竟不贪心,”许念闻言歪头打量了杨仞半晌,仿佛刚认得他似的,叹道,“似你这般自以为是的狂小子,江湖中倒也罕见。”
杨仞道:“过奖了。许老头,你刚才为何说要把这封书信送出去?”
许念道:“眼看镇上即将大乱,整个武林多半也要随之翻覆,这封信留在镇上太不稳妥,自须送走。”
杨仞听得狐疑,但见许念脸色凝重,便又道:“这信既是刀宗写的,何不再交还给刀宗?”
许念苦笑道:“若刀宗自己想要保管,当初也不会交与我了。”
杨仞道:“那你想将信给谁?”
许念肃然道:“那人便是玄真教的掌教真人,名叫李……”说到这里,目光霎时痴惘,似又犯起糊涂来,“是叫李、李什么的……”
杨仞道:“李素微。”
“不错!”许念立时拍掌道,“就是李素微那小娃儿,放眼武林,恐怕也只有他才能与燕寄羽抗衡……”
杨仞心下暗笑:这李素微是名震江湖的大人物,如今少说也有四十来岁了,却竟被这老头称作“小娃儿”;随即问道:“李素微为何要与燕寄羽作对?我可听说他俩交情匪浅。”
许念瞪眼道:“你懂个屁,玄真教与停云书院迟早要斗个你死我活……杨小子,你带上这竹筒尽快离镇,去到玄真教的总坛,务须将竹筒里的书信亲手交与李素微——”
话未说完,杨仞已连连摇头:“这俩门派之间爱斗不斗,关我屁事?那玄真教总坛远在东海之滨,你想让我跋涉万里为你去送信,未免想得太美。”
许念道:“杨帮主,你不是为我做事,而是为刀宗。”他往常称呼杨仞为“杨帮主”时,不是为了催促杨仞烧菜,便是意含嘲讽,这回语气恳切地说了出来,显是心中当真觉得此事极为要紧。
“许前辈,说来也巧,”杨仞笑道,“我恰好不爱为刀宗做事。”
许念稍作沉默,忽而嘿嘿笑道:“杨小子,你当年为何要来舂雪镇住下,还不是想靠刀宗的威名庇佑你安稳练刀,你既受了刀宗的恩惠,便该竭力报答才是,否则如何配当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
杨仞一愣,暗忖:“这疯老头自打见到竹筒之后,头脑似乎清晰了许多,转瞬便想到了此节。”他虽觉这鸟不拉屎的西域小镇本来也安稳得很,多半没有刀宗也一样是太平无事,但自己听从师命来到镇上,确也是存了一些倚靠刀宗的心思;寻思片刻,笑道:“许老头,你这话也不无道理,我便走一趟东海玄真教总坛,只是那李素微肯不肯收信,可不是我能说了算的。”
许念顿时面露喜色:“甚好,甚好。”正自呵呵笑着,却听杨仞又道:“你若要我去送信,还须答应我一件事。”
许念道:“什么事?”
杨仞道:“你须得入我乘锋帮,做我的帮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