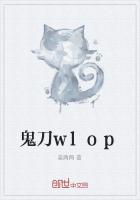孙先生这一次到日本,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第一,孙先生革命的主张,既经完成,必须要更广大地宣传,准备第二次的革命,但那时欧洲的华侨很少,也没有留学生,要鼓吹革命,也无从鼓吹。日本与中国,在地理上是很接近的,最便于革命的策划;第二,因为那年孙先生到伦敦以前,陈少白留在日本,对于兴中会的推广,已经有相当成绩;孙先生回到内地,当然是不可能了,因此只有到日本,准备凭借在日本的兴中会的基础,来做第二次的革命工作。
孙先生到日本的时候,大约是在纪元前二十三年八月底九月初的光景。到了横滨,就去找陈少白,患难余生,看见了老朋友,真觉得有异样的快乐。那时少白一个人在日本,因为几个华侨想学习国文,就利用机会,发起组织学校,但少白这时想到台湾去,现在孙先生来了,他就把这事情报告孙先生,要请他赞助。孙先生就替他题校名,叫做中西学校,教员由少白提议托梁启超在上海代请。梁启超是少白当第一次广州起义时孙先生要他到上海来招集同志时认识的,那时梁启超正和康有为进京会试,路过上海,同住在洋泾浜全安栈内,就此相识起来了,少白因为他是主张维新的,革命党里当教员的人又很少,所以就托他代聘,孙先生也很赞成。不久,少白就到台湾去。但梁启超介绍的教员,还没有到日本,他已把中西学校的名称,改了大同学校,孙先生因为这是小节,也不去交涉,这是维新党和革命党最早的联络,也是最早的伏下了冲突的导火线。
在孙先生未到日本以前,少白已认识了几个日本朋友,如曾根俊虎、宫崎弥藏等。那时宫崎弥藏病得很重,他有一个兄弟叫做宫崎寅藏又名宫崎滔天,正在暹罗,他就写了一封长信,说横滨有一个中国革命党的重要人物,要他赶快回来。宫崎寅藏回来的时候,他的哥哥已经死了,他就由曾根俊虎的介绍,认识了少白。少白把中国革命的要旨告诉了他,并且给他一本孙先生的《伦敦蒙难记》,他对于孙先生竭诚倾慕,就立刻要少白写信介绍在香港、广州、澳门的兴中会的同志,因为他在报上看见孙先生已经离开英国,他准备到广东去访求孙先生。但是他到了香港、澳门,孙先生却已来日本,他就赶回来。那时,孙先生就住在少白的寓所,宫崎寅藏一到了横滨,就到少白的寓所,但少白已经走了。这时候大约是在早晨,孙先生还没有起床。宫崎寅藏刚刚坐下来,看见里面走出来的人,就是在相片上见过的革命领袖孙先生,他快活得几乎要跳起来,孙先生因少白也曾提起过宫崎寅藏的事情,所以一见面大家就很亲热。但孙先生那时不十分能说日语,他们就用笔谈,纵论中国革命形势。孙先生问宫崎寅藏日本政府能否帮助中国革命。宫崎说:这事情必须要问犬养,犬养曾说:大臣大隈很容易讲话的,只要陆军参谋长能够同意,事情就好办。大概犬养已经和大隈谈过,不过他为审慎和秘密计,不愿意说出来罢了。犬养就是犬养毅,因为那时日本民党初握政权,大隈为外相,犬养毅帮助大隈办理外交事务,他在大隈前面是很有讲话力量的,宫崎寅藏等许多志士,都是奉了犬养毅的命令,调查中国革命的。接着,孙先生就和他讨论革命的发难地点;
“今日有志者,到处皆是,惟不敢言而已(原文矣字,疑为已字之误)。是以吾辈不忧无同志,只恐不能发一起点而已(同上)。有一起点,即如置一星之火于枯木之山矣,不必虑其不焚也。惟此起发之地,阁下以何为最善?前者弟以广东为最善,因人地合宜也。广地一月之内,必可集山林剽悍之徒三四十万,但有前年之失,当地之官,已如惊弓之鸟,到处提防,我辈举动,较前略难矣。是广东者,今日非善矣。不先择定一地,则无由定经略之策也。”
“还是以四川为负隅之地,有张羽翼于湘、楚、汴梁之郊原耳。”
“但四川不近海口,接济军火为难,奈何?”
“军火一项,虽近海口,亦所难,无已,开接济之道于浙东之沿岸乎?”
“是亦失之太远,诚如前之所言,在山东、河南、江苏交界。可招二三万众,则以江苏之海州为最善矣。暨起点之地,必先得人,其次接济军火之道,其三不近通商口岸,免各国借口牵制,海州之地,于此三者皆得握运河,绝漕米,此亦制北京之死命。”
“取于海州之事,弟已于十余年前思量之,曾到彼地盘桓七八天,细看海口之形势,不便入巨船,只离海州数十里,云台山在海中,有可靠大船耳。且州城有厘金,每小船通过稽查甚严。”
“到此时不怕厘金卡矣,弟所谓起点者,则先夺取一地,而意亦并指云台山也。”这是孙先生的答复,但孙先生接着又改变口气写道:“先夺云台,结束已成,而人县城,或事可集,然是亦不得谓恰好之地。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已。在海州则进取接济,亦利于广东矣,惟聚人则弟对此毫无把握;盖万端仍以聚人为第一着,故别处虽有形势,虽系接济,而心仍不能舍广东者,则以吾人之所在也。”
“如阁下之此地,可招二三万众,亦可集事矣。盖海州既有两便。又有其人,则北可进握山东,以窥北京;南则夺取淮扬,以通大江,则粮食无忧也。有人有粮有器,成败在乎运筹指挥之策耳。”
“从海州到河南,山东之交界,约要十数天,此间一带之地,土赤民贫,无糗粮之可续,我数千之众,逡巡之间,或为敌所乘,弟故以为起点之地,先要选(原文撰字)形胜之区。”
他们笔谈的内容很广泛,从孙先生第一次起义失败经过起以及革命后的远东国际形势,和孙先生到日本后的起居问题等等都谈到,并且谈得很投机。
宫崎寅藏在他所著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中,还记载了一段和孙先生讨论革命宗旨和政治建设问题等的谈话。孙先生说:
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岂唾手可得?必也革命……
且夫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且适合于中国国民,而又有革命上便利者也。观中国古来之历史,几经一次之扰乱,地方豪杰,互争雄长,亘数十年,不幸同一无辜之民,为之受祸者不知几许。其所以然者,皆由于举义者无共和之思想,而为之盟主者。亦绝无共和宪治之颁布也,故各逞一己之兵力,非至并吞独一之势不止,因有此倾向,即盗贼胡虏。极其兵力之所至,居然可以为全国之共主……今欲求避祸之道,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之一法。而与革命同行者,又必在使英雄各竞其野心;竟其野心之法,唯在联邦共和之名下,夙著声望者,使为一邦之长,以尽其材。然后建中央政府以驭之,而作联邦之枢纽……此所谓共和政治,有革命之便利者也。
那段谈话,可以看出孙先生民权主义思想的最早形态。所谓满足英雄的野心。也许受了早年在求学时代“四大寇”帝王幻梦的刺激。就是第一次起义杨衢云的力争总统,也何尝不是英雄思想的作祟?所以孙先生说共和政治有革命的便利。孙先生此后民权主义的完成,固然根据了世界最进步的潮流和中国立国的精神,但他初期思潮的发动,和上述两件事实,不无多少关系。
宫崎和孙先生经过几度接触,他就回东京去报告犬养毅,从此以后,常常到孙先生这里来和他畅谈;不久平山周也来了,他们对于孙先生都一致地推崇和尊敬。
犬养毅因宫崎寅藏、平山周等的报告,对于孙先生也非常钦仰,急于一见,于是就在孙先生到日后的第二年正月(纪元前十四年,1898年),由宫崎寅藏、平山周代表他到横滨来欢迎孙先生到东京。当日的情形,犬养毅曾在一篇谈话中表示过,这谈话的题目是“革命志士之风骨”,就在前年(民国二十年,1932年)发表于东京《朝日新闻》。他说:
褴褛洋服之孙逸仙氏,具有革命志士之风骨。孙氏与余第一次会晤,系在明治三十一年,由宫崎滔天等导孙氏同至余处,并为余介绍。宫崎者,一富有兴趣之丈夫也。忆外务省曾命其调查中国革命之秘密结社,在横滨会见孙氏,意气非常契合,即相偕以赴东京,并晋谒外务省报告云:“中国革命秘密结社之标本,已携来在此,以代报告书如何?”自是政界中人,一扫前此之偏见,而乐相周旋矣。当日余甚贫乏,时为新岁正月,仅以盐鱼一尾饷客,而所邀至五十人之多,如头山满、平山周、古岛一雄等皆在其列。彼等对于此眷怀故国,寄身海外之孙氏,成表极薄之同情。协商结果,遂请孙氏迁居早稻田附近之小屋内,并于门上标以“中山樵”三字,盖以用中国人名义,恐引人注目也。于是此假名之“中山”二字,竟成举世尽知之孙氏名号:即现时中国人所通称为孙中山先生是也。
这是孙先生与日本政界交际的开始,犬养毅所说的,当然是根据他的回忆,是很可贵的史料。但关于孙先生改名中山的经过,似乎说得太简单了,应该拿平山周的话来补充,他说:
同车访犬养,归途过日比谷中山侯爵邸前,投数寄屋桥外对鹤馆,掌柜不知总理之为中国人,出宿泊贴求署名,弟想到中山侯爵门标,乃执笔书(姓)中山,未书名,总理忽夺笔自署(名)樵,曰:“是中国山樵之意也。”总理号中山,盖原如此。(平山周对总理年谱长编初稿签注意见函)
大概孙先生迁居东京,是由于犬养毅诸人的邀请,但最初住的不是早稻田附近的小屋,平山周因为陪同孙先生一起去的,所以说得近于事实。当时日本还有租界制度,不准内外杂居,平山周就托名聘请中国语教授,才得开商场外侨居住的许可的先例。九月,孙先生又迁居曲町区五丁目,一直到十月,才迁到早稻田鹤町居住。从这时候起,孙先生认识了许多日本朋友,在政界的如大隈、大石、尾崎、副岛种臣等。在野的志士,如头山满、平冈浩太郎、中墅二郎、萱野长知、的墅半介、福本日南、内田良平、中村弥六、井上稚、原口闻一、平冈小太郎、清藤幸七郎、山田良政、安川、犬冢、久原、铃木、秋山、菊池宣野等。其中平冈浩太郎,是九州岛福冈煤矿的主人,家里很有财产,对于孙先生倾慕极了;孙先生住在东京时,他知道孙先生境况不佳,每月房租饭资,都由他一人负担,这样豪侠的性格,是很难得的。平山周因为能说简单的英语,孙先生和日本朋友谈话时,他可以当翻译,所以常在孙先生的寓所里。
那时,日本志士都说东洋的和平,在乎中日两国之真正的提携,两国之真正的提携,尤赖于国民双方相互的理解与拥护,所以对于中国革命是非常关心的,对于中国革命领袖孙先生尤其是热烈的欢迎。正如平冈小太郎所说:“吾辈在此理想之下所结合之同志,皆能与孙氏有理解之思想相吻合,而出以极热忱之共鸣,于是同志间一片侠气,竟至由协助而完成孙氏回天之事业。”(见平冈小太郎回想)那时日本政府对于中国革命党也许没有十分注意,对于一般志士的奔走联络,也许不能公开地加以援助,幸有犬养毅一面联络了许多志士,一面在大隈面前解释,他在那篇谈话中也说到这一点,他说:
当时政府及政党,对外国亡命来日志士,从来予以密切之注意,但以对外关系之故,表面上则不能不取以弹压主义也。余在当时与宪政本党已有关系,然无论宪政本党,或旧自由党系人,对于中国革命派,而欲其加以援助者,实未多见,尤以大隈侯对于浪人之举动,极为嫌恶,故头山满曾谓余曰:“政党方面,谅解浪人之烦扰者,仅君一人而已,君意谓何?”
这是确实的。当时犬养毅对于孙先生是有很多帮助的,但是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第一幕的“九一八事变”以后,接着就于1932年1月28日发动淞沪战事,就在犬养毅出任内阁总理的时代,他们早已忘掉当年和我们革命党所讲的什么中日提携,确保东洋和平的话,遂造成了中日两国的深仇大恨,甚至影响世界局面的纷乱,这是人类感情上的一大奇变啊!
孙先生在东京住了很久,后来因为经济上的关系,还是回到横滨去住,同时,那边华侨很多,孙先生想在那边做一番宣传的工夫,有时还是到东京来,于是他就往还于东京横滨之间。但是横滨的华侨,风气的锢塞,怕听革命的宣传,和在别个地方的华侨,没有什么分别,孙先生鼓吹了很久,加入兴中会的不过百多人。但横滨的华侨加入会党的很多,孙先生就不断地向他们开导,有时予以经济上的援助,他自己只是穿着一件很破旧的西装,但始终很镇静地抱着乐观的态度。犬养毅有时对孙先生笑着说:
“阁下倘长此抱着释迦、孔子等说法的态度,怎样能够做这样庞大的党的党魁?”
孙先生静默地没有回答,只有报之一笑。
这时候,杨衢云在南非洲听到孙先生已到日本,并且外国报纸都宣传孙先生已筹得二三百万块钱,预备再行革命,他就不辞跋涉到东京来见孙先生,当他到横滨时,孙先生正在一个友人的俱乐部内,听到杨衢云要来见,立刻勾起了那年第一次广州失败的往事,情绪复杂极了,同座的许多友人,也认为是出乎意料的事情。他进来了,孙先生就请他到旁边一间房内,把门关上了,向他斥责当年失败的责任。孙先生说:
“当时你要做总统,我就让你做总统;你说要最后到广州,我就让你最后到广州。你为什么到了时期,你自己不来,那还罢了,随后我打电报要你不来,隔一日,你又不多不少派了六百人来,把事情闹糟了,消息泄漏,人又杀了,你得了消息,便一个人拼命跑掉,这算是什么把戏?”
杨衢云俯首红脸,知道过去偌大的风波,都是他一个人造成的,他内心顿时起了极度的忏悔,他对于孙先生严正的呵斥,只有承认,便吞吞吐吐地说:
“以前的事,是我一人的错误。现在听说你筹得大款,从新再起,因此不怕远赶来,是想再为革命奋斗,请你恕我前过,容我再来效力。”
“你能认错,那就没有事,将来有机会再共事吧。”孙先生很和蔼地答复他,说着就让他走出来。俱乐部内的人,都看见他脸上罩着一层灰白而有浅红的颜色走过,就向他略事寒暄,大家心里却非常感动孙先生对待朋友不使难堪的那种伟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