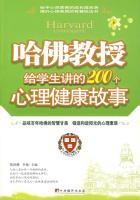Ⅰ 书目
1900年莱比锡与维也纳,弗朗茨·多伊蒂克出版社。(1899年发行)4+375页。
1909年第二(增补修订)版,同一家出版社。7+389页。
1911年第三(增补修订)版,同一家出版社。10+418页。
1914年第四(增补修订)版,同一家出版社。10+498页。
1919年第五(增补修订)版,同一家出版社。9+474页。
1921年第六版(第五版的重印,不过有新前言与修订的书目),同一家出版社。7+478页。
1922年第七版(第六版的重印),同一家出版社。
1925年全集第2卷与第3卷一部分(增补修订)。莱比锡、维也纳与苏黎世,国际心理分析出版社。543页与1—185页。
1930年第八(增补修订)版,莱比锡与维也纳,弗朗茨·多伊蒂克出版社。10+435页。
1942年全集第2卷、第3卷(第八版的重印)。15+1—642页。
尽管扉页上事先标明为新世纪,《梦的解析》在1899年11月初就已经出版了。它是弗洛伊德每次新版时都或多或少系统性地使之达到最新知识水平的两本书之一,另一本是《性学三论》(1905年)。本书第三版后,却不再标出弗洛伊德每次所做改动;而这给以后版本的读者造成一些困惑,因为新材料间或假定人们熟知弗洛伊德在本书出现很久之后在观点上的那些更改。弗洛伊德著作(全集)初版的编者尝试过控制这种困难,他们在第一卷中重印原初形式的《梦的解析》初版,在第二卷中集聚后来逐渐增添的一切。可惜当时没有系统性地实施这项工作,增补本身没有注明日期,由此牺牲了这种版本方案的许多长处。于是在后续的版本中,复归单卷的、未区分不同阶段的版本旧稿。
多数增补所包含的单项主题是梦象征。弗洛伊德在本书第六章戊节开头解释,他后来才完全明了问题的这方面的意义。
在初版中,对象征的探讨限于第六章关于“顾及可表现性”那一节末尾的少数几页。在第二版(1909年)中,对这一节没有增补什么;而弗洛伊德在第五章关于“典型的梦”那一节末尾插入了关于性象征的几页。这几页在第三版(1911年)中还有了明显扩展,而第六章原初的段落又保持不变。无疑,重新编排被耽误了,所以,他在第四版(1914年)中把关于象征的全新一节(戊节)插入第六章,他把当时收集在第五章中的属于该主题的材料转到这一节,还通过其他全新的材料来补充。在所有后来的版本中,本书的这种总体结构不再有什么改动,虽然也还增加了许多新材料。在二卷稿(1925年),也就是第八版(1930年)之后,在关于“典型的梦”一节中重新收录了先前删去的一些段落。
在第四、第五、第六与第七版(也就是自1914年至1922年)中,在第六章末尾可以找到奥托·兰克的两篇文章(《梦与创作》,1914年;《梦与神话》,1914年。在《梦的解析》中首次发表),以后却又付诸阙如。
关于书目:初版包含约80种书的一份清单,多为弗洛伊德在文本中涉及的那类著作。它未做变动也包含在第二与第三版中,不过,在第三版中,增加了自1900年起出版的约40种书的第二份书单。此后,两份书目迅速增加,直至在第八版中,首份书单包括逾260种,第二份包括逾200种。在此阶段,1900年前出版的各种著作的首份书单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确实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中被提及;另一方面,涉及1900年之后刊行的文献的第二份书单(从弗洛伊德自己在其不同的前言的说明中可以获悉)不能与关于梦这一主题的分析性论文或者准分析性论文的迅速产生保持同步。最后,弗洛伊德在本文中引用的大量书籍在两份书单中都找不到。从弗洛伊德致安德烈·勃勒东[1]的信(《致安德烈·勃勒东的三封信札》,1933年)中可以获悉,从第四版起,奥托·弗兰克单独负责拟定了这些书目。
Ⅱ 本版次
本版次基于全集第二、第三卷的双卷文本,与第八版(1930年)即弗洛伊德在世时最后一版的文本相应。同时,本版次在很重要一点上有别于所有早先的德文版:它顾及到了在不同版次中包含的异文。本版次试图标明自本书首次刊行以来所做的任何重大改动并注明日期。在一版接一版中,对弗洛伊德而言,重要的始终是补充的材料多于删除的材料。删去的段落以及弗洛伊德后来付诸阙如或者大做改动的先前版本的材料通常不收入本版次。构成例外的是我们看来具有特别意味的一些少量例子,它们被放在编者注释中。删去了兰克对第六章的补遗:两篇文章均独立成篇,与弗洛伊德的书没有直接关系;此外,它们可能会再占去50页。
书目得到完全修改;它们根据弗洛伊德著作的英文标准版第五卷在其中再现,带有附加的订正与补充。首份书目包含确实在文本中或者在脚注中提及的全部论文。第二份列举1900年之前的所有那些论文,弗洛伊德在收入全集的书目中举出它们,而在弗洛伊德的文本中没有引用它们。刊印这份清单之所以让我们觉得富有价值,是因为无法轻易得到关于较早的梦文献的类似全面书目。除了确实在文本中提及,因而被收入首份书目外,不考虑1900年之后出版的论文。然而必须就这两份书目提出警告。探究表明,在先前德文版的书目中包含许多错误。只要可能,已经在标准版中纠正了这些错误,其他一些错误在本版次中得到修正。数量并非微不足道的条目却至今没有被证明为可以核实;这些带有星号的书籍不得不被视为有疑问。
编者补充——脚注、引文出处说明以及众多相互参照提示——放在方括号中。
Ⅲ 历史
正如我们从致弗利斯的信札(《精神分析肇始》,1950年)中得知,弗洛伊德从1896年夏至1899年秋写作《梦的解析》,其间有过中断。该著作中所阐述的理论在他那里却很久以前就开始形成了;材料搜集也是如此。
除了零星分散提及此题目,这在弗洛伊德的信札中可以追溯至1882年,在布罗伊尔[2]与弗洛伊德的《癔症研究》(1895年)中,在他对其首个病史(埃米·冯·N女士的病例,日期为5月15日)的一个长长的脚注中可以找到首个重要的、出现在出版物中的出处,它提供了弗洛伊德对梦感兴趣的消息。他在那里探讨该事实,即神经症患者似乎需要把偶然同时闪过的想象彼此联系起来。他继续写道:“我早就通过在其他领域的观察能够确信这样一种强迫联想的威力。我不禁持续几周混淆了我惯常的床铺与一张更硬的卧榻,我在后者上面很可能或多或少做梦更强烈,或许只是不能达到正常的睡眠深度。我苏醒后头一刻钟还记得夜里所有的梦,努力写下它们并尝试解梦。我成功地把它们全部归因于两个因素:(1)归因于要完善此类想象的那种强迫,我在日间只是匆忙地停留于这些只是触及而未了结的想象;(2)归因于那种强迫,要把在同一意识状态中存在的事物彼此联系起来。梦的无意义与充满矛盾应归因于后一种因素的自由主宰。”
同年(1895年)9月,弗洛伊德写作其《心理学纲要》第一部分(作为弗利斯信札的附录发表);该“纲要”的第19段、第20段与第21段首次接近连贯的梦理论。它们已经包含在本著作中再度出现的许多要素,如(1)梦的遂愿特征,(2)梦的幻觉特征,(3)精神在幻觉与梦中的退行性作用方式,(4)睡眠状态暗含运动麻痹,(5)梦中移置的机制,(6)梦的机制与神经症病征机制之间的相似性。比所有这些更重要的却是:该“纲要”已经明确暗示在《梦的解析》给予世界的发现中可能是最本质的发现——区分两种不同的心灵作用方式——初级过程与次级过程。
这样却绝非穷尽该“纲要”和与之相连的1895年末致弗利斯信札的意义。可以不夸张地断言,通过该“纲要”的发表,《梦的解析》第七章,甚至弗洛伊德后来的“元心理学”研究的大部分才变得完全可以理解。
虽然不可能在此探讨个别问题,但还可以相当简单地概述诊断的基本特征。弗洛伊德在其“纲要”中本质上追求的目标是,把不同起源的两种理论合并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第一种理论最后可以溯源到赫尔姆霍兹[3]的生理学学派,弗洛伊德的老师、生理学家恩斯特·冯·布吕克[4]属于该学派,并且是主要代表之一。根据这种理论,神经生理学因而还有心理学听从纯粹化学—物理学的规律。例如“恒定原则”是这样一种规律,无论弗洛伊德还是布罗伊尔都频繁提及,1892年(在身后发表的概要中,布罗伊尔与弗洛伊德,《关于癔症发作的理论》,1940年)描述如下:“神经系统力求……在人们可能称为‘刺激总量’的机能情况下保持恒定。”由弗洛伊德在其“纲要”中牵扯进来的第二种理论是神经元的解剖学说,80年代末开始在神经元解剖学家那里得到认同。(“神经元”这一名称却于1891年才由瓦尔代尔[5]新造出来。)据此,中枢神经系统的机能单位是一个特定细胞,与邻接细胞没有直接的解剖学上的关联。“纲要”开篇几句清晰地表明,它基于这两种理论的组合。弗洛伊德写道,它的宗旨是“把心理过程展示成可指明的物质部分在数量上确定的状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肇始》,1950年,第378页)。他随后假设,这些“物质部分”是神经元;使其活动状态有别于静止状态的是“服从普遍运动规律的”一个“数量”。所以,神经元既可能是“空的”也可能“充满某个数量”,亦即“被占的”。[6]可以把神经兴奋解释成流经神经元系统的一个量;根据神经元之间“接触栅栏”的状况,这样一种流动可能遇上一种“阻抗”或者一种“铺平”。(“突触”这个术语1897年才由福斯特[7]、谢灵顿[8]采用。)整个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受制于一项普遍的“惰性”原则,神经元据此始终力求摆脱充满它们的“数量”——一项与“恒定原则”相关的原则。以这些概念与类似概念作为元件,弗洛伊德建立起他那高度错综复杂、极其富于创造性的心灵作为一个神经病学系统的工作模式。
但很快,不明之处与困难就开始积聚,在写下“纲要”后的几个月里,弗洛伊德总是忙于改善其理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兴趣却从神经病学问题与理论问题转移到心理学与临床问题上;最后,他放弃了整个项目。他于几年后在本书第七章中重拾理论问题时,显然不再力求神经—生理学基础——尽管他肯定从未放弃信念,有朝一日会为心理学建立物理学基础。[9]虽然如此,还是有早先模式的许多普遍性结构标志与众多个别特征进入在《梦的解析》中生发的新模式,而这是为何“纲要”对后一部著作的读者而言具有意义的理由。弗洛伊德先前假设的神经元系统就由心理系统或者审查机构代替了;代替物理“数量”而出现的是假设性“投注”心理能量;惰性原则成为愉悦(或者如弗洛伊德在此所称的无趣)原则的基础。此外,在第七章可以找到的一些对心理过程的详细阐述也多应归功于那些生理学先驱,回顾他们,这些阐述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例如,这适用于“回忆系统”中对回忆痕迹中断的描写,适用于探讨何为愿望以及遂愿的不同种类,也适用于强调言语性思维过程在适应现实要求时的作用。
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足以证明弗洛伊德的断言是正确的,即《梦的解析》“基本上于1896年初完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运动史》,1914年,临近第一节末)。(弗洛伊德后来才发现三点理论意义,即俄狄浦斯情结的存在最先导致正确评价梦作为根据的潜意识愿望的幼儿期根源——主宰所有梦的睡眠愿望和“继发性整合”的作用。)
弗洛伊德不仅把手稿而且把校样不断寄给弗利斯供其评价。后者似乎对本书的最后成型有过显著的影响并负责出于保密考虑删去一些段落。但最严厉的批评来自著作者本人,主要针对风格与文学表现形式:“……我相信,”成书后,他于1899年9月21日写道(《精神分析肇始》,1950年,信札第119号),“我的自我批评并非完全无理。在我身上某处也蕴含着一丝审美感,鉴赏作为一种完美的美,而我的梦著作里拐弯抹角、用并非直截了当的言辞扬扬自得、着眼于意念的句子严重伤害了我心中的理想。如果我把这种形式缺陷理解成缺乏对材料的控制,也几乎不冤枉。”
尽管有这种自我批评,虽然有一阵子弗洛伊德苦于情绪低落,当时本书几乎完全被公众忽略——出版后头六年里只售出351册——他还是始终把《梦的解析》视为其最重要的著作。“像这样的顿悟,”他在英文第三版的前言中写道,“一生却注定只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