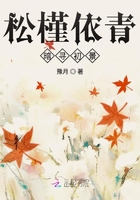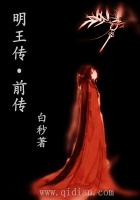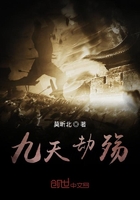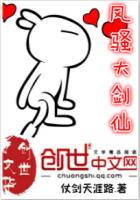有这种问题的人可能会感到很挫败,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行为。我经常问自己,这种行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换句话说,是基因决定了一个人的囤积行为,还是与他的成长方式或者经历有关?但是,无论认为是先天决定还是后天形成的,都可能简化了这一问题。强迫性囤积症既有来自基因的影响,也有来自环境的影响,但即使把这些都考虑到,也没法预测一个人是否真的会囤积物品。
我们已经确定,基因因素会导致强迫性囤积症的形成,而且如果有人有这方面的家族史,那么强迫性囤积症就会更容易出现。此外,囤积也可能是后天习得的一种应对焦虑的方式———如果一个小孩看到她的母亲用囤积的方式来缓解丧亲之痛,那么他也可能会学着用这种方式来应对自己的情绪。大多数专家都同意,这些因素对于强迫性囤积症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影响。如果一个人的基因决定了他会囤积,那么当他面对这些环境因素时,也就更容易受到影响。有时,我们也会在强迫性囤积症患者的家族病史中,发现其他与焦虑相关的问题。
也有许多人在父母是强迫性囤积症患者的家庭成长,但他们并没有发展出强迫性囤积症。这些人会对童年的生活环境作出反向的反应,对于杂乱的容忍程度比一般人更低。又或者,他们只是在基因层面上没有囤积的倾向。不管怎样,强迫性囤积症是一种复杂的状况,需要针对个人的情况制订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一般来讲,囤积行为在生命的早期阶段就会开始,只不过人们通常直到五十多岁才会去寻求治疗。有人认为,男性的囤积问题比女性更常见,而在我的诊所中,我发现女性比男性更愿意寻求帮助。在生命的后期阶段,强迫性囤积症看上去更明显,这可能是由于一些间接的原因导致的。例如,当一个人进入大学时,他的囤积倾向通常会受到遏制,因为他只有一个房间,或是有一个厌恶杂乱的室友会不断地纠正他。后来,他也许遇到心上人,步入婚姻,这在一开始会带来积极的影响。不过,渐渐地,他所爱的人也会接受一定程度的杂乱———“老爸真的很喜欢工具,车库都是他的地盘”。就像强迫性囤积症患者一样,他们也习惯了这种环境。
此后他的生活状况通常会螺旋式下降。当孩子长大离开家以后,强迫性囤积症患者可能变得更加孤独,空巢也意味着他有更多的空间来囤积,而且这时他一般也不再请人来家里做客。没有外人来观察他的房间,这意味着他可以一直否认房屋的现状,继续积攒物品。就像珍妮弗的案例一样,强迫性囤积症患者的子女们,经常会被他们父母的生活方式所震惊。而强迫性囤积症患者的配偶经常无法忍受在杂乱中生活,从而离开他们。
我经常会思考,囤积是不是来自于童年的某种缺失。例如,一个人可能小时候非常穷,得不到他需要的东西,这会不会让他在成年后更容易囤积物品?这是有可能的———我见过有些人曾因为过去没有足够的食物,所以现在过度地囤积它们。但根据我的经验,这种缺失通常不是强迫性囤积症的导火索。有些强迫性囤积症患者成长在物质充裕的环境里,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也有人成长在物质匮乏的环境里,却没有强迫性囤积症的困扰。
囤积也不是心理创伤的必然结果,不过如果一个人本身有强迫性囤积倾向的话,创伤确实可能会触发囤积。而且有研究表明,一个人经历了越多的创伤,他们的囤积问题就越严重。例如,众所周知,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会囤积食物、钱、衣物等东西。作为例子,我立刻想到了我的患者珍妮(Jennie),她是一位50岁的母亲,她的儿子死于婴儿猝死综合征。我相信,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改变她生活的严重创伤,她不会开始强迫性囤积。另一个例子是比尔(Bill),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警官。有一天晚上他去调查一起车祸,却发现是他自己的女儿被一个喝醉的卡车司机开车撞死了。他被这件事击垮了,在休假一段时间之后,他依旧没法恢复工作,因为每当他被派往车祸现场,他都害怕是自己另一位家人被卷进去了。比尔没法走出他的悲伤,于是隐居了起来。他的食物是别人送上门来的,他在网上购物以避免开车去任何地方。比尔限制了家人的来访,开始把他的时间花在收集上。他沉浸在找到一件特殊的工艺品,或是淘到便宜货的感觉之中,他在屋子里放满了这些东西,而大多都只是堆在箱子里,没法取出来。很快,他的房子只能通过这些箱子中间狭窄的小道进出了。出于对他的关心,他的家人威胁他,如果不接受治疗,就要向成人保护服务机构(Adult Protective Services)举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