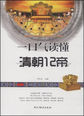1881年4月,梵高从布鲁塞尔返回父母所在的埃顿。这时,他遇到了同时到达这儿的表姐凯。她是曾在阿姆斯特丹帮助过梵高的牧师舅舅的女儿,因为刚刚失去丈夫来这儿散心。
凯表姐本就拥有修长窈窕的身材和白皙细腻的皮肤,身着的高腰大摆黑色长裙和绾成发髻盘在头顶的秀发更是衬出她的优雅和清新,远远地望去,她就像巴黎最时兴的名媛形象打扮,也像莫奈笔下惬意游园的富家小姐,优渥闲适,仿佛和矿下那些哀号悲痛的女人来自两个世界。这个温婉美人走下画卷鲜活起来时,并没有让人失望。和你谈话时,她会浅浅笑着,用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鼓励你表达的欲望;她也会低声发表自己的意见,却俨然带着一副建议而不强势的姿态;她并不是不沾阳春水,长期的家庭生活的熏陶使她成了照顾孩子、收拾家务的一把好手,但哪怕是做这些日常事情时,她的每一个剪影,也像画一样让人沉醉不已。
梵高渐渐发现,除了作画,自己每天多了一项可期待的东西,那就是见到凯表姐。见到她之后,自己的疲惫仿佛一扫而光,也觉得生活特别美好,提起画笔的欲望更加强烈。凯活力青春,这种活力与单纯不同,她的一颦一笑、隐忍欢乐都带有时光的印记,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梵高。
有时,他和凯表姐的孩子一样绕在她的身边叽叽喳喳地分享着这一天细碎的生活。“凯表姐,看看我今天刚刚画的铲土的人。”“表姐,您来帮我看看,这幅对劳动者的画像有没有米勒的感觉?”“凯,你知道我为什么现在专攻人物画了吗,因为画人物时更能训练观察力。而且能把人物画好了,风景画肯定不在话下了。”“凯,你不要叫我表弟,叫我梵高吧,这样咱们之间的关系就稍微亲近一点,显得不像外人那么客套。”“凯,不知道为什么,虽然你气质和外形比我画的农妇好很多,但都有一种深深的无奈和宿命感,凯,你知道吗?这种气质特别吸引人。”除了提奥之外,没有人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听梵高絮絮叨叨,讲一些绘画和文艺理论的事情。恪守大家闺秀风范的凯小姐言辞婉转,目光清亮,这无疑是对梵高最大的鼓励,他也一股脑地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倾泻出来。有时,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在忙忙碌碌的凯表姐旁边支起一个画板,开始调色泼墨,凯表姐就像一颗太阳,给梵高这棵植物提供了无穷的热量。
凯表姐仿佛也感知到了什么,这个表弟对自己非一般的热络和倾诉,让这个已然经历过男女之事的她有了些隐隐的不安。而当自己答应当他的模特时,他那充满热切欲望的眼神又让她脊梁发凉。她承认,这个表弟虽然身材矮小,但只要换掉工装背带还是能穿出绅士的温文尔雅,他饱读书籍,也不是粗鄙肤浅之辈。只是,一想到要触犯新教的禁忌,触碰乱伦之恋而受到众人的指指点点,她就不寒而栗,自己从小培养的淑女形象绝不能这样就崩塌。退一万步说,这个表弟虽然给自己孤寂的生活带来一些慰藉,但天天埋头画一些奇奇怪怪的画,平时沉默内向,一激动起来手舞足蹈,像发了热病的疯子一般,全无成熟稳重的上等人形象,他手中只有画板和画笔,又哪里是自己倾慕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
所以,当有一天,梵高抱着一幅表姐的油画冒冒失失地跑过来,激动地说“凯,让我来爱你吧!我爱你好像爱我自己一样。我的生命,我的艺术都不能没有你”时,凯特别淡定,自己的回答也不出意料地决绝和冷静:“不,永远永远不,没和他结婚之前,我是个独身的人,而现在和以后的人生,我也将是个独身的人。”说完,扭头把惊愕的梵高留在原地。
整整三天,梵高把自己锁在房里,他脑海里不断回想着凯的那句斩钉截铁的“不行”,伤心的级别如海啸慢慢降为地震、台风再到涟漪,最终麻木不仁。他痴痴地望着堆满房间的画作,反复咀嚼着自己的悲切。他也终于知道了自己心痛的原因,自己不慕名利,只选择了一条孤僻的自我探索和表达的道路。在这条孤单的路上,他只想找到一个陪伴和知己,能够像提奥一样支持自己又能像母亲一样温暖自己。上一次求爱的失败已经把自己折磨得半死不活,见到凯后又滋生了对爱的渴望,才又活了下来。扼杀这段爱与杀死梵高无异,而刽子手正是他爱的表姐。
首战失利后,是鸣金收兵还是迎头直上?悲伤过后,这个问题摆到了面前。他面前又浮现出两个人在一起的画面,凯像母亲一样倾听,周身散发着圣母玛利亚般的光芒,而自己像个满足的孩子,灵感不断迸发。既然那么向往和她在一起的生活,那就听从内心的声音吧。虽然她发出了神情肃严的禁令,可是只要她还没接受别人,自己就没理由放弃。
想到这儿,梵高有了精神,从床上一跃而起。他要像骑士一样,去捍卫自己的爱情。兴致勃勃的他刚刚跑出房门,就看到搬运行李的工人正在把一个个行李箱往外运,而那分明是女性用品,心头没来由地慌了一下。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他语调瞬间抬了一度。
“凯表姐已经连夜搬回阿姆斯特丹了。她说这次散心的时间也挺长的,是时间回去整理整理自己的生活了。”安娜·卡本特斯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梵高后面,仿佛看穿了儿子的疑惑。
“为什么?为什么连和我打一声招呼都没有呢?她难道不知道我还在记挂着她吗?”
“孩子,你看不出来吗?凯就是在躲着你啊。你那么主动,快把人家吓到了,人家不走才怪呢。”
“吓到?为什么会吓到?我只是告诉她我的真实想法,我又不是什么歹徒匪类。”
“孩子,在你这个年龄,追求爱情是很正常的。我向你保证,以后我会带你多参加有社交名媛的聚会,咱们找个你喜欢的好好谈一场恋爱,不好吗?”安娜的声音带了一丝恳求,但更多的是关切。
“不,我根本不在乎其他名媛,我已然找到我的缪斯女神了,那就是凯。她温婉贤淑又大方可人,我真的不想错过她。妈妈,你帮我说说好话,帮帮我吧。”梵高是一如既往的偏执。
“帮帮你?哼,休想。你有没有站在我们的角度为我们想想?”母亲目光悲切,不发一言,只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从里屋走出来的父亲。父亲面色肃穆,语调满是愤怒和斥责:“凯身为你的表姐,本是你的长辈,又刚刚成为寡妇,你不觉得你们两个结合很下流,会玷污我们的清誉吗?”
“下流?真爱怎么可能会是下流?”
“真爱?是吗?我只看到你为她疯狂,没有看到回应呢?如果她爱你,就不会连夜收拾行李回去都不告诉你一声。不要执迷不悟了,这样只会破坏我们两个家庭的团结。”父亲挡在房间门口,冷静而犀利地质问着为爱痴狂的儿子。
听到这儿的梵高青筋暴突,气喘吁吁,犹如一头受伤的野兽,他的感情被怀疑,这使他觉得受到了侮辱。
“我的爱情在您眼中就是下流,我不能接受。我必须要忠实自己的内心,去追求想要的爱情。”
“好吧,如果你真的想去,就去吧。只是要记得,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代表我们家族的荣誉,请三思而行。而且,休想让我们承担你的开销。”了解儿子的母亲无奈地叹了口气,她知道梵高身上并没积蓄,想通过这种方式断绝他的念头。
“好了,我知道了,父亲母亲,开销的事情我会自己解决,我以后也不会打扰你们了。”平静下来的梵高裹着自己褶皱的大衣,收拾了行李就离开了家,把母亲的焦急和父亲的无力甩到了脑后。
在梵高的成长过程中,他的父母扮演着稍偏正统保守但对他关怀备至的角色,所以这次的激烈反对让梵高伤心不已。他决定搁置双方的争议,靠自己的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首先要先见到凯一面。但是最重要的是先要有钱。梵高的创作动力又被调动起来。他雇用模特,指导他们摆出姿势,用新的手法创造油画,把自己的创作源源不断地寄给提奥期望卖个好价钱。他也与表哥毛威取得联系准备去海牙学画,做好了离开家的准备。他兴致勃勃地努力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还是没有卖出去画,最后还是靠着提奥解决了路费问题。
梵高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巴黎,接受早已是艺术家、画作颇受认可的毛威表哥的指导。表哥对梵高的天赋和诚意赞不绝口,热情地送了很多工具和石膏要求梵高回家仔细提高临摹技艺。
在海牙学艺期间,因为惦念凯表姐,梵高去了几趟阿姆斯特丹,但凯早就闻风躲到其他地方,接待他的无一例外不是他亲爱的沃斯舅舅。这场拉锯战持续了很久,也因为斗争双方的力量和心态呈现出几个阶段。
一开始,沃斯舅舅对自己这个外甥气愤不已,他们僵持在客厅里,都不肯正眼瞧他。
“你走吧,她不想见你。”
“不,她不是不想见我,只是需要时间来接受。你们让我去看她吧。”
“我只是想见她一面,向她表达爱意,再争取争取。”梵高的表达不甘示弱,捍卫自己爱的权利。
“你为什么那么固执己见,即使她答应了你的请求,你到现在一幅画都没卖出去,以后怎么指望养活她和孩子?哪一个正常的父亲会放心把自己的宝贝女儿交给一个连正常稳定收入都没有,要靠弟弟来接济的男人呢?”
为了制止梵高,沃斯舅舅把心里的担忧毫无遮挡地倾倒出来,虽然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对这个虔诚绘画的孩子抱有好感。这更刺激了梵高敏感的自尊心。“是,我到现在是没卖出去一幅画,但这不代表我一辈子都一文不名,当一个男人有了爱人、有了家庭,他就会想着去工作努力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激动的梵高离开座位,挥舞着手臂,“让我去见她吧,你要知道恋爱带来的折磨和苦痛。”
这句话引来了沃斯更加尖锐的讽刺:“哦,你就这么敏感、这么脆弱、天天为了恋爱无病呻吟吗?我告诉你我承受的痛苦远远比你经历得多。”
沃斯的质疑又让他想起在矿厂时那些工人不屑的话语:“我们的生活远远比你的布道更为艰难,所以我们懒得去听你那虔诚的废话。”一时间,不被接受的委屈、指责一起涌上心头,他“噌”地站起来,把整个手掌放在烛台的蜡烛上,如十几只炙热的火舌舔着自己的掌心。“谁说我无病呻吟,我现在就在尝试着钻心的痛苦。”他低声嘶吼着,额头也因为疼痛和灼伤青筋暴突,但他愤怒和倔强的双眼却没有丝毫停下的意思。沃斯被梵高这突然的举动吓得不轻,停下了嘴上的挖苦,猛地一把打翻了烛台。叔叔知道,如果再僵持下去,这头倔驴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傻事,只好轻轻地说:“她现在不在家里,你过几天再来吧。”
也许是领教了梵高的坚持,沃斯发现硬的手段不行,第二次会面开始晓之以理,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当着梵高朗读起来。在信里他以一个牧师的口吻请求梵高恪守道德,克制自己的感情。但梵高还是不为所动。
后来的会面,他们采用了迂回和怀柔战术,一方面还是不肯让他见凯,另一方面放弃了犀利的言语,还是以一种亲人的姿态感化他。最后一次,在凯的住所等了一天而无所得后,梵高落寞地离开,走在无边的夜色里。头发花白的两位老人赶上来,再没有刚才的指责,而是满脸内疚和心疼。因担心梵高流落街头,两位老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蹚在肮脏、厚实的雪里,为他找了一个宾馆住下。看着他们苍老而蹒跚的背影,本来心怀怨恨的梵高心里仿佛被戳了一刀,认识到自己的偏执给两位老人带来了如许负担。
他知道,为了家庭和亲人,他也需要放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