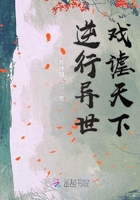这一天,在经略相公府做提辖的鲁达和朋友史进准备去喝酒。
两个人走在街上,忽然看见前面围着一群人,就到前面去看热闹。原来是史进的第一个师父打虎将李忠在舞弄枪棒卖膏药,他们就拽着李忠到潘家酒楼上喝酒。三个人喝了几杯酒,正谈得兴起,忽然听到隔壁的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地哭。鲁达便烦躁起来,把碟碗摔了一地,对店小二大喊:“俺来你酒店里喝酒,你却让一个哭哭啼啼的妇人来坏俺的心情?你说怎么办?”店小二慌忙上前赔罪,说:“提辖大人,千万息怒,这哭泣的人是这里卖唱的,他们不知道官人在这里喝酒。”鲁达一听,说:“这倒有些奇怪,快把他们叫来,俺倒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大工夫,一个六十来岁的老汉和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便来到鲁达面前。鲁达问:“你们是哪里人?为什么在这里啼哭?”姑娘带着泪痕回答说:“我们是东京人。我叫金翠莲,跟父母来这里投奔亲戚,可亲戚却去了南京,母亲病死在客店里,留下我们父女二人在这里受苦。这城里状元桥下有个杀猪的屠户,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他看我有几分容貌,就派来媒人,强要我给他做妾。文书上虽然写了三千贯钱,却是虚钱实契,一文钱都没给过我。我到郑官人家,受尽了他家大娘子的打骂,不到三个月就被赶了出来。郑大官人非但不管我们父女二人,还反要我们还那从未给过的三千贯典身钱。他是财主,财大气粗,我父女二人身单势孤,哪敢跟他争执?就只好到酒楼上卖唱挣钱给他。这两天没有几个来喝酒的,没挣到钱,眼看郑大官人就来讨钱了,可我……”说着,那妇人又嘤嘤地哭了起来。
鲁达听到这里,血气上涌,怒发冲冠,“啪”地一拍桌子,就要去找那个郑大官人算账。幸好史进、李忠二人拦住,鲁达才暂时消了气。鲁达给了金家父女一些盘缠,让他们先回老家,然后再找郑大官人算账。
第二天,鲁达就去找郑屠。这时郑屠正在柜台内坐着,看着那十来个刀手卖肉。鲁达走到郑屠面前,大叫一声:“郑屠!俺奉小种经略相公的命令,来买十斤瘦肉,不许带一丁点儿肥的,要细细地切成肉末,还得你亲手切!”
郑屠一看是鲁提辖,哪敢怠慢,慌忙走出柜台,殷勤地答对。郑屠亲自操刀,切完用荷叶包好了,问鲁达:“提辖,小的叫人送去吧?”鲁达说:“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见一点儿瘦的在上面,也要切成肉末。”
郑屠虽然心里犯嘀咕,但也切了,切完也用荷叶包好。这二十斤肉末整整切了一早晨。
鲁达又说:“再要十斤寸金软骨,也要细细地切成末,不要见一点儿肉在上面。”这次,郑屠觉出了不对,笑着说:“提辖不是故意来捉弄我的吧?”鲁达听了,腾地跳起来,喊道:“俺就是故意来捉弄你的!”说着就把两包肉末劈头盖脸地向郑屠砸去。
郑屠再也受不了鲁达的捉弄,从肉案上拿了一把剔骨尖刀,忽地跳了过来。他右手拿刀,左手过来揪鲁达。鲁达就势按住了他的左手,往小腹上只一脚,就把郑屠踢倒在街上。
鲁达又上前一步,踩住他的胸脯,提起拳头对着郑屠说:“你一个卖肉的屠户,竟然敢强抢民女,今天俺就要让你知道什么才是镇关西!”说着,便“噗”的一拳打在了郑屠的鼻子上。郑屠脸上顿时鲜血迸流,鼻子歪在了一边。
郑屠挣不起来,把尖刀丢在一边,嘴里却喊道:“打得好!”鲁达大骂:“你这个畜生,还敢还口!”提起拳头来,又朝眉梢打去,打得郑屠眼角裂开,眼珠迸出。郑屠疼得嗷嗷直叫,只得向鲁达求饶。
鲁达喝道:“你这个屠夫,你要跟俺硬到底,倒有可能饶了你,你讨饶,俺就偏不饶你!”说着就势又一拳,正打在郑屠太阳穴上,打得郑屠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只有出的气,没了进的气,一动不动。
此时,店小二和围观的百姓都吓呆了,谁也不敢劝阻。鲁达眼看郑屠的脸色由紫变青,由青变黑,心里琢磨:我只想痛打这家伙一顿,好好教训教训他,不会真的把他打死了吧?俺为了他吃官司,又没人给俺送饭,不如一走了之。想到这里,鲁达就指着郑屠的尸体说:“你这个畜生,还敢跟俺装死,等俺慢慢儿跟你算账!”一边骂,一边大踏步走了。
鲁提辖知道事态不妙,回到住处,急忙卷了些衣服、银两,提了一条齐眉短棒,出南门一溜烟儿地跑了。
鲁达几经周折,到了雁门县的文殊寺。文殊寺长老收留了鲁达,并给他剃了度,赐法号为智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