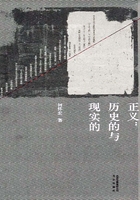在道德实践活动中,外在必然性对意志自由的限制主要通过如下两个途径而体现:
其一,当历史条件、社会环境还未提供道德意志选择的客观可能性时,道德主体就不能对行为进行“要”或“不要”的自由抉择。特别是当人类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惘然无知或知之甚少时,道德的自由永远是不可能的。
其二,当人们在进行道德自由选择时,由于选择了“恶”或不道德行为时,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必然之则便会通过外在的社会舆论和主体内心的良心这一道德心理机制从而限制道德主体的自由。所以马克思曾这样给自由下过一简单的定义:“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
(3)道德是主体在自由和必然之间进行选择的一种活动。道德活动具有人类一般活动中自由与必然关系中的一般特征。因而恩格斯认为:“如果不谈谈所谓意志自由,人的责任,必然和自由的关系等问题,就不可能很好地讨论道德和法的问题。”
自由人性中的意志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争取道德自由的能力。人们既可以正确地使用这种能力,以它为中介达到道德人格的理想境界,也可能滥用这种能力,把任性地表现这种能力当作“自由”从而成为自己恶劣情欲的奴隶。从表象上看,当个人把历史必然性、把社会需要、把对行为后果的责任弃置一旁,任凭自己一时的好恶进行选择时,这种我行我素、随心所欲的表现似乎十分自由,然而这种自由却是一种毫无规定性的、主观的空虚自负。
黑格尔批评过这种虚假的自由:“通常的人当他可以为所欲为时就信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但他不自由恰好就在任性中。”事实上,道德主体在这里恰恰是最不自由的,因为他不自觉地沦为自己恶习、情欲的奴隶,从而必然导致道德情操和人格品性的堕落。
网络被现代人视为最自由表达意志的天地。但是,这个领域里的自由同样是受限制的。譬如美国学者派卡·海曼就将黑客(hacker)的伦理限制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工作伦理。尽管黑客不是根据常规化的工作,而是根据创造性工作与生活中其他激情之间的动态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而且黑客视工作为激情和自由的融合,但他们依然有自己的工作底线不予逾越。
二是金钱伦理。黑客们不是把金钱本身视为一种价值,而是把它视为实现社会价值和开放性目标的行为动机,黑客渴望与他人一起实现激情,渴望为社会创造有价值的东西,因此获得同行的承认。三是网络伦理。它体现着黑客伦理的主动性,即主张行动中的自由与保护别人生活方式隐私的一致性,同时竭力让每个加入网络的人从中受益。恩格斯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
道德自由也同样无法摆脱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道德自由就在于对道德规范的必然性进行认识并依这个认识而行动。在这个过程中,道德主体是否自觉地认识和把握道德必然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获得道德自由的认识论前提。没有道德主体对道德规范必然性以及作为这些必然性展开的诸如群体和个体关系,社会发展的需要与自我发展的需要等关系的正确认识,即便社会历史提供了最大限度的道德选择自由,道德主体往往也要惘然不知所措,根本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道德自由的获得固然须对道德必然性的认识为前提,但又不能停留在认识阶段。显然,正确的认识只为自由提供理论上的可能性。要使自由获得直接的现实性,就必须在认识必然性的基础上发挥自由意志,通过道德实践中的积极选择,塑造和完善自己的人格,不仅越来越不为过去的坏习惯或情欲所统治,而且也日益摆脱“偶然的意志”、任性和冲动的驱使。只有这样,道德主体才真正获得现实的自由,开始使自己的道德活动在实践中走向“自律”的境界,亦即走向孔子声称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理想境界。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道德从必然走向自由,从外在限制走向“自律”,这其中意志自由的正确理解、体认和发挥是关键。因为道德主体对社会历史条件的认识和利用,以及最终实现超越现实的“从心所欲”,都是在意志自由的一系列勉力而行的努力下才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意志自由就没有道德自由。
也就是说,要正确地把握道德主体的自由人性问题,不仅要看到道德主体意志自由是以认识必然为前提的,同时还要看到在实践选择的过程中,意志自由也必须处处遵循这种必然性。在意志自由的选择过程中,道德必然性往往以道德责任表现出来。所以自由与责任(responsibility)不可分。自由应该被理解为可负责任的状态。自由包含责任,责任体现自由。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可以认为,道德自由的境界同时也是对行为高度负责的境界。
具有意志自由的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的自由选择中同时要选择道德责任,这是人的主体性的内在标志之一,也是道德主体不能轻松自在地在道德之境漫游而注定要背负重荷的原因。当然,行为主体对道德责任的负责,又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个“度”是由客观条件所提供的选择性,以及由社会道德关系规定道德主体应履行的具体义务决定的。否则,道德责任又会沦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而迫使道德主体丧失自由。
最终的结论就是,道德的自由选择是人类道德活动的主旨。每个人都是道德选择的主体,善或恶都是人运用自己的意志进行自由选择和创造的结果。人通过选择实现自己的自由人性。人正是在道德的自由选择中,从而也是对道德必然性的认识和实践中不断实现自己的道德价值,并从中体验到自己生命中“善”的蓬勃生机的。这就正如歌德所说的那样:只有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才有权享受生活和自由,也才体验到人的目的。
3.自由人性和道德规范必然性的关系问题之所以成为伦理学基本问题的根据
道德领域里涉及从而也是伦理学理论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是众多的,譬如善与恶、道德与利益、利他与利己、个人发展的权力与对他人对社会的义务、集体与个人、实有和应有、道德与社会历史条件等等关系问题,都在伦理学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之所以把道德选择中自由人性或称意志自由和道德规范必然性的关系问题视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有着内在的理论根据的。这个根据大致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人性中的意志自由与道德规范必然性的关系问题是道德活动的逻辑起点。只要认真考察一下人类的道德生活实践,便可以发现道德活动存在如下两个基本的前提:
其一,人的意志是自由的,道德主体具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和权力。否则,如果一切都是必然的,人别无选择,那么由于在这种情形下道德主体只是一种必然性的奴隶,其活动也就丧失了道德的意义,因此社会和他人也无法对这种活动进行道德评价,因为既然行为主体别无选择,自然他也就不负任何道德责任。
其二,人的意志自由又不是绝对的,如果一切都可以为所欲为,没有必然性的约束和限制,那道德也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因为道德本身就是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才拥有其存在价值的。人如果可以不要任何规范的约束和限制,那么道德、法的规范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可见,自由与必然的一般关系具体化为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和规范的必然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后,对这一关系问题的正确解决构成伦理学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出发点。
(2)人性中的意志自由与道德规范必然性的关系问题也贯穿于道德意识、道德关系和道德实践的始终。道德意识事实上是主体对道德规范必然性的认识和了解,并内化为主体自身的信念的过程;道德关系本身就是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与必然性关系的一种社会化;道德实践则更是道德主体在认识道德规范必然性基础上的一系列自由选择的实现。道德选择作为一种德行的实践活动使道德意识得以真正的对象化,使道德主体的人格理想现实化。这就正如亚里士多德说的:“一言一行……如要明白表示某种抉择,人物就有‘性格’,如果他抉择的是善,他的‘性格’就是善良的”。
(3)人性中的意志自由与道德规范必然性之关系问题的最终解决,也构成道德理论和实践的逻辑归宿。道德是属人的,也就是说道德活动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其最终目的是培养和造就全面自由发展的理想人格。
这种理想人格作为一种道德理想,事实上就是指达到一种人能最大程度地实现的自由人性,从而使自己获得全面发展的生命境界。这种理想境界的实现无疑是与意志自由和规范必然性关系问题的正确解决直接相关的。同时,这一关系问题的深刻而完善的解决,也就是道德上理想人格的真正实现。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把道德自由看成是人所能获得的最深刻的自由之一。与人能获得的其他自由相比,道德自由尤其是建立在人对自然、社会和自我本性的认识这样一个基础上,并因对其有效地实现了驾驭,从而不断地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不仅如此,人性中的意志自由和必然性关系问题也规定和制约伦理学中诸如善与恶、利己与利他、个人和集体等等关系问题的解决。而且,它往往也还成为伦理学不同流派划分的一个基本标准。譬如唯心主义的意志论伦理学无疑是过于夸大了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忽视了自由背后的必然性限制;机械决定论的宿命论伦理学则又无视人在受必然性限制的同时也还有意志的自由选择这一基本事实的存在。这一切都表明人性中意志自由和道德规范必然性的关系问题构成道德和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二、自由人性与必然规范:历史与现实的考察
人性中的意志自由与规范必然性的关系问题,也是伦理思想史和现代伦理学理论所一直关注和探讨,并在道德生活实践的历史与现实中普遍涉及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这其中,人们从理论和实践的不同角度对自由人性中的意志自由和道德规范必然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大量的探索。它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把握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与现实的材料。
1.自由与必然问题的伦理思想史考察与评析
在古希腊时期,最早的一些伦理学家们便已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并初步探讨了道德自由与客观必然性的关系问题。譬如赫拉克利特就把“逻各斯”(即必然规律)视为伦理的普遍原则,认为人应服从普遍的必然性,只有服从“逻各斯”命令的生活,才合乎伦理道德。所以他认为道德就意味着认识和服从“逻各斯”的必然性,即严于律己克制情欲。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更是在《伦理学》一书中,精辟地论述了道德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
他认为伦理学的任务就是认识必然,控制情欲,把自我和自然(即“实体”)统一起来以获得自由,从而达到人性的圆满和个人的永恒幸福。在他看来,人的理性只要能认识必然就将不受情欲和本能的支配,从而自然规律和必然性对人也就不再是消极的约束。一旦人们意识到这种必然性的约束是积极的、必要的,那么人也就摆脱了命运的宰割,达到自由和“至善”。
除了上述思想家以外,西方伦理思想史上诸如霍布斯、拉美特利、霍尔巴赫等人对道德的自由与必然性的关系问题也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他们一般地也都认为意志自由无条件地受决定于客观必然性的制约。这些思想无疑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至少证明了人的道德自由是受必然性限制的。
康德在自由与必然问题上可谓达到德国古典哲学的高峰。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了三大理性命题:其一是精神自由。康德所说的自由是指理性的自由或精神的自由,因此康德把自由范畴与自然范畴相区分,认为自由是一个原因性的理性概念,它关联着人的自由意志的决定。其二是意志自律。康德认为:“纯粹实践理性的最高形式原理就是意志的自律原理。”其三是良心自觉。在康德看来,良心是作为理性存在的人本来就具有的东西,它就是人的善良意志、义务意识、内心法则,就是人对普遍道德律的绝对尊重。因此,康德很自然地把良心自觉看作是精神自由和道德自律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
然而,无论是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还是近代的斯宾诺莎、康德等人,都陷于一种机械决定论的泥潭之中。他们事实上把自然界现象被必然性所机械决定和人性中的意志自由与必然性的相互制约性混为一谈。所以在他们的理解中,人的行为或者就像行星的轨道那样是被预定的,或者是被先验的善良意志所绝对命令的。正是鉴于这种机械决定论的错误,在尔后的西方伦理思想史上才有了对自由与必然性关系问题的唯意志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