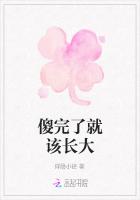二十五、在国共合作中明方向
陕北的炎夏,顶着烈日的庄稼像疯了一样生长。
漫山遍野的苞谷、粟苗、地瓜,绿油油的染得整个原野春色一片。
羊群东一处、西一处地游啃地面,像黑白棋子在绿色的棋盘上移动。
沟这边有牧羊的小伙子在与沟那边的姑娘以歌传情:
山丹丹里那个开花哟,
红艳绝,
咱们中央啊红军,
到陕北,
…………
一九三七年七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
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史称“洛川会议”)。这是在全国抗日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凯丰出席会议。凯丰、彭德怀、邓发、林育英(张浩)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一说凯丰)、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任委员。毛泽东任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萧劲光任参谋长,杨尚昆任秘书长,任弼时兼政治部主任。
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实行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改良人民生活,实行抗日外交政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抗日的教育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这个纲领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它所阐明的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为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指明了方向。
十一月二十九日,王明、康生、陈云从苏联回到延安。
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王明、康生、陈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张国焘、凯丰、林伯渠等。
年轻气盛的王明,在十二日会上,以激情四射的口气,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日与争取抗战》的报告。报告特别提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并强调: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要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给养。在军事上,他主张打阵地战,主张集中,将我们的部队编成正规军,和国民党军队一起上战场打击日本,进一步说就是保卫苏联。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与会人员感觉王明的报告与洛川会议精神显然不同。但得到多数人的赞同。这是因为王明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回国的。回国前,他又受到斯大林与季米特洛夫的接见。他的讲话是代表共产国际的意见;而另一方面,也确有一些军事干部对洛川会议中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原则抱有不同的看法,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张把运动战与游击战结合起来,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几个胜仗,这样既可以振奋我们的斗志,又可以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影响。这两种思想都促使不少人同意王明的观点。可见这些人没有正确估量形势。我们只有三万军队,配合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去打阵地战,这支军队能打几次仗?再说,如果跟着国民党军队大溃退,我们既无后方,又无根据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毛泽东后来在七大会议期间评价十二月会议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况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削弱独立自主呢?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呢?”
王明的报告没有形成正式决议。
会议决定成立“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凯丰被确定为二十五名筹委会成员之一。
会议根据南京失守,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重心转至武汉的情形,加上蒋介石的邀请,决定由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武汉,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由周恩来、秦邦宪、项英、董必武等领导南方的工作。
十二月十八日,与国民党谈判结束后,蒋介石希望王明“在汉相助”。
经中央同意,王明留在武汉。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合为一个组织,叫中共中央长江局。长江局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凯丰前往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同时兼管湖北省委工作。
在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原日租界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口办事处四楼的大石洋行,成了中共长江局机关的办公处。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危难的时候,在国共两党既联合又斗争的时候,在与王明右、“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身处长江局的凯丰,始终维护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尽管当时长江局的书记是王明,但在副书记周恩来的实际领导下,凯丰和秦邦宪、董必武等长江局领导,按照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做了大量工作。长江局的主要工作任务是:
一、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同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开展对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工作和国际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工作;
二、领导南部各省党的工作,迅速恢复党的组织,积极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三、做好新四军的工作,独立自主地准备与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同时推动和帮助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积极作战。
按照任务规定,长江局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挫败了蒋介石的“溶共”政策,反对国民党的投降活动,巩固和扩大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恢复和重建了在大革命中破坏十分严重的南方各省的党的组织,吸收了大量先进分子入党(一九三七年九月到一九三八年九月,在河南、安徽、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江苏、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广东十三省,党员发展到六万七千七百八十人(军队党员未包括在内),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七,加强了各地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领导和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支援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青年知识分子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指导完成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广泛开展华中地区敌后游击战争;全面开展了统战工作,争取国民党将领以及地方势力,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统区内组织了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等各种抗日团体,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了抗日救亡运动。
作为长江局的宣传部部长,凯丰说:“宣传工作在抗战中的作用已为抗战的实践所证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对抗战的“宣传工作无论对国外或对国内都做得不够,没有充分地使用宣传的武器,没有充分发挥宣传工作的效能。中国的抗战是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自卫战,是保卫祖国和保卫和平的自卫战、正义战,因此中国人民是站在理直气壮的方面,更能把握客观的真理和事实来发挥宣传工作的效力。”
凯丰和周恩来、王明、秦邦宪一起,在同蒋介石谈判中,经蒋介石“完全同意”后,争取到了创办一份新报—《新华日报》的权利。《新华日报》组建后,由王明任党报委员会主席,报馆设立董事会,成员是王明、秦邦宪、董必武、吴玉章、凯丰、邓颖超。《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一张公开出版时间最长的大型机关报。它在山西、广州、重庆、西安设立分馆。在长沙、郑州、潼关、洛阳、宜昌、黄陂、南昌设立分销处,销量最多时达三万多份,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作为一张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新华日报》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和反对国民党的投降活动,动员全国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战争上起到了重大的号召和鼓动作用。
凯丰作为党报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了《新华日报》的采编、出版、发行工作。凯丰对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指出说:“我们必须利用每一个具体的事实来做宣传材料,应当在一切文字的或口头的宣传上,揭露日寇一切的残暴兽行,激发每一个中国人对日寇侵略者的民族仇怨;用革命仇怨态度来教育每一个中国人去对付日寇侵略者;发挥中国抗战中每一次英勇事迹的教育作用,激发每个中国人的民族热忱;用忠实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来教育每一个中国人,使他们抱定为保卫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决心,使他们抱定中国抗战必定胜利的信念。”
由于《新华日报》缺少强有力的编辑人员,在范长江的介绍下,凯丰得知陆诒能够胜任编辑工作,凯丰就和秦邦宪、潘梓年、华西园在普海春餐馆找陆诒面谈,请他担任《新华日报》的编委兼采访科主任。陆诒曾在几个报社担任过外勤记者,但不了解“编委”是什么意思。凯丰、秦邦宪一一向他解释:我们通过党组织来领导报纸工作,具体地讲,党组织领导编辑委员会的工作。编委会是报社内部的集体领导机构,每个编委都是集体领导成员之一,不论党内或非党人员,只要参加报社工作都是报社的主人翁。我们这里没有老板和伙计之分,办报靠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的集体努力,还要依靠广大读者和通讯员的支持,就是这一点与其他各报有所区别。
凯丰还对报社同志讲,我们过去有过办秘密报刊的经验;在十年内战时期,也在苏区办过报刊。现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要办一张公开发行的报纸,大家都没有经验。没有经验不要紧,经验从实践中来,我们可以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我们共产党人对不懂的事情就要学习,只要我们发奋努力,在实践中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新华日报》出刊后,在国统区引起了广泛而巨大的反响。一星期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贺衷寒,受曾经的中共党员、后叛变成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叶青的调唆,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下午四时三十分,指使数十名暴徒,手持铁棍、利斧闯进报馆,割断电线,捣毁物件,推倒排字架……企图阻止《新华日报》的继续出版。
长江局对此作出强烈抗议,并电告蒋介石,请他设法制止。
周恩来、叶剑英和凯丰等分别专访了国民党党政军要员,要求采取有效办法,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凯丰依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周佛海就职时所提出的“以民族精神对抗强敌,以民主制度集中国力,以国防计划建设经济,以科学原理健全思想”的“四个原则”,前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与周佛海严正交涉。他指出:“……如果不及早设法调整,将要妨碍抗战宣传工作的进行。”
凯丰还将近来《新华日报》被捣和全国各地不少进步报刊被查禁等情况,对周佛海进行了通报。
面对凯丰的到来,和出具的暴徒的确凿罪证,周佛海佯装不知地说:“凯丰先生,有这种事,会不会是亲日分子挑拨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
凯丰说:“如果不信,周部长可以派人调查。”
周佛海说:“调查当然会进行,不过……”
凯丰不容周佛海闪烁其词,指出:“……自抗战爆发以来,有人以为对理论的研究将会失去它的地位,但是恰恰相反,理论书籍的销路反倒激增起来。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抗战的环境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激烈变化,以前不问国事的人现在都被战争的炮火所惊醒,使他们不得不问政治;平时注意政治的人们,现在对于一切事物不能不求进一步地认识。对这种现象,国民政府本应求之不得,怎么反过来还要对政治书籍进行查禁呢?你这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说出的‘四个原则’摆在那里,不能会上说一套、背后做一套吧?”
周沸海脸红如煮虾,却仍继续装聋扮哑说:“凯丰先生,你反映的情况我真的一无所知。如果查清中央和地方确实存在以上问题,我马上纠正。”
凯丰说:“光纠正还不够,我认为必须作出一个明确规定,将全国有利于抗战的言论和文章都充分讲出来、登出来。”
周佛海问:“你认为这个规定要表述哪些内容?”
凯丰说:“第一,应当确定,凡是不违背三民主义的原则和不违背统一团结的书报,均应予以发行和出版的自由;对于学术的研究,凡是为国内或国际上公认的学说,譬如科学社会主义,已成为全世界所公认的一种学说,应当有研究的自由。
“第二,在组织上,应当统一书报的检查。近来检查书报既无一定的组织,又无一定的标准,甲机关可查禁书报,乙机关也可查禁书报。这种现象,当然不是有组织的现象。中央不查禁的书报,而地方又要查禁,这样使言论出版也如像遭受‘关卡厘金’重重障碍。因此必须有统一的书报检查机关,查禁书报应当归统一检查机关负责。凡中央不查禁的书报,应当在全国各地通行,不得受到查禁。
“第三,确定书报检查与着作人发行人的关系。凡被查禁的书报,应当通知着作人发行人,指出被查禁之理由,使着作人发行人能依指出之理由加以更正重新出版,或查禁之理由不适当时依法申辩。……”
在凯丰的强烈要求下,周佛海无言作对,最后不得不松动进步报刊、书籍的出版。
这一松动,使我党抗日主张在国统区得以迅速传播,并使之深入人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长江局工作期间,凯丰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根据时局的变化,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日撰写了《抗战中的宣传工作》,一九三八年九月十日撰写了《保卫武汉中动员民众的几个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撰写了《动员全体人民参加抗战》等文章。这些文章,大都刊载在《解放周刊》上。文章对宣传我党抗战方针、政策,宣传毛泽东《论持久战》等着名文章起了很好的作用。
凯丰在《动员全体人民参加抗战》一文中说:“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中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胜利是属于中国。他说:‘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与政治组织力量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与政治组织力是较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与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与人民是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与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与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与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与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这一真理已经逐渐地为各方面所认识,为各方面所公认。这正成为是我们今天能够更好地发展民众运动与动员全体人民参加抗战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