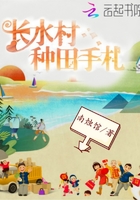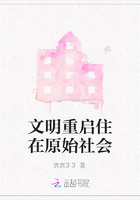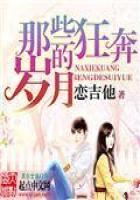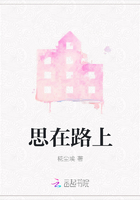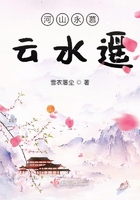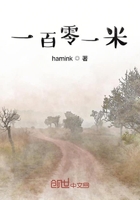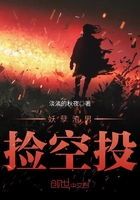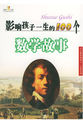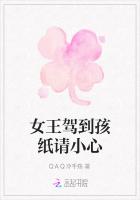我是80年代中期一代。祖孙三代修铁路。
外公和爷爷、爸爸和妈妈,加上我,三代铁路人。
记得小时候爸妈常年驻守工地,我只能跟着外公一起生活,由外公照顾我的日常生活,送我上学。对幼时的回忆,往往首先浮现在脑海里的是红砖砌成的家属大院,斑驳的院墙,对列大院路两旁的低矮瓦房,以及每家每户门口冲刷得干干净净浅浅的排水沟。
大院里住着很多和我一样跟着爷爷奶奶或是外公外婆生活的小伙伴,无一例外都是父母驻守工地,偏偏小孩子又到了上学年龄必须得送回城里来上学。父母只得求助于他们的父母,结果就变成了大院住着一帮老老小小,几乎见不到什么年轻人。
我被爸爸妈妈送回大院的时候还不到四岁,之前一直跟着他们住在位于重庆的工地驻地好几年。80年代的铁路工程,不像现在,有各种大型机械配合施工。那时所谓的铁路职工,干的活和现在工地的农民工干的活一模一样,甚至更累,更辛苦。所有的活全靠人力肩扛手抬,就算有机械配合,也只有小型机械。类似于配个混凝土搅拌机之类的,因此往往一个几百万到一千万的工程,都会持续施工好几年。在被送回成都之前,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我就一直跟着父母在工地。身边接触更多的,不是爷爷奶奶,舅舅姑姑,而是爸爸妈妈的同事。这个叔叔,那个阿姨,还有爸爸的师父,妈妈的工班班长。身边的小伙伴也是隔壁叔叔阿姨家的孩子,加上正好是独生子女一代,特殊的成长环境造成了我幼时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觉得我家就我爸妈加我三口人,再没别人。那个时候更没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概念,总觉得自己的亲人就只有父母。这个观念一直到后来被送回成都之前才被父母注意到,纠正过来。
现在回想起来,跟着父母在工地的日子全是美好的回忆。早上被妈妈叫醒起床,给我洗漱穿衣服,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能闻到食堂传出来的早餐的味道,淡淡的米粥香味,还有蒸馒头的甜味。等收拾差不多了,爸爸也把早饭从食堂端回来了。吃饭一般是在外间爸爸的办公桌上吃的。办公桌表面铺了一层玻璃板,凉丝丝的,饭碗放上去之后,爸爸还要把账簿和算盘挪到一边,再把馒头从盛粥的饭盆上端下来放到旁边,等我磨磨蹭蹭爬上木头条凳蹲好准备吃饭的时候,爸爸已经提前给我盛好了小半碗白粥,递给我掰开并夹了泡菜或是沾了白糖的小半个馒头。那时候的我也才2、3岁,记忆中食堂大师傅做的馒头个头真大啊,爸爸掰给我一小半最多只占整个的三分之一,就能让我吃到小肚肚感觉到撑,可是爸爸却能吃完两个,感觉爸爸可真是厉害。
往往不等我吃完早饭,妈妈所属的工班就要开始点名了。天气暖和的时候,我爱跟着妈妈去点名。等一帮叔叔阿姨都排队站好之后,我就站在妈妈旁边,小小的一只,站在那里还没有旁边叔叔阿姨们大腿高,努力的抬头望着面前正在点名的工班长叔叔,认真的听着工班长叔叔嘴里点到的名字,等到听到妈妈的名字的时候,抢先帮妈妈答:到。这个时候往往就会引来身边一阵善意的笑声。那时的我不明白这些笑声的含义,直到很多年后,当我某一天早上站在空地上,听见自己同事的孩子奶声奶气的帮自己妈妈答到时,内心瞬间闪过的那抹柔软,才真的体会到当年妈妈同事的心情。那是对这些跟着父母在工地上成长的孩子的疼爱以及心疼。
像我这样幼年跟着父母在工地上长大的孩子在当时不少,加上一个工地干的时间又长,动不动就好几年,因此当时项目上有自己组办的托儿所。请的年轻,有耐心又相对有文化的职工当老师,就在项目驻地挑选几间宽敞明亮的屋子当教室,父母上班之前先把小朋友送到托儿所,中午可以接回去,确实特别忙顾不上的时候,早上送去的时候就给老师打个招呼,等到下午忙完之后再去接小朋友回家都行,期间老师会根据父母告知的接孩子时间,安排好小朋友的午饭、午睡、或者是晚饭等生活杂事,甚至有时候不碰巧,父母两个人都出差,那就走之前把孩子衣服收拾好,一起送到托儿所去。可是相比城市里正规的幼儿园,这种托儿所教的东西就相对比较基础又少,相反,在我留存不多的幼时印象中,反而是我爸爸对我的早期教育插手的更多一些。因为我父亲属于后勤管理部门,只需要在办公室办公,大部分时候我都是吃午饭之前就被接回家了。等妈妈下班一起吃饭,等到午睡之后起床,就是我和爸爸两个人的工作、学习时间。
现在能回想起的往往是仲夏的下午,睡过午觉起来,妈妈已经上班去了,只有爸爸在外间办公室做着他的工作。我穿着自己的小拖鞋,踢踢踏踏的爬上爸爸对面的长条凳,跪在上面伸手去够爸爸的茶杯,揭开盖一口气把爸爸凉好的绿茶一口气喝干净,耳边是爸爸带笑的声音:“你怎么又把茶母都给我喝干净了。”
喝完水,自己去翻放在小抽屉里的作业本,爸爸给我排好字头,先写一整篇的小字,写完之后休息一会,再做一大页的加减法算术题。这个安排从我三岁开始一直持续到我被送回成都,每天如此。遇到爸爸不忙的日子,小字挪到上午,下午还能跟着爸爸在报纸上学写毛笔字。小孩子的思维估计是大人不能理解的,那会儿的我最讨厌的就是每天拿着铅笔写小字,却非常开心能拿着毛笔写字。完全没有觉得这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同一件事。就因为这个爱好,长大后才醒悟过来,年幼无知的我当时不知道被我父亲用毛笔字这一招套路了多少写字的时间。然而,尽管如此,我的一手硬币字在上中学之前依旧被评为我家除开我妈之外最丑的字。
我在写作业的时候,爸爸就坐在我的对面,手边放着一把大算盘,要么做账、算账,要么做他其他的工作,期间还会有来办事的叔叔阿姨,进进出出来来回回,最开始我还会被他们说话吸引走注意力,等到几次一直到妈妈下班我还没写完作业,消耗掉原本属于自己下午和小伙伴玩的时间之后,我就再也不愿意搭理那些叔叔阿姨们了。只会埋头认真写作业,满脑子的赶紧写完出门玩的念头。
写完作业之后,第一件事交给爸爸检查不算,还要挨个改完错才能完成当天的学习。眼巴巴的等到爸爸检查完所有作业往往都四点多了,太阳也没有中午那么晒,爸爸就会对我说“行吧,你去玩吧。”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会飞一般的跑出房门,直奔小伙伴家里,呼朋唤友的集结起来满驻地的疯跑。有时候运气不好,飞奔到小伙伴家里的时候,小伙伴自己的作业还没完成,两个小豆丁就会自以为隐秘的在父母眼皮子底下作弊,我帮小伙伴算后面的算术题,或者帮她检查前面有没有做错的地方。两个人想尽一切办法缩短时间,力求尽早组队去玩。
长大后说起来那段时间,父母常常会说,那会儿驻地虽然面积大,空地多,可是其实并没有什么可以玩的。我们一帮小伙伴往往也只能是从食堂前面的一大片草丛疯跑到后面的篮球场捉迷藏,过一会儿又从篮球场风跑到草丛去捉蜻蜓之类的,连个能玩的球都没有。见得更多的,可能是工地用的材料,配件,各种工具还有办公室成堆的资料,捉到一个蜻蜓或者蚱蜢,好几个小朋友能凑一起有滋有味的玩好久,在父母看来,真的是可怜死了。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却觉得那段时间是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候。每天父母都在身边,还有许多小伙伴一起玩,幼儿园的老师既是老师,又是熟悉的阿姨,食堂的叔叔也是经常在办公室能见到的叔叔,还有许多伯伯、爷爷、奶奶,每个人见到我们这帮小孩儿都是带着亲切的笑容,整个驻地都是我们的探险场所,无忧无虑的过每一天。
等我们这帮小孩跑完几圈,慢慢能闻到一点食堂传出来的饭菜香时,差不多就到了工班下班的时间。陆陆续续就会看到有扛着铲子,或者其他各类工具的叔叔阿姨往宿舍区走。这个时候一帮小孩子就会快跑着往下班队伍的后面跑去,一边跑一边寻找自己的父母。发现自己爸爸妈妈的时候就会飞奔而去,洒下一路带着欢笑的呼喊”爸爸!爸爸!!“或者“妈妈!妈妈!”。那种欢欣雀跃的语调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而我也曾经是这些小伙伴其中的一员,张开双手,大笑着开心的扑进我母亲的怀里。
记忆里的那段日子,整个都照耀在重庆仲夏的阳光之中,呈现出一种桔黄色的暖洋洋的感觉。家门口野地里长出来的芭茅花以及停在上面的各种颜色的蜻蜓,还有我吵着让爸爸妈妈种的向日葵,都在临近傍晚的夕阳之下随着微风徐徐摆动,组成了如今我对那段生活的全部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