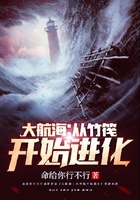“多可惜啊,埃莉诺,”玛丽安道,“爱德华对绘画居然没什么鉴赏力。”
“对绘画没有鉴赏力,”埃莉诺回答道,“你怎么会这么想呢?诚然,他自己并不画,可是他非常喜欢观看别人画画儿,我可以向你保证,他绝不缺乏鉴赏的天资,只不过没有机会去改善和增强罢了。他要是学过绘画的话,我相信他会画得很好的。他在这方面太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了,总是不愿意对任何画作发表意见;不过他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朴实而又得体的趣味,一般而言总能引导他做出完全正确的判断。”
玛丽安怕惹姐姐不快,在这个话题上就没再说什么;不过埃莉诺所描述的那种在他内心所激起的对于别人的画作的赞赏之意,却远远还未曾达到欣喜若狂的地步,而在她看来,唯有达到这样的程度,方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鉴赏力。不过,尽管在心里面暗笑姐姐的误解,她又很尊敬姐姐对于爱德华的盲目偏袒,她的误解正是由此而产生的。
“我希望,玛丽安,”埃莉诺继续道,“你不至于认为他连一般的鉴赏力都不具备。确实,我想我是可以说你绝不至于,因为你对他的态度是十分热情友好的,如果你对他真有那种看法的话,我敢肯定你待他就不会那么客气啦。”
玛丽安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她无论如何不想伤害姐姐的感情,可是又决不能言不由衷。最后她这么回答:
“你可千万别生气,埃莉诺,如果我对他的赞扬与你对他的优点长处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的话。我不像你,有那么多的机会去估量他在思想、倾向和趣味方面的细微癖好;不过我对他的善良品性和理性见识有最高的评价。我认为他是个非常值得尊敬而又和蔼友善的人。”
“我敢肯定,”埃莉诺面带微笑地回答道,“像这样的揄扬,就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听了都不会感到不满意的。依我看来你对他的赞赏是再热诚也没有了。”
玛丽安很高兴发现她姐姐这么容易取悦。
“说到他的见识和善良,”埃莉诺继续道,“我想,凡是经常跟他见面、同他毫无保留地交谈过的人,谁都不会有任何怀疑的。他那卓越的理解力和原则操守,只是因为为人腼腆使他过于沉默寡言,这才无从彰显。你对他有足够的了解,能对他那实实在在的价值做出公正的评判。不过对于那些你所说的细微的癖好,由于一些特殊的情况你对他没有我那么了解。他和我经常能单独待在一起,而你则全身心地沉浸于妈妈最慈爱的包围中了。我跟他见面的次数多,细细地考究过他的思想情感,认真听取过他有关文学与审美方面的见解;总的说来,我敢断言,他的头脑博学多识,他对阅读的爱好超出常人,他的想象力自由活跃,他的观察能力公正而又准确,他的审美趣味精雅而又纯正。他在各方面的能力就跟他的举止和品貌一样,你了解得越多,认识就越深。第一眼看上去,他的谈吐的确不算出众;他的品貌也很难说得上俊美,可是等你捕捉到他那异常动人的眼神和他那甜美可爱的表情以后,你的感觉就大为不同了。现在我已经对他知根知底了,我觉得他非常漂亮;或者至少可以说,几乎算得上是很漂亮的。你觉得呢,玛丽安?”
“我很快也会觉得他长相漂亮了,埃莉诺,即使现在还没看出来。在你告诉我像对姐夫一样爱他以后,我就再也看不到他相貌上的不完美了,就像我现在看不出他心灵上的不完美一样。”
埃莉诺听她这么一说,不禁吃了一惊,她有些后悔在说起他时竟不小心泄露了这么热烈的真情。她感觉爱德华在她心目中占有极高的地位。她相信这种尊崇是相互的;但她对此需要有更大的把握,才能因为玛丽安对他们相互钟情的确信而感到舒心愉快。她知道玛丽安和她母亲一旦有了猜疑,马上就会信以为真——对她们母女而言,愿望就等于希望,希望就等于预期。她试图将事情的真实状况解释给她妹妹听。
“我并不企图加以否认,”她道,“我对他评价是很高的——我非常敬重他,我喜欢他。”
玛丽安听到这里义愤填膺地突然发作起来——
“敬重他!喜欢他!铁石心肠的埃莉诺!哦!比铁石心肠还坏!你只是因为害臊才这么说的。你要是再这么言不由衷,我马上就离开这个房间。”
埃莉诺忍不住笑了起来。“原谅我,”她说,“我向你保证我这不是有意要惹你生气,以这么平静的方式来谈论自己的感情。请相信,我的感情比我宣称的要更为强烈——请相信,总之,我的感情就如同他的美德一样,而且我对他的怀疑——莫如说我对他的希望是他对我的感情能够得到保证,而不是出于任何的轻率或是蠢行。但如若超过了这个限度,你切不可信以为真。他对我是否有意,我一点把握都没有。他对我的情义到底有几分,有时候也显得令人生疑;在他的真情实感完全得到确定之前,我希望能避免因异想天开或是言过其实而对于我单方面的情感做出任何不切实际的鼓励,我想这应该没什么奇怪的吧?在我内心深处,我绝少——我几乎丝毫不怀疑他对我的偏爱。可是除了他自己的倾向以外,还有别的问题需要考虑。他还远没有实现经济上的独立。他母亲的为人到底怎样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从范妮偶尔提到的她的所作所为和观点主张来看,我们从来都不会倾向于认为她是亲切友善的;要是爱德华想要娶一个既没有巨额财产又没有高贵地位的女人为妻,料必会是困难重重的,如果我认为爱德华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玛丽安惊讶地发现,她母亲和她的想象居然距离事实这么遥远。
“你还真是没有跟他订婚!”她道,“不过,这很快也就会发生了。这种拖延倒也有两个好处。一则我就不会这么快就失去你,再者爱德华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提高他对你所钟爱的艺术追求的天生的鉴赏力,这对于你们将来的幸福可是绝对不可少的。哦!他要是能被你的天才所激发,学会自己画画儿,那该多么令人高兴啊!”
埃莉诺已经把自己真实的看法告诉了妹妹。她不相信她对于爱德华的倾心会像玛丽安所想的那样一片光明。有时候他会显得没情没绪的,如果这并非表示他态度冷淡的话,那也说明他们的未来当中有什么几乎同样不容乐观的障碍。如果说他是因为感觉到她的情义还有些靠不住的话,那至多也只会让他有些焦虑不安。没道理会让他的情绪经常表现得那么灰心沮丧的。更合理的原因或许能在他的经济地位尚未独立中找到,这一点不容许他放任自己的情感喜好。她知道如果他不谨遵慈命巴结上进的话,他母亲是既不会容许他就这么舒舒服服地在现在的家里待着,也绝不会容许他组建自己的家庭的。因为对这一情况心知肚明,埃莉诺是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大放宽心的。她不敢指望他对她的喜爱当真能功德圆满,尽管她母亲和妹妹仍旧觉得那么理所当然。不,他们俩相处得越久,他的情义在她看来就越显得没有把握;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那么几分钟令她备感痛苦的时刻,她会感觉他对她的感情也不过就是友谊罢了。
可是,不管这种感情的实际性质如何,一旦被他姐姐有所觉察,也就尽够让她心神不宁的了;同时,也就让她表现得粗暴失礼起来(这种情况是越来越普遍了)。她一抓住机会,就不依不饶地辱慢自己的婆婆,故意说起她弟弟的伟大前程,说起费拉尔斯太太是决计要给两个儿子都攀上贵亲的,要是有哪个年轻的姑娘妄图勾引他的话,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她这番话说得是这么露骨,弄得达什伍德太太既不能装聋作哑,也没办法强自镇定。她无比轻蔑地回了她一句,马上就离开了那个房间,下定决心不管有多不方便,花费有多大,也必须马上就搬走,不能让她挚爱的埃莉诺再在这儿多待一个礼拜,忍受嫂子这种含沙射影的恶意中伤了。
正是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达什伍德太太收到了邮局送来的一封信,信里提出了一个特别及时的建议。来信主动提出有幢小房子可以出租,租金非常便宜,房主就是她的一个亲戚,德文郡[12]一位有钱有势的绅士。这封信就是这位绅士的亲笔,写得情真意切,洋溢着真正乐于助人的精神。他说他听说她正需要个住处,虽然他能提供的只是一幢乡间的小别墅,但他向她保证,只要她觉得地方合适,一切都可以按照她的要求和需要装修布置好。他在详细描述了一番房子和花园的情况以后,恳切地敦请她和女儿们一道前来巴顿庄园,他自己的公馆做客,好亲自决定巴顿别墅——因为这两处房产都位于同一个教区——为了她们居住的舒适该如何进行改建和装饰。看来他是真心诚意地想尽快帮她们解决困难,整封信又都写得那么亲切友善,对他这位表亲而言真不啻于雪中送炭;尤其是在原本更亲近的亲属却待她如此冷酷无情之际。她都等不及去细想或是打听了。她一面读信,一边已经下定了决心。巴顿位于德文郡内,距离萨塞克斯如此遥远,单凭这一条,在几个钟头以前就足可以抵消它可能具备的一切优点,现在却反倒成了首要的可取之处了。远离诺兰庄园已经不再是件坏事;反倒成为值得向往的目标;相较于继续寄人篱下,忍受儿媳的窝囊气,这真成了幸事一桩:永远搬离这个她如此钟爱的地方固然令她痛苦,却也强似在这样一个女人当家的地方定居或是暂住。她当即给约翰·米德尔顿爵士回信,表示对他的好意万分感谢,愿意接受他的建议;然后忙不迭地把这两封信都拿给女儿们看,她得征得她们的同意以后才能把回信寄出去。
埃莉诺一向就认为她们如果能住得离诺兰稍微远一些,会比继续生活在目前的这帮熟人当中更为可取。所以,基于这一点,她没有反对母亲打算搬到德文郡去的主张。而且,按照约翰爵士的描述,那所房子规模既小,租金又罕见地便宜,对于这两点她都没有反对的理由;因此,这个计划虽说无法为她带来任何美妙的遐想,远离诺兰庄园虽说并不符合她的希望,她还是没有劝阻她母亲把那封表示同意的信寄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