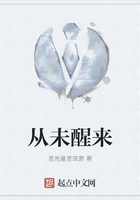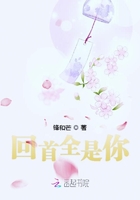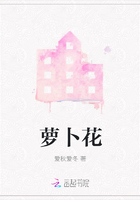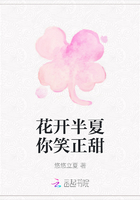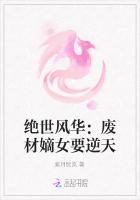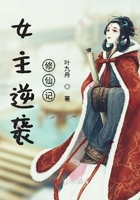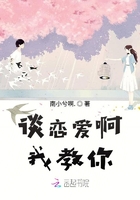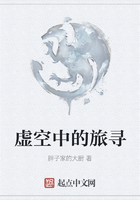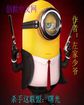3月12日是“个人记忆”开业两周年的纪念日,老简再三斟酌,准备了三十份邀请函,想要组织一场特别的纪念活动。
上午9点,嘉宾们陆续到场。老简如常,准备了简单的茶点和水果。除此之外,老简还准备了一样特殊的零食。9点半,确定不会再有人到了,老简说起了开场白。
“欢迎各位莅临‘个人记忆’博物馆。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能来‘个人记忆’共度生日的朋友,应该就是‘铁粉儿’了。”
老简的话引来一阵笑声,老简也跟着笑,笑完接着说,“大家也看到了,桌子上摆了一样特别的小零食:康乐果。唉,一说完这个词,我就暴露年龄的缺陷了。”
大家又是一阵哄笑。老简继续说,“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个人记忆的人,是一位新朋友。她带来的是,关于她姥姥的回忆,而康乐果就是她记忆中的一个关键点。”
大家纷纷寻找,猜测着哪张生面孔是今天的分享人。“每个人离开后,都会为亲近的人留下点儿什么,今天这位朋友说,康乐果就是她的姥姥留给她的经典回忆。下面,有请今天的分享人,严方。”
一位年轻女士走到老简的身边,向大家鞠了一躬,坐在了大家面前。“大家,早上好。我是严方,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见面。”打过招呼。严方开始诉说她的记忆。
………………
回忆我的姥姥是一件很简单,也很复杂的事情。直到现在,我都感觉姥姥没有离开过,她好像还躺在那间屋里的那张床上,只要我走过去,问上一句,“知不知道我是谁呀?”她就会张开眼睛,看上一会儿,然后笑着说,“燕方啊”。姥姥是河北人,说话会带着些口音,叫我时,偶尔就会说成“燕方”,其实我的名字是严方。
我的童年回忆里,有相当一部分内容都与姥姥有关。因为周末、节日,都要去姥姥家。那种联系就像是一座宝塔中的一层,无法抽去,也无法略过。
与姥姥后半生一直相关的一个词就是“种地”。到现在,我都记得,妈妈带我去姥姥家,为了抄近路,我们沿着铁道边的高地,从房后走过去,然后趴在高坡上,对着坡下正在地里忙活的姥姥喊“姥儿”。喊完了就把头缩回来,接连几声,再等着姥姥因为疑心自己听错来找我们。
姥姥很喜欢种地,她也很幸运,家的附近有大片大片的荒地,所以邻里邻居都在种地,你家一块,我家一块,种好了还可以比比看谁家种的比较好。
姥姥家的小棚子是我童年时最喜欢探险的地方。不同于一些小棚子的黑暗无光,姥姥家的小棚子总是明亮的,里面虽然也杂乱地堆着各种物品,可是一眼看过去却会觉得干爽,现在想来,那画面就像加了一层彩铅笔的滤镜,灰灰旧旧的,却透着温馨的气息。我对小棚子里放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劈板子用的斧子,做木工用的锤子、手锯、刨子,砌墙用的抹板,和灰用的铁锹,还有各种各样的木料、钉子、皮革,玻璃丝袋子、麻袋,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姥姥亲手放进去、摆布起来的。要用的时候,姥姥进去一找就能找到。我也喜欢钻进小棚子里找东西,虽然有时候棚子里连我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可是垫着脚尖、左手扶一下、右手扶一下的晃晃荡荡的感觉,却像在机关中穿梭一样有趣。
姥姥家的屋里还有两个小吊棚,一边吊棚高一些,架在火炕上,用来收纳被褥、衣物什么的;另一边吊棚矮一些,架在对面,装一些经年不用的杂物。
炕上的吊棚我最喜欢,小一点儿的时候,我总惦记爬上去,在上面躺着睡觉;大一点儿不能爬了,姐姐就用吊棚的檐压住床单,让床单垂下来,这样,床单里面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山洞”,大人们干活的时候,我和姐姐就可以在“山洞”里玩了。
我对装杂物的吊棚有种难以割舍的情结,我总想着有朝一日可以将上面的东西都倒腾一遍,看看里面到底都有啥好东西。姥姥总笑我,她说上面都是破烂,没有宝贝,她的宝贝都摆在明面上了。
姥姥的宝贝是电匣子。姥姥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听评书。可能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家里还没有电视的缘故,听广播是姥姥仅次于种地的兴趣。历史题材和武侠题材的小说,姥姥都喜欢听,通常都是早晨起了床,姥姥就把电匣子打开,放上广播,然后她就洗脸、做饭,开启一天的生活。不知道是不是跟着姥姥听了很多评书的缘故,我才对故事有了很深的感情,所以一直想从事写作。
姥姥是个很要强的人,年轻时,姥爷跟着单位支援西线,去了西安,就留了姥姥带着三个孩子在这边,姥姥干了很多苦活累活。当年在体育场那边有运菜的活儿,姥姥就去做过,姥姥个子不高,却和那些干活的男人一样,一包一包的扛菜赚钱。姥姥还捡过煤核贴补家用,每天天刚蒙蒙亮,趁着锅炉房将煤渣运出来,姥姥就拎着夹子和带子去了,连夹带捡,弄一袋子回来。后来姥姥时常想起那些岁月,她会举着手,示意我看她的指甲,然后告诉我,她捡煤核的时候,指甲缝里都是黑的,等到不捡煤核了,那指甲缝缓了好几年才重新褪回到原本的颜色。姥姥还卖过康乐果,那是一种用玉米面做的小零食,小时候卖几分钱一根,一买一大把,套在十根手指上,一根一根咬着吃。我出生后,姥姥就已经不再卖康乐果了,她开始领退休金,于是就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种菜上。
因为血稠的缘故,姥姥十分渴睡,她自己常说,当年在沙发厂上班时,她手里还做着活呢,人就迷迷糊糊得睡着了。所以,姥姥不敢看孩子,怕自己睡着了,孩子发生意外。即便如此,姥姥还是照看了我一年,这是三个孙辈中唯一的特殊待遇。姥姥对我,确实是有些特殊的。姥姥不会做饭,做些普通的家常菜还可以,但是那些精巧一些的菜她就不会做了。但是有一次,姥姥给我做了一条干烧鱼,那是她向大舅学会了之后,趁着我去的时候,做给我吃的。姥姥还悄悄告诉我,让我不要告诉姐姐和弟弟,怕她们会嫉妒。
姥姥一生,从来不信神异之事,可是,她身上却发生过几件。有一件事是姥姥讲给我听的,她说在她小的时候,有一年过年,家里人聚在一起,要祭拜先祖。她是女孩,是不允许靠前的。她说自己那时年轻气盛,说了句“我还不稀罕拜呢”,就挑门帘出了屋。可是她前脚放下门帘,后脚就听到背后有人重重地“哼”了一声。她就有点儿害怕了,心想是不是惹了哪位叔辈亲戚不高兴,回头要是跟她爹告状,她爹就得骂她了。可是事情过去几天,她爹也没说什么,她心里就犯了疑,就问她的一个堂哥,那天她甩脾气走之后,谁跟在她后面到门口了。她堂哥告诉她,没人过去门口,大家都在祭桌前说事情呢。姥姥因此一顿后怕。她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你看我不信这些事,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说道。那一声“哼”可能就是老祖宗因为我犯犟,不高兴了。姥姥说,你别说信与不信,尊重是一定要有的。
因为说起了这种神异的事,姥姥还说了她出生时候的事,她说她娘生她那晚做了个梦,她娘领着个孩子走在路上时,遇到了一个老道,那个老道看了看孩子,说这个孩子是“门头沉”,会压得后面的男娃不敢出来,老道说,你要是同意,我就帮你领走她吧,要不以后你家就没有男丁了。可是她娘不同意。结果梦就醒了。
姥姥出生后,她娘又陆续要过三个孩子,都是男孩,都是早夭。第三个男孩为了能养活,特意取了个贱名,叫“小褡裢”,可是“小褡裢”也没有活过四岁。后来,姥姥的娘找了位高人来破解,高人说,姥姥的命格太大,没得改,但是说姥姥的娘再要孩子,会生个女孩,这个女孩命主门户,当儿子养,就可以“顶门户”了。果然,时间不长,姥姥的娘又有了,生了个女儿,就是我的姨姥。姨姥来这边探望过姥姥,见着她,我愈发信了姥姥的故事,姨姥的眉眼间确实是英气横溢,说话干净利落,连走路的姿态和步伐都透着男人的硬朗。
姥姥的一生有好几道波折,住烧煤的房子曾经煤烟中毒;午睡时因为没注意受了风而面瘫了一段时间,针灸了一个多月才好;做馒头揉面时闪了腰,躺了好几个月;八十多岁时在家中摔倒,腿部骨折做手术加了钢钉。
生命里的最后几年,姥姥过得波澜起伏。
腿部手术后,她大多数时间都要卧床,但是姥姥很坚强,等到腿稍微好一些,她就会自己支撑着坐起来,有时还能扶着椅子下地活动一番。那年,姥爷家的亲戚提议迁坟回河北。姥爷执意要跟着回去探亲。大舅、妈妈和老舅轮番上阵,软硬兼施,希望姥爷别回去。八十多岁的人,长途跋涉,难免奔波劳苦,万一有个闪失,儿女不敢冒险。可是姥爷非常固执,一定要回去,到底,大舅禁不住姥爷的软磨硬泡,和弟弟一起,带着姥爷回了关里。
姥爷从关里回来后不久,姥姥就出现了异样。开始是不怎么吃饭,接着就彻底不吃饭了,最后连水都不喝了。一连九天,水米未进,只是躺在床上,偶尔自言自语一些大家都很着急,不管说什么,姥姥都置之不理,只是自己躺在床上叨叨咕咕。我妈一狠心,从背后抱着姥姥,掰开姥姥的嘴硬给她灌水,开始时姥姥还控制着不咬她的手,后来,水灌进去几口了,姥姥就开始咬我妈的手。
我们一筹莫展,想送姥姥去医院,可是一动姥姥,她就哭喊不停。一天中午,我去姥姥家,想看看她情况有没有好一些。说话时,姥姥还能认出我,还问我怎么没去上班。等我一张口劝她喝水、吃东西,她就不想和我说了。她伸着嶙峋的手向我摆一摆,悄声对我说,她不能喝水,她要回龙宫了,她要去喝她娘的奶水了。我听着这话,心里难受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我和同事说到这事,同事给我出主意,让我们找民间的玄学先生给姥姥看看虚病。我打听到了两位先生的电话,先给其中一位乐先生打了电话,乐先生说,有五个人在闹我姥姥,三个男的,两个女的,都是姥姥的长辈,他们要带她走。我问乐先生有什么破解的方法,乐先生说要去姥姥在河北老家的村头,找一棵树做一些法事。这方法费事费力,我还将信将疑,就给第二位侯先生打了电话。我向侯先生报上了姥姥的名字和岁数,问用不用把本人带去他那里看看。侯先生直接告诉我,不用来了,她妈找她呢。你们烧点儿纸送送吧。
我记得特别清楚,但是是下午,我站在阳光明媚的地上,却感觉心底往外冒凉气。一种前所未有的畏惧涌上心头。我知道,这是我病急乱投医的结果,可是这种谶语式的暗示却让我心中的希望更加渺茫。
后来,我们到底是找到了乐先生,请他就近做了场法事。不知是巧合,还是奇迹。说来也是惊悚,我们天没亮就去做了法事,回到家以后,妈妈到床边跟姥姥说了几句话,问她饿不饿,她就张罗要吃东西了。
我和姥姥一样,也是不相信这些奇闻异事的。可是只要姥姥能健健康康,让我信上一次,我也甘愿。
自那以后,姥姥总算恢复如常了,虽然还是只能躺在床上,但是她能按时吃饭,能认出我们,能跟我们说说话,这就已经足够了。
姥姥走的很突然。虽然妈妈一再说,如姥姥这般的年纪,如果有走的一天,也是难免,我们应该平心静气的接受。可是真到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有些事不是那样简单。
每周去姥姥家聚会是我们家多年以来的习惯。这个周日也是如此,我们去了姥姥家,妈妈问姥姥想吃儿什么,姥姥说想吃白菜馅饺子。吃饭时,姥姥有点儿不舒服,吃了两个饺子就下桌,回床上躺着了。临走时,我妈招呼我去跟姥姥打个招呼,我也不知是怎么想的,说自己没有带玉坠,就没太敢往姥姥跟前去,只站在妈妈身后看了看姥姥。
妈妈觉得姥姥好像有点儿喘,问我是不是有同感。我看了看,感觉是有点儿,大舅说姥姥这几天就是这样,因为姥姥有气管炎,所以应该是老毛病影响的。听了大舅的解释,我们放了心,就跟姥姥说了再见。没想到,这就是我见姥姥的最后一面。
周一凌晨时,大舅打来电话,说姥姥有些不好。我妈和我爸就赶去了姥姥家。妈妈让我不要担心,让我第二天早上过去姥姥家陪姥爷。
我也觉得不会有什么事,所以就继续睡觉,可是翻来覆去的,总觉得胸口压着一口气,睡不踏实。早上起来,匆匆收拾了一下,我就去了姥姥家。给姥爷做好了早饭,我就在家看着姥爷和外甥女,其他人都去了医院。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知道,所以我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心里一片空白。坐在这个位置上,刚好可以看见屋里的床,平时,我坐在这里就能看到躺在床上的姥姥,可是今天坐在这里,我只能看到那半边空床。
妈妈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在家里找找姥姥的照片,说会用到。我到床头柜里取出了装零七八碎的盒子,想要打开时却觉得手很沉。打开盒子,翻找照片,我忍不住落泪了。我知道找照片意味着什么,因为知道,所以心里的背上便抑制不住地涌出来。我发现姥姥没有合适的标准照,最好看的一张照片还是五六十岁时拍的一张黑白照片。翻开手机,我发现自己给姥姥拍的都是生活照,要不就是她唱民谣或者吃东西时的视频。我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给姥姥多拍几张好看的照片,又想谁会闲着无聊带着这样的初衷去给别人拍照片,又想着我还没有跟姥姥再见上一面。我一边想,一边掉眼泪。
外甥女过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在想太姥姥。
外甥女又问我“太姥姥干什么去了”。我说,太姥姥出去办事了。
外甥女问我“太姥姥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太姥姥要去很长时间。
她点了点头,继续去看动画片了。这一刻,我有些羡慕她,羡慕她能轻易地接受这样一个借口,羡慕她还不懂得悲伤。
姥姥是3月12日走的。这天是植树节,是一个象征希望,而且欣欣向荣的日子。我觉得这就像姥姥一生的写照:始终生机勃勃。
我还是留在家里照顾姥爷和外甥女。因为大病未愈,家人都不想我太过参与姥姥的丧事,于是,我就像个旁观者,看着他们忙碌,看着他们操办,看着他们送走我的姥姥。
出殡那天清晨,天边出现了一片形状奇诡的云霞。爸爸特意招呼我出去看,他对我说,风从虎,云从龙。你姥姥是有福的人。高龄喜丧、子孙尽孝,这是你姥姥修来的福气。
姥姥走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改不了口,一问我去哪里,都是去姥姥家。好像姥姥还在,一直未曾离开。
姥姥是个性格坚毅的人,她一生的际遇和境况,彰显了她属相为龙的特点,勇毅坚韧、自强不息。直到姥姥离开,我才发现,除了回忆,姥姥没有留下什么给我们,一如她从没有向我们要求过什么。
姥姥爱吃肉,爱吃拔丝地瓜。
姥姥会唱抗日民谣:同志我问你,你到哪里去,过路的通行证,你可带着呢?拿出来看看,拿出来看看,你才能过去。站岗的规矩,不能马虎的。
姥姥经常安慰舅舅,只要姥爷和舅舅闹了别扭,姥姥就会安慰舅舅,反手还会假模假式地拍打姥爷两下,为儿子出气。
姥姥最喜欢的人是我爸,她总说,姑娘不够好,女婿比姑娘好。
姥姥会蒸枣塔,一层面一层枣,过年时蒸上几锅,看着喜气,吃着管饱。
姥姥腌腊八醋时喜欢放点儿糖,腌好后酸甜辣三味齐全,口感绝佳;可是腌糖蒜时,她却要放一点儿盐,咸香酸甜,另辟一味。
姥姥走后的一年时间里,我总会在各种各样的生活细节中想起她。我觉得,这就是思念。
不是悲伤,只是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