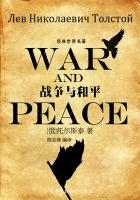大家一想就想了四五天。在这四五天里,白天做《涅槃经》的“笔受”,晚上又要聚在一起,发挥各自的想象力,各讲各的防鼠、防烟的绝招儿。那天后晌,老跋陀打坐时灵光一现,慌忙站起来说:“我怎的忘了,世上有一种荧光木发出的是冷光,如能找到荧光木,不仅再没有油烟子冒出来,不仅小老鼠再也无油可偷了,岂不是连灯油也不必再用了吗?”话刚落地,慧光就说:“师父,那哪儿成呀,你们知道什么是荧光木吗?”大家都一声不吭地摇头。慧光说:“荧光木就是棺材木,是破棺材上掉下来的木块块呀,咋能把它放在经堂之上、而且让它的冷光照在佛经之上呢?”跋陀吓了一跳,说:“果真如此吗?”慧光说:“我住在银杏树下的时候,年年碰见荧光木,它只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才发光,是死人骨头上的磷光,也叫鬼火,风一吹就跑;你一跑,带动了风,它就跟着你跑!”跋陀吓得一哆嗦,说:“哎嗨,又怪我胡言乱语了!”
大家正说得热闹,甘露台下又十分适时地传来与数天以前同样悠扬、同样嘹亮、同样中听、同样正中下怀的叫卖声:“喂,谁要灯啦?哎,谁要气死老鼠的灯啦,哎,不会冒烟儿的灯啦!哎,俺专卖大汉朝流传后世、气死老鼠、还不会冒烟儿的省油灯啦!哎,做这灯不用棺材板儿、油烟子也不熏鼻子窟窿眼儿啦!哎,列位再不出来,俺就过时不候啦!哎嗨,俺就关着门卖疥药,痒者自来吧!哈哈……”
他喊叫着,担着担子就要出村,慧光倏地出现在甘露台上,“那不是小保哥哥嘛,你卖这灯为啥叫气死老鼠灯?”
“老鼠偷吃不了这灯里的油,都把肚皮给气炸了呀!”
“怎的又是不冒烟儿的灯?”
“那还用问,不冒烟儿就是……不冒烟儿的意思。”
“你咋不上来呀?”
“你们这个土堌堆上,还有人对俺博士叔信不过,你那门,俺不敢进!”
正说着,稠又跑下去,夺过小保的扁担,担起担子就上了甘露台。
小保在译经堂上打开一个箱子,大家又都看傻眼了。只见箱子里放着一疙瘩生锈的青铜器物,他把这青铜器物稳稳地放在书桌上,原来是一个青铜铸的一尺多高的童子。童子单膝下跪,左手平托着一个圆盘,右手举起一个鸟笼般的罩子,罩在圆盘上。小保说:“这就是气死老鼠灯,也是不冒烟儿的灯……”
跋陀急忙说:“请批讲,请批讲!”
小保转动着罩子说:“这是活动灯罩,能转动、能开合;童子胳膊和体内都是空壳,体内装水,右胳膊是烟道,灯罩与烟道相连。可将上次送来的‘省油灯’放进这个灯罩。用灯时,灯罩把油烟子送入烟道,进入体内水中过滤,用俺博士叔的话说,这叫‘取光藏垢’。用灯后,关住灯罩,不管是老鼠还是猫都钻不进去,谁想喝这盏灯里的油,都得活活气死!因此,童子灯与‘省油灯’配在一起用,这灯就叫……”
慧光接腔说:“就叫气死老鼠、不冒油烟的省油灯!”
小保又点着头说:“然也!”
稠问:“可从哪里装水?”
小保说:“这灯是组装起来的,你取下灯罩,随意往体内装水就是了。”
道房和慧光当即按照小保所言,在童子灯腹中装水,把“省油灯”放在灯罩内,点着灯,演练了一遍。灯头上的油烟果然被灯罩吸入烟道,进入蓄水的灯腹内;灯罩不仅上通烟道吸去了油烟,转动灯罩,还可以改变灯光的亮度和照明的方向;熄灯后关闭灯罩,就把“省油灯”的灯碗和灯油严严实实地封闭在灯罩中了。译经堂上一片欢腾。
老跋陀喜上眉梢说:“真是巧夺天工,闻所未闻!姬博士是从何处寻得此灯的啊?”小保说:“这是他在太学当上五经博士时,他的老师——一位太学教授拿家中祖传藏品赠送给他的。教授的先祖曾在宫中做官,告老还乡时,带回了这盏童子灯,说是汉朝宫中用灯。巩县铁匠炉村有一位给皇家做过铜器活儿的吴大匠人,博士叔请他看了童子灯,他说这是铜匠行里的极品,听他的祖师爷爷讲过这盏灯,祖师爷爷却也不曾看见过。这灯到现在已有五六百年,可惜不曾用于民间,已经失传了。我博士叔说,此灯转赠给大禅师,也就物尽其用了!”跋陀感叹说:“此灯太贵重,我实在受用不起!”道房说:“如能按照此灯的道理和式样,仿制数盏;再去陶瓷窑上烧制足够用的‘省油灯’与仿制童子灯相配,岂不甚好?”跋陀说:“好呀,只是我们不可再拿捏着架子,让小保这位小施主来回奔跑、扯着嗓子喊叫了,我要亲往荥阳拜望姬玉博士,与他面商此事。明晨出发,道房与我同往。”话刚说完,小迷瞪就跳起来说:“姬博士早就来了,正在大雄宝殿上香呢!”跋陀恍然大悟说:“我正为博士总是冲着我们的‘心里想’、送来我们最需用的灯具犯糊涂呢,原来是你这个小迷瞪当了博士的卧底!”小迷瞪说:“是道房师兄派我去的!”道房缩着脖子暗笑。跋陀又催说道房:“你还磨蹭什么,这次再不可坐等姬博士登门,快跟我到寺内方丈室迎见博士。”
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见。姬玉当即同意请吴大匠人仿制童子灯数盏,而且在此次会见跋陀之前,已在陶瓷窑上定制省油灯若干盏,可与仿童子灯相配。但他执意不言价钱,而要将这些灯盏作为他对译经堂的专用布施。跋陀仍因上次谈到的原因,再次惶恐表示,不便接受儒家名士入寺削发为僧,但他紧接着,便以少林寺方丈兼译经堂译主的身份,特邀博士担任译经堂“正字”兼“润文”二职,负责纠正梵译汉文字上的错误,并在不失原意的前提下,对译文进行润色,提高其汉文品格。为了表示对姬玉的尊敬,道房还特意说明,师父说了,要安排姬玉博士在译经堂左侧与译主跋陀平坐。姬玉推辞再三,终因恭敬而忐忑从命。
值得后人记住的是,跋陀与姬玉的会谈是佛学与儒学结缘、科学与艺术并重的一次会谈。他们在灯具议题上谈得十分投机,不仅用科学的眼光对童子灯“取光、藏油、去垢”的实用性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还用艺术的眼光对“童子举灯”在造型上的可观赏性也进行了异口同声的赞叹,并由此延伸其艺术思维而共同提出,在艺术上不可重复童子灯的造型,务必找到其不可互相取代的“唯一性”。
老跋陀与姬玉都具有丰富而灵动的艺术想象力,二人谈到高兴处,灵感如泉水潺潺出,当即确定以大象、犀牛、天鹅、大雁、猴子的形象为仿制灯艺术造型的依据,比如,可设想这是一只游水的天鹅,它以回首远望的姿态叼着灯罩,将其置于自己的脊背上,它那优雅、细长的脖子就可以成为烟道,通入蓄水的腹腔,两条瘦长的细腿可以省略,作游水状即可,以免灯盏不稳;再比如,以一头吉祥厚重的大象为造型,用它的长鼻子勾起灯罩,灯罩与长鼻子相通,鼻子就是烟道,象腹储水,四条壮实的粗腿是灯的可靠支撑,等等。二人当即兴致勃勃地画了图样,决定由姬玉博士负责仿童子灯的监制,先期的译经工作应即刻在“省油灯”的照耀下开始进行。
跋陀与姬玉亲密会见后,在甘露台上举行了译经正式开始的庆贺仪式。那天特意请来了深谙梵乐的佛门乐工。在庄重、清越的梵乐声中,跋陀带领弟子,在甘露台上种植了两棵柏树,以取其佛荫庇护大地的寓意。后来,这两棵柏树都长成了高六丈、粗六尺、绿荫盖满整个译经堂的参天大树,历经千年沧桑,甘露台上殿宇已荡然无存,两棵柏树却依旧撑起了千年不衰、愈老愈浓的绿荫。
直到公元1984年9月的一天,村民堆放在树下的麦草起火,烧焦了一棵柏树,剩下的那棵也日渐枯萎,嵩山便时常在夜深人静时发出苍老的呻吟:“疼啊,疼啊,娃儿们!”据说,一千五百多年以前,当柏树苗刚刚种上的时候,跋陀也曾在一天夜里听见过嵩山的呻吟:“疼啊,我老疼啊,娃儿们!”跋陀只顾得翻译经书,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便用手指敲打了耳朵,继续埋头于经卷之中。次日,山上就发生了意外的灾祸。
二十二、山火
那是晚霞缠绕在山崖半腰的时候,在山神庙门前的老柿树下,年约四十仍风姿绰约的山神婆着农妇装,正坐在草墩子上用龙须草编织草鞋,几只山喜鹊急急飞来,向山神婆“喳喳”鸣叫不已。
山神婆说:“你们嘁嘁喳喳地乱吵乱叫,叫我听谁的?”
山神婆正说着,高大、瘦健的山神佬身穿樵夫装,腰系青藤,背竹篓,赤足走来,接口道:“老婆,喜鹊又向你说什么,莫不是说我坏话?”
“喜鹊说,少林寺和尚毁树开荒,山禽、小兽都无法在那里居住了!”
“怪不得我脚背上又疼又痒!”
正说着,又有一只乌鸦扑棱着翅膀落于枝头,向山神婆“哇哇”直叫。
“乌鸦又打啥‘小报告’?”
“它说和尚在山上起石头、垒地堰,压了水脉,泉水断流了!”
山神佬气恼地说:“建造少林寺时,他们还毁了二百亩山林,我正要去找跋陀算账呢!”说罢,顿了顿脚,便倏地没了踪影。
夜晚,译经堂的雕花窗棂里透出明亮的灯光。
在甘露台下,道房正坐在门楼外边的草地上,望着星星吹木笛。
山神悄然而来,冷不丁儿喊叫道:“这笛儿吹得不赖!”
道房也喜欢听人夸奖,笑着问:“咋个不赖?”
山神揶揄说:“公鸭子叫似的!”
道房报复说:“大施主谬赞了,我吹的是‘老虎磨牙’!”
山神问:“这‘老虎磨牙’属于哪个曲牌?”
道房信口胡说:“倒是个好曲牌:《百鸟朝凤》!”
山神说:“哎呀,老虎也来磨牙,这百鸟还朝得了凤吗?”
“此话怎讲?”
“你们少林僧人闹得山林不安,百鸟都搬家了呢!”
“有这样的事?”
“速叫老跋陀出来见我!”
“我师父正在翻译经书,不见客人。”
“我不是客人!”
“那么,你是什么人?”
“我是讨债的债主!”
山神跳进门楼,上了台阶,却被道房拦住了。
“我师父从不借债,哪里有什么债主!”
“此债不是人债,是天债!”
跋陀听见吵嚷声,急趋门前问道:“是哪位施主找我?”山神接腔说:“不是施主,是来要债的债主!”说着,就推开拦路的道房,登上了甘露台,挤进了译经堂。跋陀急急问:“请问,老僧欠了你什么债?”山神哼了一声,说:“山水债!”跋陀惊诧地问:“何谓山水债?”山神说:“这嵩山山水,本为嵩山生灵所共有。可你们建造寺院时,毁我山林二百亩,眼下,又有僧人掘地开荒,断我泉水,毁我林木。我刚才巡察过了,寺院的后山上,小斑鸠已经没有地方做窝,画眉鸟也没有心思唱歌儿,鸟兽都忙着搬家了!”跋陀眨巴着眼睛问道:“果真如此吗?”山神说:“快给我搬太岁椅来,我要坐下来问话!”
跋陀急忙让稠搬来一把罗圈椅,不胜惶恐地说:“对不起,我这里没有什么太岁椅,请尊臀委屈一下,就坐在这把楠木椅子上问话如何?”山神轻轻一跳,跳到罗圈椅上,就蹲在椅上,向跋陀伸出一条腿来,指着小腿上的褐色疤痕:“你瞧,这就是你们建寺时砍伐山林,给我留下的一大块疤瘌!”又指着脚背上一个乌黑发紫的肿块,“你寺僧人正在这里毁树开荒,哎哟,我的脚背好疼啊!”跋陀惊异地说:“这山林竟长在大施主的腿上、脚上了吗?”山神抬起光脚丫子,竖起大拇脚指头,扭动了一下,又用手指指点着说:“少林寺在此。”跋陀急忙捂住山神的脚指头说:“哎呀别动,我的寺院吃不消!”
跋陀跟三个弟子拉了一个背场,紧急商讨后,又匆匆走过来,躬身问道:“请问大施主尊姓大名?”山神嘲笑说:“好记性,你真的把洒家忘到脑后了吗?”跋陀眯着眼,上下审视了山神一番,又不胜惶恐地摇了摇头。山神说:“去年,你进入嵩山时,在磨盘山下,曾借宿我家,与我并肩打坐……”跋陀又摇了摇头说:“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山神说:“怎么,你不认账?好吧,让我学给你看,你在我家住了一夜,次日一早醒来,是这个样子……”山神站起身来,模仿跋陀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四顾不见弟子,就露出一脸惊慌的表情喊叫:“道房、稠在哪里?”又学他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在山神庙前拱手道谢,清理嗓门儿,甚至学他用沙哑的声音喊叫“老哥”,都学得惟妙惟肖,惹得稠和道房都“哧哧”发笑。山神问道:“怎么?时隔一年,你就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跋陀傻傻地看了他的表演,惊奇地问:“难道您就是山神庙里供奉的那个泥胎吗?”山神气得跳起来说:“我怎么是泥胎?那是洒家的泥塑金身,我有事出行,或是回后殿歇息,就叫他替我坐在那里值班,懂吗?”
“那里只是一个小小的破庙,怎成了你山神老爷的官署?”
“那只是我在嵩山北区临时办公的行署。”
“你那行署的房子过于矮小了一点。”
“我最讨厌住高楼大厦,再高再大,还能高得过、大得了嵩山不成!”
跋陀觉得这番话非同凡响,急忙拱手而拜说:“哎呀,果然是山神大哥!”
山神仰着脸说:“不能随便来个傻老头就叫我大哥!不瞒你说,这中岳嵩山上的大事小事,大到山洪暴发、崩山溜坡,小到小松鼠偷吃松子儿,小斑鸠做爱垒窝,玉皇大帝都交给我管了。哎呀不好!”山神指点着脚背大叫,“我这里火烧火燎!”
跋陀说:“道房,快拿清凉散来!”
山神说:“后山又在烧荒,清凉散管个鸟用!”
话刚落地,山神就倏地不见了踪影。
后山坡上浓烟弥漫,火舌正在引燃一大片灌木和野草。
道房、稠随跋陀向山上疾行。山神率一群猴子从浓烟中钻出来,缺了半只耳朵的猴王也紧紧跟随在山神身边。猴王瞅见了跋陀,就止住脚步,向跋陀拱手施礼,口中“吱吱”有声。山神说:“老跋陀,你听见了吗?这猴王一连声地叫你师父,还怕火烧着你,叫你赶紧离开这里呢!”山神又用猴语对猴王说了一番话,接着又翻译给跋陀:“我对它说,你赶紧走吧,不要理他,是他的和尚放火烧荒,烧了你们的家园,你跟他亲热个?”遂又挥着树枝,引导猴群离去。猴王恋恋不舍地望着跋陀,眼里含着泪水。道房用猴语问:“猴娃,你们要到哪里去?”猴王和猴娃们都低头不语,神色黯然地向深山里走去。跋陀喊叫说:“猴娃,你们走好啊!”山神抢白他说:“还说啥走好走不好,嵩山原来就是它们住的地方,你们偏要来这里捣乱,还叫人家走好啊!”山神说着,又钻进烟火中。
跋陀、道房迎着浓烟前行,又见山神领着一群野兔、刺猬、松鼠在火光中逃窜。鸟巢在浓烟中坠地,鸟蛋破碎。一对飞逃的斑鸠发出惊慌的叫声。一只斑鸠落在山神的肩上,“咕咕”鸣叫不止。此时的道房已精通嵩山鸟语,跋陀急急问他:“小斑鸠说些什么?”道房却露出为难的样子未做翻译。山神生气说:“我最讨厌这样的翻译,只翻译好听的,刺耳的话装作没听见,把你师父蒙在鼓里!”遂向跋陀翻译说:“小斑鸠正在怪我呢!它问我:‘你为啥老是袒护这个不识好歹的大头陀,还有他这个傻不拉叽的憨弟子?在黑熊沟,你叫我给他们引路;在磨盘山,你叫我给他们搬兵;去年,小鹦鹉受伤,你又要我送去一股东南风,让鹦鹉乘风去皇宫为他报信儿;眼下,我刚刚自由恋爱,有了个知疼知热的当家的,你又派俺小两口在这里安家,当了你的观察哨,要俺终生守着这个老糊涂,随时向你报告他的消息,怕他受了委屈。可他手下的和尚却在这里点火烧荒、掘地三尺,闹得飞禽走兽都无家可归。山神爷,莫怪俺抗命,从今天起,他这个老糊涂,俺再也不侍候了!’”山神言毕,就看到小斑鸠厮跟着它的“当家的”,向深山飞去。
跋陀听了,又傻了似的瞅着浓烟发呆。
山神说:“你又呆呆地瞅个啥?”
跋陀说:“我怎的瞅不见我寺僧人,这真的是我寺僧人惹的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