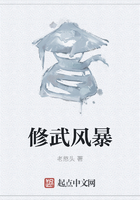一、失踪
北魏孝文帝将国都由平城迁到洛阳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惊诧不已的事情,就是孝文帝亲赐的最高僧官沙门统——天竺国大禅师跋陀的神秘失踪。这位大禅师身材魁梧、浓眉高鼻,往人群里一站,不仅比别人高出半个脑袋,模样也与汉人迥异。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佛陀。因他仪态华美、面容清奇,大家都叫他“美佛陀”。他怎么说丢就丢了呢?孝文帝刚刚把文武百官在洛阳安顿下来,就下了一道特别的圣旨,要统领佛门的沙门都惠深,立即找到老跋陀的下落。
惠深急忙到洛阳城中的四十三所寺院里挨门寻找,发现由平城拥入洛阳的两千多名僧人已使得每一所寺院人满为患,却没有找到跋陀和他的弟子道房的踪影。只是听人说,有几个老僧经不住旅途的风寒劳顿,没有走到洛阳,便在途中夜宿时“坐化”了;还有一些僧人因过黄河时渡船超载,不幸溺水身亡。但也有人在黄河岸边看见过跋陀,说他等渡船等得无奈,弟子道房就拱起脊背,把用于绘画的素绢铺在自己的背上,请师父捉笔作画。跋陀刚刚画好了一条黄河大鲤鱼,就听见“轰隆”一声巨响,那鲤鱼摇头摆尾,掀起了数丈高的大浪,把跋陀和道房卷进了黄河。可也有人说,是道房为给师父解闷而吹奏他那支神秘的木笛吹出了毛病,师父点题《哀鸿》,道房吹的是孤雁长鸣之声,却引得长空中一只孤雁扑棱着翅膀俯冲下来,驮起跋陀和道房飞上了天空,渐去渐远,最后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消失在天地相连的地方。
惠深听了一个个吓人的消息,心里正七上八下地犯愁,皇上却又派身边太监小六子,领来一乘八抬大轿,再次传旨,要跋陀立即乘轿进宫,还带来四名御前侍卫,保护跋陀的安全。惠深慌忙巴结小六子说:“小哥哥呀,你就在皇上面前替我说几句好话,再宽缓几天。听说这街头巷尾,也打破了僧俗不可混居的规矩,竟有数百家民宅里也挤进了僧尼,叫我一家一家地找吧!”十六岁的小六子觉得那一声“小哥哥”很是受用,就做出哥哥的样子出谋划策:“莫急,你听小哥哥我的吩咐就是!”惠深急忙问他:“有何吩咐?还不快讲!”小六子说:“咱就在大街小巷贴满寻人告示,画上老跋陀的图像,写上赏格;再找一面锣来,你敲锣,我吆喝,咱俩边走边敲边吆喝:‘老跋陀,哐哐;皇上找你呢,哐哐;快给我爬出来,哐哐哐哐。’何愁找不到他?”惠深连连摇头说:“我的小爷爷,万万不可!咱们鲜卑人一到中原,就把人家天竺国的大禅师、咱们皇上亲封的和尚头儿——比我这个沙门都还要官高一等的沙门统给弄丢了,遮丑还来不及呢,再敲着铜锣、扯着嗓门儿喊叫出去,岂不叫中原人笑掉大牙!”小六子说:“那就算我啥也没说,反正在平城我就跟跋陀的弟子道房常来常往,跋陀也口口声声称我为‘小六居士’。我就带着轿子,跟着你查户口就是了,查出了老跋陀,就把他往轿里一塞,抬上就跑!”
惠深和小六子领着兵士、带着轿子,快步上了街头。
这时候,有一个十二三岁的红衣童子,高高踢起一只毽子,毽子上插着七彩的野鸡翎毛,在半空中迎风翻飞。红衣童子追随着毽子飞越轿顶,用洛阳话叫道:“哈哈,从平城来的傻货,咋把你们的傻和尚给俺弄丢啦?哈哈哈哈!……”
二、猴娃太子
跋陀和道房却正在洛阳街头游荡。
在云冈石窟一个幽暗的石洞里经历了五年的坐禅修行并熟读汉人儒家经典之后,老跋陀又在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中舒展了筋骨,沐浴了公元495年春天的温柔阳光和带有野薄荷味儿的和风细雨,穿过了比平城那边稠密而热闹的村庄和聪明的中原农夫赶着黄牛犁耙得平展、暄腾的黄土地,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古都洛阳。
老跋陀觉得,能够无拘无束、无人过问地与弟子浪迹于古都街头是一种难得的幸运,因为在平城后来的几年,他过得实在是太红火、太喧闹了。自他打坐时进入了“火光定”的境界,出现了整个身体都被笼罩在熊熊火光中的绮丽景象以后,他的禅房便时时受到平城市民的包围。每天到了他打坐的时候,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和游手好闲之辈就会蜂拥而至,用观看珍禽异兽的目光观看他“火中打坐”的奇景。“火光定”也惊动了朝廷。孝文帝对这位曾经在西域周游列国而终于在他佛法兴盛的京城修得正果的天竺禅师表示了极大的敬意,立即在武周山为他开凿石窟,别设禅林,让他在那里大施教化,并封给他一个最高僧官昭玄沙门统的荣誉职务。
“火光定”给跋陀带来了出乎意外的荣耀和喧闹,闹得性喜幽居、偏爱独处的跋陀头昏脑涨。使他惶恐不安的是,在他心神合一、净心无染时才可以产生的“火光定”,已经有好长时间不曾出现过了。他决意到洛阳后就让自己隐居于一个偏僻、宁静而不被人注意的寺院,让世人忘记自己,以便专心修行并做好他倾心已久的一件佛门大事,就是按照当朝皇帝提倡的普通话——“洛阳正音”翻译梵文经书,在汉人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中原大地传播佛学经典。因此,他一到洛阳,就向朝廷隐瞒了自己的消息,不事声张地寻找环境幽静的寺院,以便尽快地安定下来,开始翻译经书。却没有想到,他几乎跑遍了洛阳的寺院,也没有找到可以落脚的地方。
跋陀和道房又来到了洛阳南城。南城是平民居住区,也许在小巷深处的民宅中可以找到一个暂可栖居的小院或是一间小小的禅房。而首先吸引了他的视线的,却是一个人声喧闹的广场。紧挨广场的名叫天街的闹市上,是密密麻麻的商店酒肆,像一座座狭窄而精巧的鸽笼,悬挂着形形色色的招牌,打着随风飘摇的酒幌子。对洛阳再次成为国都作出快速反应的第一批商贾和艺人已经到来,街道上时有牵着骆驼的胡人,还有耍猴者与玩蛇人,让猴子蹲在肩上或将蟒蛇缠于脖颈,或吹长笛,或奏胡琴,来到天街广场上献艺。
道房问:“师父,我们要寻找幽静的地方,怎的又跑到闹市上来了?”跋陀说:“来读一部大书。”道房说:“哪里有什么大书?”跋陀伸出手指,在闹市区画了一个大圆,说:“这里就是一部大书。华夏古籍上记载的‘摩肩接踵’、‘挥袖成云’的都市风景,还有中原古都的市井百态全都写在这里了。我们先开开眼界,还可以听听洛阳闹市上的声音,再去找落脚的地方。”他说着,忽地用手指扒拉着道房的耳朵说:“你听你听!”道房听见叫卖“烫面饺”、“猪头肉”、“羊杂碎”、“驴肉汤”的声音此起彼伏,就连忙捂着耳朵说:“师父,我不敢听了!”跋陀问:“何以不敢听了?”道房说:“叫卖声勾我口中馋虫,可我们出家人是不可以动荤腥的呀!”跋陀认真地想了想,说:“今天可以随意些,可以叫你的耳朵、还有你的鼻子尝尝洛阳的味道,浅尝辄止,如何?”道房郑重点头说:“谢师父!”就努着鼻子闻起来。
跋陀和道房被人群推拥着,路过一家酒肆,只见一个堂倌儿用草绳穿透鱼鳃,掂着一条活蹦乱跳的金色大鲤鱼,正向路人叫喊:“客官儿,进来饮酒吧!这是今天大清早才从洛河里捞上来的金鲤鱼,千里挑一的金鲤鱼呀!一片鱼鳞一片金,吃了金鲤鱼,日进斗金啦!”道房怕他纠缠,急忙护着跋陀,夺路而去。堂倌儿见他俩穿着破旧的僧衣,又盯着他们的光脑袋,讪笑说:“两个光葫芦,一对穷光蛋!”道房说:“师父,他像是用洛阳话骂我们呢!”跋陀品味多时,批讲说:“非也,他是夸我们呢!所谓‘光葫芦’者,是说我们的脑袋像发光的葫芦一样好看;至于‘穷光蛋’嘛,顾名思义,也显然是一种可以发光的蛋,都是很好看的东西!”道房露出顿开茅塞的样子,点头称是。
他们走进了天街广场。道房为师父开路,挤进了一堵圆形的人墙。被人墙圈着的是一个鸡毛纷飞的斗鸡场。他们虽然见过公鸡为争夺食物、为占有母鸡而相斗,却还是第一次看到公鸡被它们各自的主人煽起没有来由的仇恨,在看客们的挑逗和助威声中凶狠搏斗,用锋利的尖喙对啄,用粗壮的利爪跳起来猛击对方。一只鸡被抓瞎了眼睛,另一只鸡被啄掉了鸡冠,鸡脖子上也被啄光了羽毛而鲜血淋漓,却仍在拼死啄斗。
跋陀忽地用长袖遮住了眼睛。
道房问:“师父,您怎的不看了?”
跋陀说:“我不敢看了!”
“怎的不敢看了?”
“我的心乱了!”跋陀说,“我在汉人的古籍《左传》和《史记》上,看到过斗鸡的事情,却没有想到是这样的惨不忍睹!”
“古籍上怎么说?”
“说的是距今一千年前,鲁国贵族季氏和郈氏相约斗鸡,一方在鸡的翅膀里暗自撒上了芥末,企图辣坏对方鸡的眼睛;另一方却暗自给鸡装上了铁爪,结果季氏的鸡败了。季氏大怒,就带兵攻打郈氏,占领了郈氏的封地。鲁国国君率师惩罚季氏,季氏又联合两家贵族势力打败了鲁国,鲁国国君便逃奔到齐国去了。”
“哎呀,斗鸡也能斗出这样大的乱子!”
“斗鸡是会斗出杀伐之心的呀!”
“师父,我的心也乱了!”
“赶紧走吧,去找个能把心平着放的地方。”
师徒俩正说着走着,忽听得有人大声喊叫:“抓住它,抓住它!”
随着喊叫声,有一只身穿红马甲、歪戴白毡帽的猴子,坐在一辆摇篮般的小车上,赶着拉车的小白狗飞驰而来;忽而丢下小车,蹿跳到路边一棵老柳树上,与躲在树荫深处的一只猴子会合,便在一棵棵枝叶相连的路边柳树上不停地蹿跳着,逃往洛河岸边去了。耍猴的汉子掂着鞭子追过来,声声叫骂着:“小王八羔子!”急向河边追去。替他守着小车和小狗的烂眼圈老汉在他背后喊叫:“别撵了,你撵不上了,它是跟它那个‘相好的’骚货私奔了!”看客们都哄笑起来。
烂眼圈老汉对看热闹的人说:“都别笑,这事也真的奇了!我跟耍猴的是一个山村的乡邻。开春以来,他来洛阳耍猴,我多次跟他一起来洛阳山货行里送货,每次都看见一只母猴在树林子里等这只公猴,躲躲闪闪地追随着它。半路上歇脚时,趁耍猴的打盹儿的工夫,母猴也会凑上来,跟公猴亲热一回。今天来耍猴,又被这只母猴盯上了。刚才,公猴表演了‘猴公子赶车’,看客们都拍红了巴掌,一迭声地叫好,‘猴公子’捧起柳条筐,看客们正雨点般地向筐里扔钱,那母猴又在老柳树上陡然现身,‘猴公子’便扔了钱筐,追赶母猴去了。耍猴的被搅了场子,钱筐也叫人踩瘪了,明晃晃的铜钱撒了一地。几个泼皮货争着捡了地上的铜钱,一阵风似的窜进小巷里去了。哎嗨……”烂眼圈老汉哭笑不得地说,“平时叫人耍的猴娃,这一回倒是把耍猴的给耍了!”看客们又都哄笑起来。
人们正说笑着,跋陀却望见耍猴的用绳子捆着猴子的一只前腿,像押送犯人一样拖着走过来,找到了丢在路边的小车和小狗,便把猴子吊在老柳树上,骂道:“狗娘养的,前天你跑到山里找‘相好’,我翻了几架山才把你给找回来;今天刚叫你进城露露脸儿,你个小王八羔子一瞅见那个骚货,就把钱筐子给我撂了!”他恶狠狠地抽着鞭子,骂道,“我非抽死你个小兔崽子不可!”
时时注意学习中原语言的跋陀,只一会儿,就学到了关于猴子的三个称谓:狗娘养的、小王八羔子、小兔崽子。他经过认真的思考,才估摸着是耍猴汉气晕了脑袋,错骂了猴子的种群,那一连串的鞭子却没有发生任何偏差地抽打在猴娃的身上。那猴娃倒是个倔犟的硬货,它悬空打着滴溜儿,挨着鞭抽,却始终咬着牙不吭一声,毫无求饶的表示,颇像一条好汉。小白狗早被吓坏了,它蜷缩在小车后边,战战兢兢地偷窥着主人的暴行,鼻子里发出“呜呜”的哀鸣。
跋陀忍不住向耍猴的拱手施礼说:“耍猴师傅,老僧代猴娃向你求情了!”
跋陀话刚出口,道房就跑过去给猴子解开了绳套。猴子从树上跌落下来,便眼巴巴地望着跋陀,忽地匍匐地上,向跋陀行了个跪拜之礼。跋陀一转身,像是撒开了一个大喇叭似的撒开了僧袍,僧袍合拢时,便把猴子罩到了僧袍里。
耍猴汉气恼地问:“和尚,我的猴娃呢?”
跋陀反问道:“你还要用鞭子虐待它吗?”
耍猴汉说:“不,我要用鞭子调教它。”
跋陀说:“耍猴师傅,猴子也知道痛呀,心里也知道难受,只是它不会说出来,全靠当人的心疼它!”
这时,又有许多看客围了上来。跋陀便向众人掀开了僧袍。大家惊异地望见,猴娃像是怕别人把它抢走似的,把四肢紧紧地缠抱在跋陀的一条腿上,两只脚在跋陀的腿上绞缠着,打了个结。猴娃的耳朵被打裂了,有半边耳朵血淋淋地耷拉下来;红马甲也被撕碎了,身上布满了鞭子抽打出来的一条条带血的伤痕。跋陀还记住了猴娃的眼睛,那是一双深恐再次受到虐待而惊慌、迷茫地窥视着人类的眼睛。跋陀不忍再看这双眼睛,就放下僧袍,再次盖严了猴娃,转而对耍猴的说:“耍猴师傅,猴娃正痛得打哆嗦呢!”
耍猴汉说:“你倒管得宽,你跟猴娃到底是哪门子亲戚?”
道房动怒说:“休得胡说!我师父是皇上亲封的昭玄沙门统、从天竺国来的跋陀大禅师。”
人群中扑闪着惊诧的目光,传来窃窃私语声。
耍猴汉却毫不气馁:“就算他是皇上亲赐的啥啥沙门统,可我倒要问问,皇上说没说过,那啥啥沙门统可以霸占我的猴娃?”说着,就要向跋陀动手。
道房急用身体挡开耍猴汉:“这猴娃是我师父收下的弟子,不能任你虐待!”
“俺的猴娃怎的成了胡僧的弟子?”
“你没看见吗?猴娃一见我师父,就行了跪拜之礼!”
“我说不过你,却打得过你!”耍猴汉揪住道房,又要动手。
看客们急忙拦住了他。
烂眼圈老汉把他拉到一旁,说道:“你要再发火,我可要怪你糊涂了!”
“俺咋个糊涂?”
“我眼看着这猴子跟你无缘,说不定是你前世欠了它的孽债,还不知道以后会惹出多少祸事来哩!何不顺水推舟,把猴娃卖给大禅师。既成全了大禅师跟猴娃的缘分,你也借坡下驴,免得再生事端。”
耍猴汉变软了口气说:“那就要看大禅师舍不舍得花钱了!”
烂眼圈老汉又向跋陀说:“小的还要替这位耍猴的乡邻说几句话,他驯养这猴娃也是操了心、出了力、花费了银钱的。大禅师慈悲为怀,总不能牵着猴娃就走,总得拿出够为猴娃赎身的银钱才是。”
跋陀露出一脸的惶恐说:“可我们出家人不摸钱财,身上从不带钱的呀!”
道房却小声提醒说:“师父怎的忘了?我们离开平城时,皇上怕我们路上化不到斋,特意给我们发了一百六十枚新铸的太和五铢钱。我们一路上都遇见慷慨大方的施主,连一枚五铢钱也没有花出去呢!”
跋陀大喜说:“那你快把银钱拿出来呀!”
道房说:“师父莫要着急,还不知道要给猴娃出多少赎身钱呢!”
那边,烂眼圈老汉跟耍猴的已经把手伸到一个空布袋里,互相用手指捏起了暗码。只见手指头在布袋里像小老鼠一般地鼓拥乱动,一个说:“这个价咋样?”一个说:“这个价,不能少了!”一个又说:“让出这个数,权当送给我一壶酒钱!”
跋陀和道房正看得发呆,烂眼圈老汉又拉长了跋陀的袖子,把他的手指头伸到跋陀的袖子里,捏起了跋陀的手指头。跋陀没有捏过“暗码”,不知他意欲何为,惊慌失措地抽出手指,连连向手指上“噗噗”地吹气,又惹得看客们哄然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