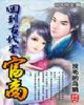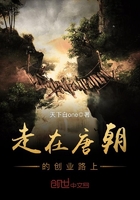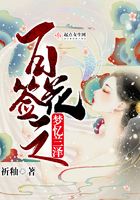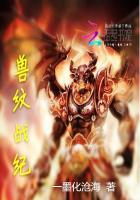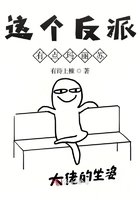[你的春色不染心境]
地址:上海常德路195号常德公寓
于我而言,对上海的最好体验就是背个包在静安区游荡,在各种老建筑前流连,冷不丁碰上一栋有来头的宅院,便有邂逅的窃喜。这感觉也似极了年少时在青岛的时光,背着书包在老街上晃荡,头顶有浓密的法国梧桐遮盖,旁边有一个个欧式庭院,觉得好玩就进去“探险”。
这样的游历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似乎也成了我与故人穿越时空联系的唯一方式,每站在一个故居前,作品中的一些文字便成为具象,一点点蛛丝马迹也能让我欣喜。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被我曲解为“读了他的书,就去他生活过的地方找他”。
我读张爱玲还算早,大概是1994年,那年我14岁,购得一套安徽文艺出版社的版本,一读便沉迷。如今看来,那版四册文集收录作品不多,错漏不少,远非佳品,但张爱玲在大陆的普及,却恰恰在那时开始。
还记得一个笑话,高二时,班主任叫张安林,某日宿舍里同学聊天,一个总嚷嚷要看书却有阅读障碍的同学说“听说有个作家现在很红,书很好看,叫什么来着?好像跟我们班主任名字差不多”,我说是张爱玲,他大叫“是啊是啊”,不过后来他看了几页,便说跟林语堂一样无聊,放弃了。
之后的很多年里,张爱玲都是我的最爱之一,即使她已沦为许多人装模作样的工具,即使很多人只是通过电影(如《色戒》)才开始了解她。曾读过一篇文章,说张爱玲、达明一派和昆曲都能让人沉溺,此语深得我心,这恰恰也是我的“三大件”。
去上海寻访张爱玲故居,第一站自然是常德路195号的常德公寓。她住过的公寓不少,但时日最久、故事最多的当属这里。
她在这里写下了《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封锁》《花凋》等,还有我最爱的《金锁记》。也是在这里,她与胡兰成相识相恋并秘密结婚。
常德公寓当年名叫爱丁顿公寓(也译作“爱林登公寓”),是当年那条路上最高的建筑,恰在十字路口,楼高七层,意式风格,墙面为淡淡的粉色,乍看上去还有点偏黄,中间有暗红色竖纹搭配,尽管重新粉刷过,仍可见墙身的斑驳,最抢眼的是每户的阳台,两翼对称伸展,尽头为椭圆形。公寓大楼前是一排法国梧桐——那恰恰是张爱玲所描绘的情状。
那时,张爱玲与她那位著名的姑姑张茂渊住在一起。两人各居一室,有自己的卧室和盥洗室,中间有厨房相连,要见面,开门即可,但若不想见面,也可从消防门进出,可算是各有私人空间。她们的经济也各自独立,自己赚钱分摊房租和水电等开销。我喜欢这种看似无情的分明——人与人之间若想持久,财务就必须分明,很多人会错误理解“谈感情不谈钱”这句话,所谓“不谈钱”,是指彼此不计较,但绝不等于财务可以不清晰甚至一团糨糊,金钱最易惹纷争起误会,算得分明反倒免除后患,有助感情的长久。
她们也住得长久,1939年搬入这爱丁顿公寓,起先住在51室,1942年搬入六楼65室,直住到1947年。
张爱玲曾写道:“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我也爱“逃世”这二字,而且极赞同她的说法。如今说起“逃世”,很多人总爱搬出什么田园生活、返璞归真之类的词,摆出一副甘居乡下小屋,可抛弃手机电脑电视的样子,可他们往往只能尝个新鲜,若真让他们一直住下去,没几天就会闷到发疯,见到鸡屎猪粪便避之不及,漫漫长夜也不再煞有介事数星星……所谓叶公好龙,大抵如此。
我是个享乐主义者,对现代化带来的各种好处甘之如饴,该用则用,只要不沦为物质的奴隶即可。真正的隐居是心灵之隐,不管你身在何处,所谓“大隐隐于市”便是这个道理。隐居与享受物质也并不冲突,刻意将“隐居”与所谓的田园生活、乡下小屋画等号,以显示自己不是物质的奴隶,其实恰恰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又沦为了环境的奴隶。也恰恰说明了心仍未静,隐居并非出于本心,只是出于姿态,即沦为了姿态的奴隶。
张爱玲对人生实在看得太透,透彻如明镜,所以独立,所以自主,不做姿态,却比任何人都更有姿态。
她在常德公寓的生活极是惬意,每日有人送报送牛奶,洗澡有热水,家务和煮饭都有佣人操办,周瘦鹃曾写过她的客厅:“乘了电梯直上6层楼,由张女士招待到一间洁而精的小客厅,见了她的姑母,又指向两张照片中的一位丰容盛髻的太太给我介绍,说这是她的母亲。茶是牛酪红茶,点心是甜咸具备的西点,十分精美,连茶杯和点心碟也都是十分精美的。”
她也做到了逃世,极少出门,直到与胡兰成热恋后才有露面,以至于这几年间,除了诞生了一部部作品之外,很难寻得她的其他记录。据说,她连人都不愿见,有人来访,她甚至会自己站在走廊里隔门回答:“张爱玲不在!”
除了爱情,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止她逃世。可奇女子的爱情,也总与世间情事无异,那些哀伤寂寞、离合悲欢,亦如影随形。哪怕她看得再透,文字里的清醒渗入骨髓,也终究当局者迷。
胡兰成也吃过闭门羹,他第一次来拜访张爱玲,敲门却无回应,他不死心,便从门下塞进一张纸条。情事就此如奔马,来得极快,其间跌宕,张爱玲很少提及,唯一参照便是胡兰成的《今生今世》。
他在《今生今世》里写这座公寓:“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原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的,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断乎是带刺激性。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地来去。”
张爱玲也喜欢在阳台上看上海,那阳台长长的,尽头处呈弧形,圆润地包裹着看风景的人。一个个白天与黑夜,她看着远方灯亮了又灭,看旁边电车场的车出出入入,那些情境与细节,总能在她的文字中找到。
隐居者如她,并不怕寂寞,一页页掀过的旧时光,旁人看来触目惊心,于她只是岁月静好——她是“成名要趁早”的人,却也更早懂得了淡漠。至于爱情,也只求静好,至于姿态,高或低都只随心,就像她写在照片背面的那句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静静地低到尘埃里,静静地欢喜,静静地开出那朵花,只是,几年之后“我将只是萎谢了”。
1946年11月,胡兰成回到这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晨离去,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没过多久,张爱玲也搬走了,带走了伤心,也带走了过往。如今走入常德公寓,仍能寻到一些故迹,但也面目全非,唯一例外怕是门厅墙上的那个木质信箱。据说《色戒》上映之后,张爱玲的新粉丝如雨后春笋般一茬茬冒了出来,即使有些人此前从未读过张爱玲作品,也虔诚至花痴状,一波波跑来寻觅张爱玲的故迹,这里的住客不堪其扰,只能在门口安装大铁门,还挂上“私人住宅,谢绝参观”的牌子,结果到访者只能隔门探视,这门厅里的旧信箱变成了“圣物”,人人拍张照片回去留念。
我去寻访之时,倒是清清静静,保安一开始隔门跟我说话,客客气气,后来聊得投机,就开门拉我去看那座老电梯,据说是英国产的奥斯汀电梯,不过已经粉刷成了绿色。他还告诉我,六楼张爱玲故居的大门还是当年旧物,不过不方便带我上去。我说无妨,脑子里莫名想起林夕写给黄耀明的一句歌词——一见又如何,不见又如何,你的春色不染心境。
心淡了,便无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