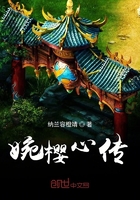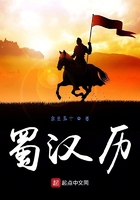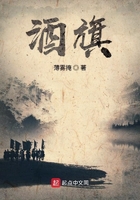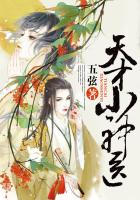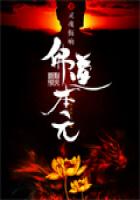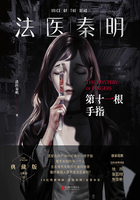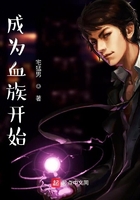[只愿天下情侣,不再有泪如你]
地址:福州鼓楼区杨桥路
说起林觉民,自然要提《与妻书》,这篇同时被选入两岸课本的情书兼遗书,字里行间俱是深情。
年少时读《与妻书》,常感壮怀激烈;年纪渐长后再读,挂心的却是林觉民的妻子陈意映——一个弱女子怎能承受这样的打击?《与妻书》的壮美与柔情,林觉民的大义凛然,都已留名千古,可陈意映呢?人们或许只记得她是林觉民的妻子,只记得《与妻书》开头那句“意映卿卿如晤”,有谁知道她在林觉民牺牲后不到两年就抑郁身亡呢?
所以,去寻访林觉民故居,私心里倒多半是因为陈意映。林觉民故居坐落于福州鼓楼区杨桥路,门口挂着两个牌子,一是“林觉民故居”,一是“冰心故居”。馆内有《与妻书》的复刻版,工整小楷,一丝不苟。看着这工整文字,那场景也如跃眼前,一个年轻人独坐灯前,在一方手帕上挥笔写着遗书,写自己对爱妻的思念,写自己对生死的淡然,情至浓时,便“泪珠与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
那些生前身后事,就在这一千多字的《与妻书》中一一呈现。不过,《与妻书》最让我喜欢的是那些生活点滴:“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
那些情致尽在汉语的美当中展现,而故居中虽有雕像,却也难寻故迹。
这是一栋传统福州民居,木质大门、石板地,有竹有花木有假山。据说院子原有三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拆除过半。1992年,新一波旧城改造到来,原计划将这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彻底拆除,建高楼大厦,同时在别处建个纪念牌坊权当补偿,好在有识之士为之疾呼,故居方得保全,并辟为纪念馆。
我们太不尊重历史,以至于一座名人故居的保全,都成了天大幸事。中厅有林觉民塑像,几个房间辟为有关辛亥革命的展室,西南小院便是《与妻书》中提到的“双栖之所”,一厅一室,院内有二人铜像,林觉民坐于圆凳上看书,陈意映站在一旁。见此情境,突然想到所读资料:18岁那年,林觉民与陈意映成婚。他租房办私学,并在家中办女学,宣扬西方民主制度,妻子陈意映、堂妹林孟瑜等都成了他的学生。
那些少年意气,早在他13岁那年便已迸发,他在父亲逼迫下参加了科举考试,可无意功名,在考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字,便扬长而去。
其实,林觉民可算是“既得利益者”,林家在当地是大户,在某些人看来,他完全不需要如此激进,但林家不但出了林觉民,还出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尹民、曾参加辛亥革命的林肇民,当然还少不了后来叱咤政坛的林徽因之父林长民。
体制内的受益者一旦觉醒,往往最为坚定。关于广州起义,各种记述已然太多,那是一场极短促的起义,且结局早如预料,就如林觉民自己所说:“吾辈此举,事必败。”但他还说:“然吾辈身死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这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身处局中,却能拨开迷雾,看清未来的脉络。
说回陈意映吧。新婚一个月时,林觉民因主张革命与父亲吵架,离家出走,后听说父亲挨家旅店找他,于心不忍,便于三天后回家,陈意映在劝他体谅父亲的同时,还说了一句“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
可是,怀胎数月的她跟不上林觉民赴死的脚步。在《与妻书》中,林觉民感慨造化弄人,不能与对方相伴到老,负了那深情厚爱,“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一对爱侣,终被历史撕裂。他也无悔,“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所以,他舍小家,为大家,“为天下人谋永福”。
林觉民牺牲后,林家避难搬走。买下他们旧宅的人家姓谢,家中有一女儿谢婉莹,就是日后的冰心。所以,在此故居中也辟有关于冰心的部分。
据载,悲伤欲绝的陈意映一个月后早产,生下遗腹子林仲新。不久后,革命便成功了,大家同欢庆,陈意映想必也是喜悦的,但悲伤注定如影随形。据说,福建革命政府成立时,福州的第一面十八星旗就是她与另两位烈士的夫人一起赶制的。但我相信,与革命有关的点点滴滴,于陈意映来说都是残酷的刀,让她想起亡夫。林觉民牺牲一年多之后,陈意映抑郁而终,年仅22岁。
在彼岸台湾,林觉民是音乐人极爱描绘的人物。童安格、李建复和齐豫都曾唱过与他有关的歌。在童安格的《诀别》里,有雅致的“灯欲尽,独锁千愁万绪。言难启,诀别吾妻。烽火泪,滴尽相思意,情缘魂梦相系”,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句“只愿天下情侣,不再有泪如你”。李建复的《意映卿卿》里则有一句“今夜我的笔蘸满你的情,然而,我的肩却负担四万万个情”。齐豫的《觉》里,有一句“把缱绻了一时,当作被爱了一世”,不过作为女人,她也同情陈意映,质问林觉民“谁给你选择的权利这样离去”。
他们已唱尽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