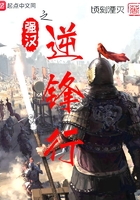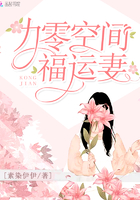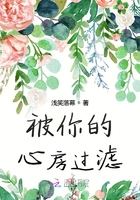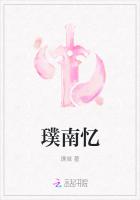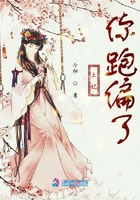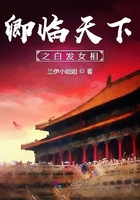[劫后桃花]
地址:青岛福山路1号
大概是小学三四年级时,我放学后常爱跑去青岛的福山路一带,它与红岛路、齐河路形成一个岔路口,距离中国海洋大学(当年国立山东大学校址)的后门不远,每逢春天,便有大量樱花桃花盛放,整条街上都是欧式庭院,花岗岩围墙斑驳沧桑。那时的我,已读了不少小说,却又未经人事,满脑子奇思怪想,每天上课时都在走神编故事,比如回到古代背着单刀闯江湖,又比如穿越至动漫世界跟着漂亮姐姐冒险,放学后便坐在那些欧式庭院的围墙或台阶上继续“构思”,各种剧情于眼前闪回。
长大后爱上电影,四处淘碟,攒下数千张DVD,终日沉湎于光影中。也爱话剧,自驾车去周边城市看各类演出,关于戏剧史和电影史的书买了一本又一本,寻觅各种旧事。后来才知道,那时流连的青岛福山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委实是名流荟萃之地。沈从文、吴伯箫故居均在这条路上,而路口的福山路1号,那个我常常坐在其门前编故事构思“剧情”的所在,则是洪深故居。
洪深,中国话剧的开拓者,早期极负盛名的电影艺术家。洪深故居极为雍容气派,居高临下,可远眺海湾,入门有左右石阶梯,有花岗岩照壁,大铁门尽管年久斑驳,可沧桑中仍可见昔年华丽。
青岛的名人故居,多与当年国立山东大学有关,名流学者前来任教,校方安排小楼租住,可洪深故居却是他的私产,是其父洪述祖的产业。
洪家是晚清名门,先祖是乾隆嘉庆年间的大儒洪亮吉,曾因言获罪、视死如归,其后人也不乏骨头硬的才子。洪述祖亦长于诗书画,却偏偏少了气节,一生贪财好名,因出身名门,曾任多位晚清名臣的幕僚,却屡屡因贪渎而遭解职甚至通缉,后攀附袁世凯。
宋教仁案后,洪述祖前往青岛,买下福州路1号,还曾在崂山的南九水附近找了一处山海相间的好地,建了一栋大别墅,名为“观川台”。1914年11月7日,青岛被日军占领。次年,洪述祖一家被赶出观川台,日军把这栋豪宅变成了军用的饭店。洪深曾经回忆:“日本人的拿去,是毫无道理拿去的,是利用武力拿去的。有一年,据说因为料理店的营业并不起色的缘故,日本人曾经要我父亲赎回,只需我父亲贴他六千元的损失,我父亲不愿花钱去买那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
后来,洪述祖离开青岛,却在上海遭为父寻仇四年之久的宋教仁长子宋振吕发现,被捕后判绞刑。
丧父时的洪深,正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攻读化学烧瓷专业,得知噩耗后的那年秋天,还差一年就可毕业的他选择了放弃,转而投考哈佛大学的戏剧文学专业,从此弃理从文。
这个选择无疑与父亲的死有关,毕业回国后,尽管洪述祖已死去数年,他仍登报声明与父亲断绝关系——此举在我看来既没必要也没人性,不过联想“五四”之后知识分子与家庭的种种隔膜,境地更为特殊的洪深选择用这种方式与旧式家庭告别,亦算情有可原。他也曾在《印象的自传》里写道:“我父亲不幸的政治生命使我陡然感受人情的残酷。我父亲下狱之后,许多亲戚朋友,尤其是我父亲走运时常来亲近的,立刻都拿出了狰狞的面目。一个不负责任无能为力的我,时时要被他们用作讥讽或诟骂的对象。而普通的人士呢,更是怀疑你,鄙视你,隐隐地把你不齿人类;仿佛你做了人,吸一口天地间的空气,也是你应当抱歉的事情……但身受的我,却从此深深地认识到了一个人处在不幸的环境中的痛苦。”
多年后,他仍对此耿耿于怀,1942年,他对友人马彦祥说:“我的那次家庭变故,给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决定,第一,我这辈子绝不做官;第二,我绝不跟那些上层社会的人去打交道。我要暴露他们,鞭挞他们。这样我就只有学戏剧这一条路。这条路我在国内学校读书时候就有了基础的。”
他创造了中国戏剧史和电影史上的诸多第一。比如他是中国第一位在国外专修戏剧的留学生,1928年首创“话剧”一词,创作了中国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申屠氏》,创作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中国第一所正规电影学府——中华电影学校也由他创建并亲任校长。1934年8月,他受梁实秋和赵太侔二人邀请,回到年少时曾客居的青岛,任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主任。
著名的电影剧本《劫后桃花》便在这期间完成。故事大意是清朝遗老祝有为逃至青岛,置办房产用于养老。谁知一战爆发,德国战败后,青岛被日军占领,原本与祝有为关系不睦的表侄余家骧投靠日本人,并迫害祝家,祝有为猝死,祝府被改作日本人的娱乐场所。这生活无异洪深家庭的翻版,只是做了戏剧化渲染,剧本中的祝府,原型显然是崂山的“观川台”。
正因对这生活太过熟悉,《劫后桃花》成就极高,是洪深的代表作——讽刺的是,他那些描写工人和农民的剧作,尽管一度被称许,但历经岁月沉淀,当我们不再以意识形态评价文艺作品时,《劫后桃花》便脱颖而出。1935年,明星电影公司将此剧本拍成电影,主演是影后胡蝶。电影的取景地便是青岛。这部片子在影史上被誉为“历史的照妖镜”。好玩的是,据说在那段时间里,洪深居所曾日日被希冀一睹影后风采的影迷们包围。
院内并未栽种青岛随处可见的桃花,不过每年四月走在福山路上,仍是一片花团锦簇,艳丽的桃花与樱花、紫藤花一道,沿街可见。
那些典故,即使简单道来,也有莫大魅力,令人神往,而发生了这一切的故居,便是我与陈年旧事的最好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