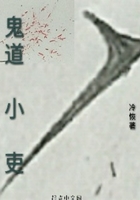就像他并不知道我的秘密,也不知道我在花园地底藏了一具尸体。他只向我感叹过,今夏的紫藤花开得格外繁盛,一嘟噜一嘟噜沉沉压在花架上,葡萄果儿也似的。
“圆珍,毛栗呢?这两天怎么不见那小东西?”
嘉瑞问起那只他送我的小猫。
是啊,毛栗呢?我也许久没见过它了。我努力去回想最后一次看见那小猫的情景,想来想去都想不分明,反而惹得我头疼起来。
“大约是走丢了吧?”我这样回答嘉瑞。
“没关系。”嘉瑞说,“朋友家里的母猫又下了一窝猫仔,你若喜欢,我再给你抱一只来就是了。”
嘉瑞整整陪了我两天。
周日傍晚时分,他在紫藤花架下轻轻亲吻我,说他下个周末将要去外省出差,不能来陪我,有事可以给他打电话。
我笑说:“你就不怕我红杏出墙,你脑袋上长出一片青青草原。”
嘉瑞深深看我,叹气说:“圆珍,我说过,你要是喜欢上了别人,尽管跟他走。我毕生惟愿你能幸福,如果我不了你幸福,那你大可以去别人那里追寻。”
“当真这么喜欢我?”我半开玩笑地说。
“我爱你,圆珍。”嘉瑞张开手臂拥抱我,嘴唇贴在我的侧颈,在那里留下他温热的鼻息,“我爱你,从第一眼看到你,我就爱上了你,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背叛任何人,在这世上我只爱你,别的谁也不爱。”
天快黑了,嘉瑞没开车,要赶末班车回市里,只能依依不舍同我告别,一步三回头离了珍园。
我坐在紫藤花架下,夜风吹来,带来山野间的凉意。入了夏,草窠里到处都有虫儿鸣叫,热热闹闹,此起彼伏。夏夜就是这般喧嚣吵闹,让人安静不下来。
我在花架下坐到了天完全黑下去,才起身回屋。
不知怎么,二楼浴室的窗户里竟亮着灯。我想,也许是嘉瑞走时忘记关了。
我直接往二楼走,准备冲个澡就上床休息了。然而我刚踏上二楼,就发现了地板上的异状——几天前,被我用刀刺死的黑衣女人躺倒的位置,出现了一大滩水迹。我曾费力擦洗过地板,因而记得,这水迹的形状,同当时那块血迹一模一样。
一串湿漉漉的脚印,从水迹里往前延伸,一直延伸到浴室门前。浴室的门开了一条缝,温黄灯光从里面露出了一条线的量,轻轻撒在脚毯上。
我发现自己没有勇气再往前走,顺着脚印走到浴室门前,打开那扇虚掩的门。
我发了疯般冲下了楼,跑到紫藤花架下面。没有工具,我就用自己一双手,徒手挖开了我填起来的坟墓。
坑挖得很浅,根本不是一个人能躺下的深度。
我从土里刨出来的尸体,属于我心爱的小猫毛栗。
它胸口的位置插着一把尖刀,我将它拔出来,才发现,那正是我用来刺黑衣女人的那一把。
夜风轻轻吹着,温柔得像硫磺温泉中的水流,像远处高楼上的笙歌。
微弱的星光里,我看见黑衣女人一步步向我走来。她有着鲜红的唇与鲜红的指甲,她的面孔像雪那样白。
我想起来了,我认得她。
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唯有周乐云喜欢穿黑色。
那是一个性格豪爽,坦率磊落的女人,如果生活在武侠小说中,必定是一位数一数二的侠女。
侠女嫁了一个老实巴交的温柔暖男,恰似黄蓉与郭靖。老实人名叫谷嘉瑞,虽没什么大出息,但父辈留下的家底殷实,足够他们过一辈子富足生活。
他们本该拥有幸福美满的一生。
周乐云的老家与我家是邻居,她幼时被托付给老家的姥姥照顾,就跟我成了玩伴。她家境一直优越,而我父亲在我年幼时意外过世,母亲长年患病,家中穷困潦倒,于生存线上挣扎。但周乐云不曾看低我,她将我视为妹妹,凭着一股子热心肠,她常常出钱接济我父母,连我的学费也一并包揽。多亏她,我才能顺利升入大学,完成学业。
周乐云比我大四岁,我上大一时,她已经毕业。她同谷嘉瑞学长大学交往四年,一毕业就结了婚。谷嘉瑞在他父亲的公司里谋了一个闲职,周乐云则做起了家庭主妇。他们想要一个孩子,但尝试了许多种方法,都没能如愿。
周乐云一个人在家嫌闷,便时常把我从学校召来与她同住。她的大房子里甚至有一间属于我的小小卧室,她为我精心布置妥当,指着那张颜色粉嫩的小床对我说:“圆珍,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但我知道,房间是她为她未来的孩子准备的,只是暂时让我借住罢了。
她待我是极好,我也并非不领情。她拥有这世上许多女人都羡慕不来的好运气,哪怕施舍给我一星半点,也足够照亮我的人生。我只是一个她用来满足自己同情心与慈悲心的对象,换作另一个身世可怜的女孩子也一样。
她从来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接受她的施舍。
我其实并不想睡那张粉色的公主床,我想睡的,是周乐云谷嘉瑞夫妇那间宽敞富丽的卧室里的大床。
我的寒暑假有大半时间在周乐云家中度过。我喜欢游泳,周乐云家里有座游泳池,每逢夏天,我可以一整天泡在游泳池里。
我总穿着高中时用打工赚到的钱买的便宜泳衣。那是我第一次给自己买东西,是唯一一件属于我的东西,尽管它有些小了,布料缠着身,稍微一动便露胸脯露屁股。周乐云多次笑我节俭,说要给我买件新的泳衣,都被我拒绝了,就这一样东西,我不想要别人施舍给我。
更何况,这件便宜泳衣也不是全无用处。
我知道有人在看我,当我在泳池里游泳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炙热滚烫的,一直黏在我身上。
我知道那是周乐云的丈夫谷嘉瑞。老实人也不像他表面看起来那样老实,而菩萨心肠的侠女也并非菩萨本尊。
从这一层面来说,其实每个人都是陌生人,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完全了解一个人。
我大二那年暑假,周乐云被查出了卵巢肿瘤,住进了医院。谷嘉瑞亲自去医院照顾他的妻子,日夜陪护,弄得自己疲惫憔悴,特别是得知他的妻子将被切除子宫与卵巢,再也不能生育后,他心理上都产生了巨大压力,一下子消瘦了许多,看得人心疼。
我一个人留在周乐云的家中,用她的化妆品,擦她的香水,穿她衣柜里一件又一件的昂贵衣裙。我在镜中看自己,眼睛明亮,嘴唇红润,皮肤白皙,身体柔软纤细。我是年轻的,健康的,就凭这一点,我就该胜过周乐云,我就该拥有本属于周乐云的人生。
没想到那天谷嘉瑞会忽然回来。我穿着周乐云的旗袍,戴着她的珍珠项链,手里夹着周乐云已经戒了许久的烟卷,伴着CD里的老歌跳舞的模样,恰好被谷嘉瑞撞见了。
他用不加掩饰的热烫目光打量我,说:“圆珍,你很像年轻时候的乐云。”
自然会像,我同周乐云日夜相处,把她的情态习惯学了个七八成。我知道自己怎样低垂着眼帘,怎样勾着唇角,怎样扭摆腰肢走向他,会让过了这么长时间清心寡欲生活的谷嘉心旌摇荡,魂不守舍。
我走到了他面前,伸出手臂勾住他的脖子,踮起脚,轻轻吻了吻他的嘴角,然后附在他的耳边说:“嘉瑞,你不是想要孩子吗?让我给你一个孩子吧。”
那天夜里,我终于如愿以偿,睡到了周乐云那张大床上。
卧室墙壁上挂着周乐云与谷嘉瑞的结婚照。刚毕业的周乐云,穿着洁白的婚纱,嘴角挂着幸福的微笑,眼神一尘不染。她就安静地待在照片里,看着我与她的丈夫在她的床上乱搞。
我始终与照片上的周乐云对视,张大嘴向她发出无声的嘲笑。我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感,不是因为做爱的对象是谷嘉瑞,而是我破坏了周乐云幸福美满的家庭——那感觉就好似亲手打碎了一只精美且昂贵的花瓶,那种撕裂美好事物的,毁灭性的快感。
我不禁想,如果周乐云死了就好了。如果她死了,我就可以占有她的人生,成为谷太太与这座房子的女主人。
可惜周乐云的手术很成功。医生切除了她的卵巢与子宫,把癌细胞从她身体剥离掉。她的性命暂时保住了,只是身体整个垮掉,变得干瘪瘦小,毫无风韵可言。
在周乐云术后恢复那些日子,我与谷嘉瑞每夜都在床上鬼混。在妻子眼皮子底下偷情,这样的事实让我与谷嘉瑞都无比兴奋,抱在一起抵死缠绵,仿佛世界末日前最后的狂欢。
我想过会被周乐云发现,也想象过周乐云会是各种反应,但我无论如何都没能料想到,真相居然会害死了她。
那是我大二暑假将要结束的时候,周乐云送我回学校,开车的人是谷嘉瑞。
我在邻市上学,开车大概需要两个小时,途径一段陡峭的盘山公路。我不明白周乐云为何坚持要我连夜去学校,也许她已经对我与谷嘉瑞的事有所觉察。
我坐在后座,一路上都在观察副驾驶的周乐云。她除了面色有些苍白,并无异样,甚至会在后视镜里冲我微笑。
或许是因为初秋的天气太闷热,天边堆积着铁青色的积雨云,云中翻滚着雷声——或许是快要下雨的缘故,我隐隐感觉不安起来。
车子行驶到盘山公路上时,周乐云忽然转过头面向我,问了我一句话:“圆珍,你喜欢我家的游泳池吗?”
我下意识回答:“喜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