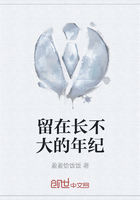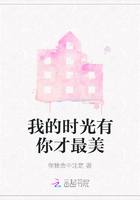长期的斗争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他于1908年2月去世,年仅三十四岁。
穆斯塔法·卡米勒留下了一些著作,其中有《诸民族生活和罗马的奴隶制》《东方问题》。
他被认为是这一时期的天才和民族复兴的奠基人之一。他是个有才能的新闻作家和雄辩的政治演说家。他作品的风格朴实明朗、强劲有力。他的思维能力很强,能聚精会神于自己所思考的内容,因而言辞达意,毫不造作。他的演说激情洋溢,语句中的慷慨昂扬之词直到今天还萦回在人们耳际。他不愧是埃及民族主义的领袖,是后来演说家、政治家们的导师。
萨阿德·柴鲁尔(1927/1347)
萨阿德·柴鲁尔生予埃及西部省的伊布亚纳镇,幼年在乡塾学习朗读、写作、背诵《古兰经》,后到爱兹哈尔求学。爱兹哈尔的教学方法适应了他喜欢思辨的天性。在那里,他以口才流利、聪慧和论证力强而著称。他求学于哲马伦丁·阿富汗尼,受到老师革命精神和文学风格的熏陶和影响。他曾参加阿拉比革命,后被监禁数月。出狱后从事律师职业,很快便成为律师首领,被任为国民上诉法院顾问,以后主管教育部工作。他重视用阿拉伯语讲授所有科目,并指令将各门学科教科书都译成阿文。在他主管司法工作期间,为适应时代精神曾修改了一些法律,改革了部分司法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举行和会时,埃及起而要求自己的权利,并组成了代表团,萨阿德任代表团团长。为此,他和他的同伴被英国军事当局放逐到马耳他岛。但他不甘失败,从那里回到巴黎暂住下来,等待时机,为争取祖国权利继续斗争。
1920年他和一些代表团成员前往伦敦,与英国政府谈判埃及的要求,谈判虽然失败,但他返回埃及时仍受到人民极其隆重的欢迎。不久,他再次被英国政府流放,被赦后仍然回到埃及。1923年宪法公布后,他出任内阁总理,后任议长,直到1927年去世。
萨阿德·柴鲁尔是当时东方最大的演说家之一。他的演说明白流畅,富有感染力,具有充分的论据和严密的逻辑。他的语言朴质、隽丽、真诚而达意。仅仅作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民族自由战士之一——即便不是绝对最伟大的话,也足以使他感到自豪的了。
易卜拉欣·雅兹基谢赫(1847—1906/1264—1324)
生平1847年3月2日,易卜拉欣·本·纳绥福·雅兹基出生在贝鲁特一个语言和文学之家。他从小生活在酷爱文学和语言的环境中,这一特殊环境促进了他才能的发展,使他聪慧早熟。父亲发现他的才能后,对他特别关注,从小教他语言基础知识,鼓励他的文学爱好。他很小就开始吟诗、写作、钻研语言、博览各门学科的书籍,并在暇时从事绘画、雕刻和音乐,不到十四岁便制作出第一个阿拉伯日历。他早期喜爱诗歌,后来转向散文,以后成为这一领域的巨匠之一。
其父纳绥福死后,他与艾哈迈德·法里斯·舍德雅格之间展开了长期争论,并因此在文学家中出了名。1872年,他被委托创办《成功》报。
那时耶稣教神父们都希望有一部精确的阿拉伯文《圣经》译本,他们发现没有比易卜拉欣谢赫更适合于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了,他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他在埋头自学中获得了希伯来语和古叙利亚语基本知识后,经过九年辛勤劳动,终于取得成果,《圣经》以最好的预期效果问世,特别是《旧约》,全由他一人译出。
当他与耶稣教神父们一道工作时,他们希望他能编订一部阿拉伯现代词典,这便是他直到临终还未完成的《语言珍奇》词典的诞生原因。在这些年中,他还被委托校订一些宗教和文学等方面的书籍。在翻译《圣经》期间,他在贝鲁特住了几年,之后在主教学校教修辞和文学。他培养了一批在阿拉伯文学界享有盛誉的文学家,如哈利勒·穆特朗等。这期间,他还将父亲的某些著作简编成现代教科书,使它更容易为学生所接受;他还继续完成了父亲的未竟之业,用了四年多时间对穆太纳比的诗歌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完成了穆太纳比诗集的注释、校订、补遗和出版工作。他在主教学校任教时发表了《毕业生进修文学课程》演说。在贝鲁特的最后日子里,他开始编著《先驱者的希望》一书,出了两部,第三部因他去世而未能完成。
那时,新闻业正在阿拉伯国家兴起,出版了《心灵》和《文摘》两种杂志。易卜拉欣谢赫切望回到新闻界,尤其是从事有关科学方面的写作。当时,著名的波士特博士在贝鲁特创办了一份命名《医生》的医学杂志,后来停刊。于是易卜拉欣谢赫便和他的两位朋友柏萨拉·吉尔扎勒博士和哈利勒·苏阿达博士合作,于1884年使《医生》杂志复刊。该杂志除刊登他们写的医学和科学文章外,还刊登他单独写的文学和语言方面的文章,其中最有名、最有价值的是《语言笔录》。杂志出版一年后,他发现未取得预期效果。他看到埃及是自由之乡,是文学和新闻的发源地,于是决心离开《医生》杂志到埃及去创办一座印刷所和一份科学杂志。在这之前,他先到欧洲各地游历并筹办了一些必要的印刷器材。他到开罗后,与吉尔扎勒博士合力创办了《宣言》杂志。在《宣言》杂志上他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语言和时代》。但是,新杂志只出了一年,两个朋友便分道扬镳。易卜拉欣谢赫于1898年单独创办《光明》杂志,销路颇广,一直出了八年,直到1906年他去世。
易卜拉欣·雅兹基谢赫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一生致力于科学和创作。他的一生是不断获取知识、孜孜不倦努力工作的一生。除喜好科学外,他还酷爱艺术美。他生性孤僻,但这并未妨碍他热爱祖国,他对祖国的热爱使他成为一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勇敢热忱地为祖国的进步和解放而斗争。他对己对人都率直诚恳、不虚伪做作、不自欺欺人。他坚持真理,敢于公开披露事实。他努力维护自己的尊严,但却从不伤害别人。他清廉正直,不愿获取廉价报酬和不光彩的物质利益,他不出卖事业以换取金钱和职位,不拿荣誉作交易,不甘忍受屈辱。尽管他有时一贫如洗,也决不为生计而向任何人屈节。他事事知足,并以此自得其乐。他经常做好事。那是为了仗义,而不是为了个人荣誉或别有所图。这方面的最好证明,是他的许多文章和他为之校订却把全部功劳归于别人的大量书籍。
易卜拉欣谢赫对自己尊严和荣誉的维护有时到了高傲和严峻的程度,这特别表现在他对自己的敌手,尤其是对舍胡神父的某些批评和反击上。不管怎样,易卜拉欣谢赫是一位内心最纯洁、品德最高尚、最受崇敬、最具多方面才能的作家之一。
易卜拉欣·雅兹基的诗歌和散文易卜拉欣谢赫很少写诗,尽管如此,他对诗歌还是像对其他方面一样精益求精,达到了在散文和语言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因此,他的诗歌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他的文学活动的一个方面。
他有一本名为《项链》的小诗集,共九十多页,系手抄本。后来由他堂弟在巴西石印出版,并增补了一些他的书信和纪事诗。他还有两首未收进诗集的诗歌,一是曾在《光明》杂志上发表的描写花卉的诗,一是他二十岁时在叙利亚协会朗诵的《米姆韵基诗》。
众所周知,阿拉伯新闻业成长之初十分羸弱,但它在一些极有才华的人如艾哈迈德·法里斯·舍德雅格、布特拉斯·布斯塔尼教师、艾迪布·伊斯哈格等手中逐渐得到发展、进步。他们是阿拉伯新闻业振兴的先驱,他们在克服每个阿拉伯新闻工作者都曾遇到的困难和使阿拉伯语适应充满各种新发明、新创造的时代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一艰巨的任务在易卜拉欣生活的时期仍需付出极大努力才能完成。他以极大的志向献身于这一事业,并取得两个方面的重要成就,即按规范方式办报和改造新闻语言。
易卜拉欣谢赫酷爱科学,博览群书,他创办的刊物中有相当数量关于科学方面的论文和文章。他荣获过瑞典和挪威国王颁发的科学奖章,他还被遴选为巴黎、安特卫普和萨尔瓦多等地的天文学会成员。易卜拉欣谢赫写过有关化学、物理、自然、医学等方面的文章,在每个方面都表现出广博的知识、透彻的见解和对事物深刻的理解,并能通过自己的发现把科学的益处告诉人们,显示出他杰出的科学才能。
他写过天文方面的文章,其研究证明他对最新理论、对天文学中互相对立的观点的广泛了解。他有时甚至费尽心力去创立自己的观点。
他敢于去碰好几代优秀数学家都无力解决的将圆七等分的难题,他的解答近乎正确。
尽管如此,他还不能算是一个科学家,因为他的观点大部分是从书籍刊物中获取的,很少有个人发现,即使有,其价值在科学上也微不足道。但这并不是说他缺乏大科学家的高度才华,他缺少的只是必要的实践。他在改造语言,使其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任何科技术语、专业词汇方面的功绩足以弥补他的缺陷。他是当时我国第一个了解科学发展、希望能在阿拉伯民族中对之进行普及,使他们了解西方的进步并促进自己民族文化发展的有识之士。
易卜拉欣谢赫的伟大在于他是一个信念坚定并为之奋斗和献身的勇士。他为了执行使命而忠诚工作、奋斗一生,从不动摇和退缩。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宁愿在贫困中生死,也不去追求财富、官职和地位。他牺牲了自己的休息和健康,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尽管体弱多病,他仍坚持以毕生精力完成了这一领域广阔的使命。
如果没有这种献身精神,如果不是对使命的坚定和忠诚,那么近代文化复兴就不会建立在这么坚实的基础上,无论在制作字模便利印刷方面、在培养复兴人才方面、在提高新闻和科学的水平方面都是如此,且不说他对现代复兴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语言的重大贡献,不说他为许多文学家树立了楷模的精良的写作技巧。
批评家们对易卜拉欣谢赫的普遍指责是他的著述不多。这一指责也许有一部分是对的,如果我们注意到易卜拉欣谢赫没有在他思想和实践的各个领域留下一部完整的、独具价值和声誉的著作的话。他不像其他文学家们那样,声誉往往建立在一部系统的著作或某一方面的专著上。
然而,只要我们仔细分析这一指责,就会发现它毕竟不能全部成立,也丝毫不能降低易卜拉欣谢赫的价值。首先,他在著述、校订、注释、教育和制作字模等方面的工作范围之广,是不能轻视的;其次,易卜拉欣的声誉不只是来自他的作品,而且还来自他对整个时代全面、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至今仍未消失。他无论是著述、校订、注释还是教学、制作字模,都是为他后来的文学家铺平前进的道路,成了各方面的范例,从而为效法者创造成功的条件,给整个复兴打下基础。
沃利丁·耶昆(1873—1921/1290—1340)
生平沃利丁的祖父是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的外甥,母亲是塞加西亚的一位公主。他三岁时随父移居埃及。父亲死后,他被送进安扎尔贵族子弟学校学习阿拉伯语、土耳其语、英语,后又学习法语。以后开始写作和吟诗。早期,他支持政府。后来他到伊斯坦布尔,看到国中阴谋不断、腐败盛行,愤然回到埃及,创办《公正》报,抨击暴虐、主张改良,后因财务困难而停办。以后他在一些埃及报刊上发表文章。
阿卜杜·哈密德苏丹为了拉拢他——至少是为了堵住他的嘴,任命他为教育部最高委员会委员。他常和政府官员们发生冲撞,因为他发现他们缺少诚意、心术不正、对工作敷衍塞责。他和反对政府的埃及自由战士接触,因而被跟踪、侦查,住处周围布满了密探。一天,他外出为妻子娜福莎请医生,一个警察上前阻拦,沃利丁气愤地打了他。省长对他横加指责,他把省长摔倒在地。于是他被监禁,后被流放到锡瓦斯。他从锡瓦斯给亲人们写信,亲人们不久便前去与他相会。他还与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通信联系,并埋头阅读、著述、写诗,以减轻在流放中的烦愁,就这样一直到被赦。
回到埃及后。他继续从事写作。后来侯赛因·卡米尔苏丹委任他作宫廷文书,他写诗赞颂他,得到宠幸。不久,他患哮喘症,继而患胸疾。后病逝于赫勒万,葬在开罗。
沃利丁生性有些神经质,思维敏捷清晰。他酷爱自由,敢于直言,不怕心术不正者的攻击和妄自尊大者的揶揄,面对暴虐者而毫无畏惧。他为人易处,十分敏感,且诙谐善谑。他慷慨大度,窘困时坚忍,位高时清廉。他对褊狭性的厌恶和对旧传统的憎恨是彻底的,涉及思想、社会的一些领域。他不顾及家族风习或宗教礼仪,不注重传统的写作方式。也许他在这方面的过分,是由于他未对传统作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