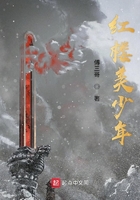回民教争如无外力的干预,必然逐步加剧。而所有大的教争事件,都免不了官府介入,官府介入后通过打压教争的某一方稳定局势,则被打压的一方便会将斗争矛头转向官方。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继为花寺掌教的马桂源与穆夫提门宦的冶成祖率领两派在西宁因分寺诵经互争,官府派提督成瑞剿办,为回民击败。③总督乐斌捏报胜仗,被革职。户部尚书沈兆霖于同治元年(1862)正月初七署总督,在西宁、碾伯两邑士庶的“具控”下,于正月十六日进剿“滋扰西宁、碾伯两县,村落多被蹂躏”④的撒拉回民,因营伍废驰,不能得力。至四月再次进剿,据文献,“毙贼四千余名,焚毁村庄多座,该匪被剿穷蹙”。六月十九日,“该喇嘛百户及总乡约马归源率领十二工头人六七十名,并撒回三百余人,至代理巴燕戎格厅通判王锡文处跪求投诚”。⑤马桂源当时年仅二十岁,此次投诚,为他以后与官府的互相合作奠定了基础。
马桂源(1843-1873),亦称马归源,祖籍河州,寄籍西宁,是花寺门宦创始人马来迟的第四世孙和第六辈掌教。咸丰十年(1860)继大哥马复源为花寺掌教、回民总约、赏戴五品花翎,因以“顶子太爷”知名。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三。桂源“雄于货,曾捐候选同知。”⑥乡约是西北回民社会中国家机器的最末端,赏戴花翎和捐纳同知则使他与官方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其兄马本源,行二,有武举的身份。①
马桂源虽投诚,但官府无力节制,教争事件层出不穷。同治二年,“临洮、华寺两教籍办教之新旧滋事。汉番良民被其杀掠,亦聚团以备。”②据玉通奏称,三月初九,马桂源聚众数千“将东关、北古城、北关一带居住洮教回子杀伤大半。”丹噶尔厅、威远营等处也于初六日教争,双方互相攻杀,各有损伤。但此次教争为了避免官府过多介入,花寺方面向前往调解的官员特意强调“伊等两相争斗,不敢扰害汉民。”似乎这样便给足了官府面子,使他们得以继续维持统治地方的假象。但实际上,附城、城内的汉民确实没有受到攻击,但在南川营、丹噶尔厅的各村庄都受到冲击,③官府根本无力控制。
元年(1862)七月初二,署总督沈兆霖溺死,④玉通鉴于营伍废驰,军威不振,饷需支绌,进剿无兵,民团不济于事,不得已倚已投诚的马桂源、本源兄弟为心腹,借以维持西宁地区的粮饷和统治,“至是檄桂源署循化厅同知,本源署循化营游击;后(同治七年——本书注)又调桂源署西宁府知府,本源署西宁镇标游击,代行西宁镇职务军政。大权遂为马氏昆仲所握。”⑤但从以后局势的发展看,马氏兄弟虽握重权,但难获汉绅支持,为此实行修孔庙、改畜牧之法,⑥以拉拢绅民之心。八年(1869)十二月初十,玉通病死,预师接任,则干脆驻于距西宁300里外的平番,马氏兄弟对西宁的统辖更为方便。这个过程中,他们实际并没有与官府官军形成根本对抗的局面,只是借由武力优势取得教争优势、控制地方局势,代理了官方统治。但马氏兄弟的命运颇具悲剧性,二人为清廷实际出力甚多,但最终却被官方视为必须除去的死敌。
马桂源一身而二任,既是政府官员,又是回民领袖;他的权力与其说是官方授予的,还不如说是他背后回民势力的反映。当时官员奏称“其实西宁郡城城(外)[门]之启闭,回匪司之;公文之往来,回匪拆之;官民之出入,回匪主之。虽无戕官显迹,而已阴踞城池。”清廷也“不得不暂示羁縻,冀图他日大举。”①同治六年(1867)西宁镇总兵黄武贤更加夸大其词,“所有在城文武官员,被匪挟制多年,任其使唤,非朝廷之官也。……民不敢阻,官不敢办,任从匪意,惨不胜言!”②左宗棠也认为“至如西宁之马尕三,借称就抚,挟持官军,而西宁汉回兵民各务,阴归其掌握,名为官抚回,实则回制官,与滇回之包藏祸心,如出一辙,尤勿论也。”③
马桂源继任掌教时年仅二十岁,他虽是教门的首领,但很长时期并不掌握西宁回民军军权,回军的领导权实际归马尕三所有。官书说,“逆回马尕三欺其年幼,冒充阿浑,煽惑撒回。马归源上年八月进山即被马尕三拘留,假其名目,号召撒匪滋事。”④恩麟也认为马桂源“年幼才闇,不能约束属下,因而狡黠之徒恃众妄为。”⑤据说马桂源本人与马尕三关系恶劣,“查西宁回民总约马桂源与马文义怨毒颇深,久欲投诚,无如各处回众尽从马文义一人,不遵马桂源约束。”⑥官府无奈,不得不仰仗马桂源堂叔、游击马永泰之妾马乜氏⑦招谕调停。后来主政陕甘、深受儒家教条熏陶的左宗棠等人无不视此为奇耻大辱,谓“西宁名存实亡”。①
实际上,西宁府地区形成了多头军政的局面。官府虽名存实亡、退居幕后,但作为国家统治的象征,仍然继续存在;官府的实权归花寺回民掌握,其掌教同时兼有国家官员和回民教主的双重身份;马尕三领导的最有力的军事力量则不完全受官府、掌教控制。以西宁府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形成了极为复杂的局势,回、汉、藏各族群、回民各派系矛盾尖锐,难以控制,不惟清廷官员棘手,马桂源署任,也一样难于招架。
这种局面渐渐改变。同治十年(1871),一贯强硬行事的马尕三病逝,在马桂源的安排下,西宁回军由教主家族的马永福接统。马永福性懦不能制众,听马氏兄弟是从。这样,马桂源身为现任官吏、回民教主的同时,又掌握了西宁回民军事力量。在金积堡战役阶段,署理西宁的马桂源兄弟并没有支援过宁、灵回民军。十一年(1872),清军进军河狄、西宁,他们也多次配合清军的军事行动。败退西宁的陕西回军、西宁本地回民及河狄回军求抚,他们更是居间出力不少。西宁局势也向主和的方向推进。
然而,在权力大大加强的同时,他们与清军日益互不信任、相互戒备。白彦虎、禹得彦、崔三(伟)等部转移到西宁后,强化了他们稳固自身势力的决心。兄弟二人借口陕回据大小南川,拒不呈缴马械。左宗棠恐激起事端,以进剿陕回为辞,令提督何作霖带马步八营先赴碾伯,刘锦棠继之。抵大峡口时,陕回、土回已联合抗拒。据说清军又得到已降回民的探报,说马桂源在西宁府东关私宅会见陕回首领共议抗拒官军。马本源自称统领陕湟兵马大元帅,马桂源仍称知府。②若依此说,马氏兄弟的行动则有将西宁地区置于控制之下的长久打算。然而在当时清军节节胜利,势如破竹的情况下,这种打算只能落空。一嗣河狄抚局成,清军节次进攻肃州,解决回民势力对西宁地方的支配也同时成为官方目标。期间,西宁的存留官员、汉绅势力扮演了重要角色。
由于西宁仍存有以豫师为首的官府力量,他们实际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为官军的进攻积极做着准备,所谓“堵击外匪以翦其羽翼,暗整各团以助我兵力,筹备粮草以备大兵进剿之需,添筑堡寨以为转运畅行之路,时发示谕遣员开导以安其反侧,散其胁从然后步步为营、持重而进。”①这导致马桂源的实力被一步步削弱、架空。
同治十一年(1872)八月,马桂源带精壮回军出东关,前往东校场校阅部队,两日不归,西宁城内官员、汉绅在署西宁道郭襄之的带领下,关闭城门,不准他再入城。②此时,进军西北的各级军政官员已决意要抛弃马氏兄弟,马桂源向驻静宁的清军总理营务处陈湜求援,并未得到支持,反而“令其不必进城以释群疑。”此后屡与官军战,屡败之余,又屡次向清军乞抚,皆不获准,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兄弟二人最终于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为已投诚受抚的马占鳌计捕于西宁城外东山,押赴兰州凌迟处死。
除西宁外,丹噶尔厅、大通县的失陷均与回民教争有关。大通汉团因与回民军对战,城破后遭到严重报复。《平回志》载,同治四年(1865)二月庚午,“大通县回与汉团接战,入城劫纵监犯,掠汉民财物一空。居民惊恐,投井服毒者男妇以千计。”③迄十二年(1873)正月刘锦棠克复后,据称“向有三千余人,逆回马寿自小峡败归,戕其丁壮。现仅留老弱妇女六百余口。”马寿被清军磔于市,“汉民争摘其心肝,啖之立尽。”④对此高文远先生批评说:“人民反抗政府,政府出师命将平乱,是正常之政治运作,擒其首恶,绳之以法,亦为法律之必定程序,行刑之后,任令乱民摘其心肝啖之立尽,为毫无法度的行为,实有失战争的道德与原则。”⑤刘锦棠沿用左宗棠策略,“迁城关回民于河东西,另招城西北逊布马、广利顺、张家寺各汉堡难民实之。路旁回堡亦量与汉民更易。”①这种措施实现了国家统治的秩序稳固,也是对回民的毫无顾忌的歧视性举措。
总的来说,马氏兄弟控制西宁期间比较温和,与官方的合作也较为深入,所以清军杀马氏兄弟之后,没有再对西宁回民进行报复性善后行动。就整个河狄西宁这块边缘地区而言,清军并没有触动当地回民社会的根基,回民的力量也没有遭到严重打击,成为日后西北回民社会组织化走向高峰的中心区域。②
六、肃州一隅的回民起义
肃州为陇西重镇,是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内地联结新疆的必经孔道和举足轻重的交通枢纽。肃州起义回民的核心力量为猎回,张集馨谓“猎户生长山谷中,路径熟识,日以捕牲为业,枪亦施发有准。”③这种生活方式造就了他们犷悍善战的性格,所谓“然猎户犷悍,多系回籍,桀骜不驯……地方官绳之以法,便千百为群,夺犯伤差,公然抗拒。”甘肃提督索文平定“野番”时,曾借用猎回的武力,肃州猎回即为索文所置,“甘肃野番滋扰久矣……提督索翰堂两次带兵剿捕,附近边圉,渐臻安谧。而新疆大道,仍安置猎户三千人,来往护送官商,并挖金砂,以为生计。”④索氏家族即因此与肃州猎回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在索文之子索焕章时发挥了作用。索焕章在新疆与妥明起义,即与较邻近的肃回互为声援,肃回领袖马文禄也被妥明封为元帅。
肃州地区的回民反清是由发生于他处的洗杀回民的事件引发的。“肃州回族皆住东关,或策名仕版,或经营商务,安居乐业,本无叛心。”同治三年(1864),发生于凉州府古浪县大靖堡的屠回事件刺激了肃州回民,慕寿祺称“后闻大靖堡之屠回、甘州之驱逐回族,咸有戒心。至是,南山猎回先反,肃回知公家不容己也,始谋叛。”①这样,肃回于四年(1865)二月在猎回首领马文禄领导之下起义,随即赚取城池,杀毙官员,控制官府,很长一段时期内,肃州“……各门均系回民把守,稽查出入、文武衙门公事皆由回弁主持。”②这种情形与西宁是很相同的。河西一带东自古浪、镇番(民勤),西至玉门、敦煌,甘、凉二府和肃州、安西州等广大地区的回民,都先后卷入起义浪潮之中,但各处旋起旋灭,肃州渐次成为河西回民起义的中心。
马文禄,又称马四,河州人,寓居玉门惠回堡,曾是甘州提督索文部下的“镇标都司”。③同治八年后肃回与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达成短期的“抚局”,马文禄又以“马忠良”的名字见于官方文书。肃州本地的回民力量其实并不强大。据成禄奏,“肃州本城回民不过四五百名,尚有口外哈密缠头寄居在城者三四十户,此外各处寄住回民约有二千,半系妇女老弱。”④在左宗棠进规陕甘以来,各地战败的起义回民纷纷集中至肃州:“其客回从逆者,关外则沙州、哈密缠头,红庙子各种,关内则西宁、河州、循化、保安营、陇西、狄道、伏羌、甘州各种,及陕西流徙之回,约共两万有奇,能战者半之。汉民日微,回党日聚,势不至沦为绝域不止。”⑤广泛地联合各地穆斯林共同抗击官军,成为肃回起义的一个特征。
马文禄曾被“妥得璘伪封元帅”,以“西宁猎户纠聚撒拉回番即西宁、河州剧盗偷儿于此,以通关内外花门消息”⑥,并且“妥逆曾遣股贼四千来援”。①一段时期内,很可能“肃城一切事宜悉听乌鲁木齐逆首佗阿浑(即妥明——本书注)指挥。”②因此学者谓,“肃州及河西回民起义起了沟通关内外各族穆斯林起义的桥梁作用,陕甘同新疆各地的各族穆斯林起义是互相联系,戚戚相关的,形成了以回族为主体的西北穆斯林大起义。”③尽管如此,到同治九年(1870),“缘肃州一带良回尚多,易于开导。”④此种矛盾的情形与肃州当地回、汉民人并无重大民族矛盾有关。
清军克服肃州,湘军一部损失慘重,包括悍将杨世俊在内的大批将领阵亡。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刘锦棠率新组湘军自西宁至肃州,驻营南门,“所抚陕回崔伟、毕大才等驰马城下,呼马四告以死期已至,善自为谋。马四自知生路已绝,亲诣大营乞降。”⑤显然,原为清军劲敌,现已投诚重用的崔伟等人亲自现身劝降,对马文禄触动极大。或许他认为可以得到与崔、禹等人一样的归宿。然而这样的恩遇没有再临,他的结局跟马化龙一样,本人及骨干共九名于九月二十三日被清军“磔之中军”。